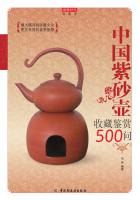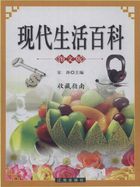小说与戏曲无疑是明代文学最有特色、最重要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明代文学的高潮要到晚明才真正到来。这样说并不等于本书要把诗文从明代文学史上开除,它们也是明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和西方不同,有它自己独特的发展史。其独特处在于小说和戏曲同生共长,彼此依托,关系密切。不把它们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要弄清其发展规律简直就不可能。因为相当多的作品是在书会才人、说唱艺人和民间无名氏作家那里经世代流传之后,才最终由文人写定的。它们是不同世代的作者,在连续不断的流传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文人的小说、戏曲,在它的带动下成长起来。
“书会才人”这个名词,最早见于元代钟嗣成的《录鬼簿》,后来就一直流传下来。然而,对于书会才人的身份,前人并没有做出明确的界定。其实他们就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改编写定者。有必要说明的是:所谓集体创作,并不是指同一时间的集体参与(在不同时代的参与者之间当然不可能有彼此间的讨论和质疑),而是指不同世代的民间艺人,对历来传承的小说、戏曲加以删润和修改。这里存在着一条可以粗略地称之为优胜劣汰的进化律,如果某一时期书会才人的删润和修改不是后来居上而是相反,他们的业绩就有可能被后人置之不理,而重新以他们着手前的式样为依据。
上面说的改编写定,包括从被动的记录到全面的创作等种种不一情况。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小说、戏曲,都经历了长期的、不止一次的改编和写定,才能从不太完美的素材发展为比较完美的作品。在这个过程中,书会才人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顾名思义,书会最早应是说话人的行会,后来扩大到杂剧、商谜等其他伎艺。明代容与堂刻本《水浒传》引首词所说的“书林”,南戏《小孙屠》
所署“古杭书会编撰”,《宦门子弟错立身》所署“古杭才人新编”,都证明它们是书会才人的作品。书会才人可以同时是演员,也可以以编写为主,不一定上场演出。尽管《醉翁谈录》对编写小说的才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事实上编写戏曲的才人必须满足更高的专业要求,至少在书面知识上是如此。戏曲有严格的格律,包括四声和协韵。因此,书会才人必然同时也是文人。但由于社会地位低下,他们算不上士大夫。《录鬼簿》之所以将名公和才人加以区别,其意义就在这里。
古代的书会是很松散的组织,可能没有任何确定的组织形式。书会才人在宋金时代实际已经产生,虽然还没有找到同他们真实身份相符的记载。入元以后,由于科举考试停开的时间很长,文人因此大批沦落为书会才人,喧宾夺主地将原来文学修养不那么高的书林中人挤到一旁,使自己成为其主流。洪武、永乐时代,尽管文人经常遭到政治迫害,但作为社会的一个等级,文人(包括书会才人)的地位有所改观,他们又恢复了原来的身份。现在所能找到的关于书会的最后记录,见于朱有炖的杂剧(《刘盼春守志香囊怨》第一折)。后来,大多数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写定者,就由社会地位略高的文人接手了。
人们对明代戏曲的发展有诸多误解,其中之一是杂剧在金元以后成为绝响,少数文人和他们豢养的男女演员在书斋或红氍毹上吹弹演奏,只是文人茶余酒后的一种自娱,与民众已经隔绝。但据《金瓶梅》对戏曲演出的描述,当时上演的杂剧有《西厢记》(六十一回)、《金童玉女》(三十二回)、《两世姻缘》(四十一回)、《留鞋记》(四十三回)、《风云会》(七十一回),另有《抱妆盒》杂记(剧),曲文和今本不同。事实上明代杂剧之盛,远远超出一些人想当然的看法。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元代杂剧约550种(不妨指出此书所录元代杂剧中,有多本是宋金时代的作品),他的《明代杂剧全目》所载明杂剧则有523种。且不说在明初有朱权、朱有炖两个亲王的杂剧创作和理论研究,其后在传奇之外兼作杂剧的也大有人在。
如《红线女》的作者梁辰鱼、《昆仑奴》的作者梅鼎祚、《一文钱》的作者徐复祚。还有以杂剧闻名于世的文人,如徐渭和他的《四声猿》,汪道昆和他的《大雅堂杂剧》,王衡和他的《郁轮袍》、《再生缘》、《真傀儡》、《没奈何》等都是不能轻易抹杀的。朱有炖的杂剧在明初广为流传,《四声猿》后附有演出注意事项,在汪道昆和王衡的杂剧中也不难找到演出的记录,说它们是案头剧同样不符合事实。
人们对明代戏曲的第二个误解,是关于南戏的起源与存亡。兴起于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和长江流域广大城乡的南戏,被人为地局限于温州一隅,并且有人硬说它在明代已成绝响。事实上保留至今的古代南戏文献,关于杭州的记载还略多于温州。南戏中惟一经文人彻底改编的是赵贞女的故事。人们熟知的它的改编者,即《琵琶记》的作者高明,是温州瑞安人。应该指出高明改编《琵琶记》,是在远离温州的宁波栎社。广为流传的关于赵贞女故事的陆游那首诗——《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之四所反映的,是流传于绍兴农村的民间传说,离温州较远,离杭州却很近。众所周知,一个剧种的兴起,必以一种唱腔作为依托,而温州至今没有找到产生于本土的唱腔,这是南戏产生于温州论者不可逾越的障碍。
南戏是否在宋元之后趋于衰歇?只要看一看《金瓶梅》就可以得到解答。西门庆家正式宴请高级官员时,如第四十九、六十三、六十四、七十二、七十四、七十六等回,演唱的都是海盐腔,尤以七十四、七十六回的记载为详细。这无可置辩地为南戏在明代的流行提供了明证。金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先后媲美,而传奇之盛实际上集中于晚明,这个观点概括了古代戏曲发展的基本趋势。但这样的概括过于简明扼要,容易引人误入歧途。
民间南戏由于流传和创作的过程很长,难以确切地指明它的年代而被忽视。人们通常说的宋元南戏,实际上并不限于宋元,在整个明代它的创作并未衰歇,它在民间的演出和流传也在以同样的规模继续。只是由于文人传奇的兴起,南戏失去了昔日的垄断地位,而使人误认为它已经衰落。
人们对明代戏曲的第三个误解,是所有的传奇都为昆腔而创作。传奇的繁荣发展,迎来了晚明直到清代中叶,中国戏曲舞台在金元杂剧之后的又一个昌盛时代。昆腔艺术家对《琵琶记》、《荆钗记》、《玉簪记》、《牡丹亭》等唱腔艺术世代累积的创造和发展,已使它们成为我国民族文化艺术遗产中的瑰宝。但它们原本并不为昆腔而创作,昆腔对它们的移植和加工是后来的事。更确切地说,所有的南戏和文人传奇都是南方各声腔的通用剧本。就戏曲创作而论,并不是从梁辰鱼的《浣纱记》开始,所有的传奇都有意为昆腔而创作。昆腔作为民间南戏的一个分支,曲律由宽而严不可能一蹴而就。它经历了漫长的完善过程,即使是苏州曲家也不例外。
事实证明,《浣纱记》以后,并没有很快就出现昆腔在戏曲舞台上独家称雄的局面。还是以《金瓶梅》为例——全书没有一次提到昆曲或以笛子为主要伴奏乐器的南戏中的其他声腔。即使第三十六回写到在北方深受欢迎的“苏州戏子”,那也不是昆腔演员。在汤显祖和沈璟时代,昆腔和其他地方剧种同时并存,同一曲本既可以由昆腔演出,也可以由其他剧种演出,至多经过简单的适应性的改编。这可以看成由创作本到演出本的必经步骤,即使现代话剧也不例外。南戏和传奇的区分并不取决于它们的唱腔,不是只有南戏为四大声腔所同时适用,传奇则只适用于昆腔。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南戏是民间戏曲,而传奇是文人的改编和创作,二者所有不同的属性都由此产生。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发展经过话本这一阶段,现在已成定论。但话本不能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宋之话本》中那样望文生义地被解释为说话人的底本。他显然是以自己所熟悉的教员的讲稿作为比附。这个解释难以同绿天馆主人的《古今小说叙》所言相吻合。话本就是供人阅读的写本。说话人师徒之间口口相传,不需要什么底本。然而,几十年来人们对鲁迅的说法信从不疑。人们对话本的另一个看法,是以为话本就只是散文,没有诗词韵语,一旦有诗词韵语,就变成了拟话本。这恰恰同事实相反。最早为说话艺术提供详细记载的文献资料——南宋的《醉翁谈录》,在甲集卷一《小说开辟》中就直截了当地说:“吐谈万卷曲和诗。”《水浒传》第五十一回对白秀英说书的描写,则可说是一个具体的印证。因为有诗词韵文的插唱,话本又称为词话。一物二名,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讨论明代“四大奇书”的时代和作者,必须打破一个陈腐的观念,即以为它们是个人作家一次完成的作品。
署有南宋绍兴十七年除夕自序的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卷五,记有“霍四九说《三分》”,可见以三国为题材的说书那时已经水平很高。至治(1321-1323)新刊《全相三国志平话》,可说是三国平话中最早的一个雏形,《三分事略》则是它改头换面的一个赝本。从史实走向小说,三国故事在晚唐北宋间的这个过程相当缓慢。《三国志平话》着力描写刘、关、张,取法于《水浒传》写英雄,两个不同的题材在长期流传过程中曾经相互交流和影响。由平话本的五万五千字加工发展成约五十八万字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在嘉靖元年(1522)刻印,宣告三国故事正式成书。书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贯中编次”。据此,罗贯中是多次增订中的关键人物,最后由他写定。但嘉靖元年刻本,在某种意义上说可能只是抽象地存在,原书没有流传至今。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的《三国演义》,已在三百年来的流传中作为定本被人们接受。被窜改的李渔序和冒名金圣叹的序不会出自毛氏之手。可见,现在所见的《三国演义》,在毛氏之后又经过后人的增订。
号称四大奇书的另外三部,无一不经过同《三国演义》差不多的演变过程,这是中国小说史最基本的事实之一。故事流传早而成书却很迟,在世代艺人的流传中逐渐成熟,最后由某一文人改编写定——本书把这种类型的中国古代小说和戏曲称之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它们都是在长期流传过程中经过不断的加工整理而成书,其优点和缺点,都很难由某一个天才或非天才的作家来负责。
《水浒传》故事初次成型当在元代。因为故事形成和成书是两回事,成书应迟于故事形成。《金瓶梅》原是《水浒传》系列故事的一个分支,后来它由附庸而成大国。《金瓶梅》和《水浒传》一样,都是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形成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带有宋、元、明不同时代的烙印。《水浒传》的写定比《金瓶梅》早,但它们的前身——“说话”或“词话”的产生,却很难分辨孰早孰迟。与其说《金瓶梅》以《水浒传》的若干回为基础,不如说两者同出一源,同出一个系列的《水浒》故事的集群,包括西门庆、潘金莲的故事在内。从某些方面看,《水浒传》中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故事比《金瓶梅》早,从另外一些方面来看又可能相反。这是成系列而未定型的故事传说,在长期演变过程中出现有分有合、彼此渗透、相互影响的正常现象。
现存小说《西游记》一百回本,以华阳洞天主人校、金陵世德堂本为最早。它也经历了漫长的演变累积过程。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他的弟子慧立和彦悰编写的《大唐慈恩三藏法师传》,为《西游记》的某些情节提供了虚构的依据。《西域记》和《法师传》若干史实的记载和宗教信徒的幻觉,客观效果同小说的艺术虚构相似。大约在玄奘身后六个世纪,杭州中瓦子张家刊行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现存最早的以取经为题材的民间艺人传本。《西游记》和《封神演义》孰早孰迟,迄今尚无定论。假使两者的成书年代都已确切地考察清楚,雷同的片段也未必都是迟的因袭早的。因为两书都经历了长期流传过程,包括民间艺人说唱阶段在内。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如果它们在形成过程中彼此渗透,成书早的作品也可能受到成书迟的作品的影响,成书迟的作品的产生和流传,反而比成书早的作品更早。
中国古代个人创作的长篇小说,在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世代累积型长篇小说带动下兴起。终于脱颖而出的个人创作和早已存在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之间,还存在着同时兼有个人创作和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双重性质的作品,同一作品所包含的两类性质可能强弱比例很不相同,有的两者比例不相上下,有的则可能三七开或是相反。在个人创作兴起之初,很少存在绝对的纯而又纯的个人创作。我们说某一作品是个人创作,只是就大体而论,正如同无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成分怎样大的作品,它都至少有一两位或更多的个人之手把它加以编集和修订。据此,我们把《绣榻野史》以及时代相近的一些作品,作为中国古代个人创作长篇小说兴起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