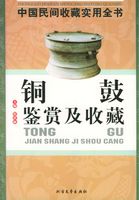现在所见可信的中国长篇小说个人创作,以吕天成的《绣榻野史》为最早,它成书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前后,是对《金瓶梅》的拙劣模仿。在《金瓶梅》中,富有现实意义的对社会黑暗的揭露和若干色情片段同时并存,《绣榻野史》却除了色情之外别无所有,全书说不上有什么艺术性。如果说《红楼梦》表现了《金瓶梅》对后来小说的积极影响,那么《绣榻野史》却相反,是《金瓶梅》恶劣影响的一个实例。此后依然有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长篇小说继续成书问世,但个人创作已经出现,并正在逐渐加强它的势头。要着重说明的是,《绣榻野史》在上述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潮流中出现,它不是孤立的事物,领先并开拓个人创作长篇小说新时代的,不只是某一部小说。
《于少保萃忠传》已具有个人创作的明显特色,但它成书时代较迟,在1611年之后;《钱塘湖隐济颠语录》是隆庆三年(1569)刊刻,它类似个人创作,实际上是世代累积民间传说的汇编,“作者”很少有加工和润色。这两部作品都属于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一个最大分支,即史传体演义小说。
所有这类小说都从借鉴《三国演义》起步,从某一角度看,它们都是《三国演义》成功或不成功的模仿者。前者过实,后者则趋近怪诞,都没有像《三国演义》那样在虚实之间保持恰当的比例而取得成功。较有成就的首推《新列国志》和《隋唐演义》,前者有冯梦龙的加工,后者有褚人获的改编。
从余邵鱼、余文台到冯梦龙,他们作为出版商而从事改编,以至一定程度上创作历史小说的现象引人注目。模仿、因袭和引用同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虽然相近,却不是一回事。在模仿、因袭和引用的后面可以影影绰绰地看出个人作家的创作活动。
在从模仿起步的较早的个人创作长篇小说中,引人注目的还有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1597),简称《西洋记》,共一百回。前十七回以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为主,个人创作的成分虽然不能排除,但只占次要地位;后八十三回则以模仿为主,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成分只占次要地位。全书既有前后一致的风格,也有各部分不太一致的表现,可能这正是各段故事来源不同所留下的痕迹。赵景深说《西洋记》的作者“好像写童话一样”(《中国小说丛考·三宝太监西洋记》),实际上这不是童话,而是世代累积型民间说唱文学的特征。
中国古代短篇小说有两个源头:文言短篇小说可以溯源于史传体和笔记小说,它们从《史记》发源,较多地以文言或接近文言的语言写成,作者是文人。白话短篇小说在明代独步天下,但从明初瞿佑的《剪灯新话》开始,文言短篇小说仍以微弱缓慢之势,一脉不断地发展,不仅成为通向清代《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的桥梁,也为兴盛于晚明的文人拟话本提供了大量创作素材。如晚明最出色的文言短篇小说家宋楙澄(1569-1622),他的《九龠集》中的《珠衫》、《负情侬传》原为纪实之作,而假托根据传闻写成,复经无名氏之手,演变为“三言”中的名篇《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虽然这仅只是富有代表性的一例,但足见文言小说对白话小说的影响,是明代短篇小说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作为大型文言短篇小说集,王世贞所编《艳异编》代表了另一种类型,它和白话短篇小说的题材也有互见现象。至于《情史》与“三言”、“二拍”的关系,更是为人关注。
白话短篇小说同长篇章回小说一样,在话本的影响下出现,它们和文言短篇小说的关系,不仅表现在大量从中取材进行白话改编,还在于它们中的一些作品本身就有较重的文言成分。如《通言》卷十的《钱舍人题诗燕子楼》、卷二九的《宿香亭张浩遇莺莺》以及《恒言》卷二四的《隋炀帝逸游召谴》。也可能它们都是宋元旧篇,成书较早。文人拟话本繁荣于晚明,是以话本为范式的短篇小说,为人们公认的拟话本这一指称,正是对这种形态的描述。就总体而论,冯梦龙的“三言”是以编纂宋元旧篇和明代流行的说话故事为主的话本小说集,其中可以确定完全是编者冯梦龙个人创作的,只有一篇《老门生三世报恩》,从这个意义上看,它又是文人拟话本的开始。与“三言”相反,凌蒙初的“二拍”在整体上是较典型的文人拟话本,陆人龙的《型世言》则由拟话本向个人创作跨进了一步。
白话短篇小说大盛于晚明,这是因为它雅俗共赏,适应了大众文化的需求,并给传播者带来了不小的经济利益。作为大众文化传播的使者,编纂者、创作者和出版家,更或一身兼几任者如冯梦龙,他们在其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虽然道德说教是这类小说共同的宗旨,但广大的巿场和出版效益无疑才是他们传播这类小说的重要动力。巿场运作手段在他们那里已经比较成熟。《古今谭概》初刻时遭遇冷落,改名为《古今笑》后购者踊跃,“初刻”出版后“二刻”应巿场之需草草推出,不过是其中的一二例而已。对这样的现象,我们今天并不难以想象。
晚明还有一类近年来被人们称之为中篇传奇小说的作品。它们以并不古奥的文言文为语体,篇幅长于短篇而短于长篇,被收载于明代坊间所刻的多种通俗类书中,作者则很少可考。现在可以追寻的最早作品,是元代旧篇《娇红记》。但《娇红记》显然不是纯粹的旧篇,而带有明代的气息。
在它的影响下,晚明出现了《吴生寻芳雅集》、《龙会兰池》、《联芳楼记》、《钟情丽集》等一批同类小说。其实它们写的多半是才子佳人的世俗艳情,并没有多少传奇色彩,其表现形式则介乎话本和拟话本之间,正如它们的作者可能也介乎文人和艺人之间。
如上所述,小说戏曲在明代文学史中虽占有独特的地位和很大的比重,但并不意味着因此而可以抹杀传统诗文在明代文学中的成就和意义。
然而不轻视它是一回事,对它的实际成就能否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是另一回事。对明代传统诗文进行纵向比较在情理之中,但我们既不赞同由此而产生的对它的片面否定,也要尽可能避免走向一些人对它全面肯定的另一个极端。事实上,明代诗文中有许多值得玩味或重新探讨的问题。
明代是通俗文学洪流滚滚,而传统文学相对衰落的时期。其实这种情况并不始于、也不曾中止于明代。客观地说,明代不过是宋代以后传统文学衰落史上的一环。在这样的环节中,的确没有产生像李、杜、韩、柳那样的诗文大家,但这只是事物的一面。另一方面,即令在寂寞冷落的衰季,局部也会出现蓬勃生机,甚至产生几个名家,这是明代传统文学的又一个客观实际。再者,从导复古的前七子领袖李梦阳,到反复古的公安派领袖袁宏道,明代传统诗歌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向民间诗歌学习,这表明通俗文学与传统文学不仅不是对立的,而且传统文学往往主动地向民间学习,从另一个途径促进自身的发展,这也使我们必须从新的视角看待明代传统诗文。
宋濂、刘基和高启一向被作为代表,用来证明明初诗文的繁荣,但实际上他们都是由元入明的文人。宋濂以文章华国,载道颂圣,成为新一代正统文学的典范;刘基、高启的诗歌,则无复在元时风标。这时期名士鲜有善终,包括宋濂和刘基。以高启为首的吴中四杰皆死于非命,曾是诗文昌盛之邦的吴中文坛气象萧条,这是明初政治整肃的又一结果。吴中四杰入明后虽未辍于咏歌,但气韵格调蕴含着与朱明王朝开国盛世不和谐的悲音。需要区分由元入明的文人创作在精神意象上与此前相比有什么不同,而不是混为一谈;需要探究这时期文人身后的政治整肃对他们的创作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而不只是就作品论作品。
此外,明代文学史上引人注目的文学复古运动,在明初即已掀起风潮,却往往为人忽略。作为整个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前浪,明初文学复古主要缘于传统文学自身发展的因素,同时也与这时期文人对新王朝盛世的认同有关。明初文学蔚然称盛,流派众多,复古也有种种观点和表现。
但由于同处一个大环境,这些主张在多元化中呈现出趋同现象。明初文学复古的理论、实践、争议和弊病,对中晚明文学复古运动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永乐以后,随着由元入明诗人的逝去,诗歌进入了明诗时代——这个时代以“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官僚集团及其诗风的形成为始,虽然“三杨”诗风的性质一直没有得到切实的定位,它与杨士奇复古理论的关系也没有引起人们注意。“三杨”诗风在仁、宣两代承平盛世下出现,历来以空虚庸俗为人诟病,其实它的致命之疾不在歌颂太平盛世,而在千篇一律,缺少性情;“三杨”不能算作一个文学流派,而是一个官僚群体;他们的诗是君臣、同僚之间的唱和,算不上文学创作。“三杨”不像宋濂和刘基那样,以元朝旧人的身份,带着乱世的失意和对亡元的深刻体会进入明朝。
他们可说是明王朝造就的人才,既没有对元末弊政的感受,也没有丧乱的经历,在太平时势中成为内阁官僚,并导了承平盛世的馆阁诗风。
李东阳和茶陵派崛起于传统文学衰颓、通俗文学尚未形成气候之时。
李东阳在明代政坛和文坛上所处的特殊地位,使其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作为馆阁重臣,他在政坛、文坛上的地位与“三杨”相似,但他的文学成就以及对当时和后来的影响,则非“三杨”所能企及。
他从理论上对馆阁诗风进行了全面总结,也有相当数量的馆阁制作。但我们今天要强调的却是他的另一面:他是明王朝造就的第一个有广泛影响的诗人,他的文论具有强烈的道统色彩,在诗歌创作上则主张学习汉、魏、盛唐。他作了一百首古乐府,又强调内蓄情志(《王城山人诗集序》、《赤城诗集序》),外兼比兴(《怀麓堂诗话》)。他三次走出馆阁,创作了不少实践其诗学观的优秀作品,它们是对“三杨”诗歌真情无存、兴象丧失弊病的有力反拨。前七子尊崇汉魏盛唐,显然来自李东阳的影响;他们的乐府诗“以我之情,述今之事”(李梦阳《驳何氏论文书》),说明李东阳的影响是积极的。李东阳对明代诗歌发展的推动,显然要大大超过他对馆阁诗风的因袭。他以馆阁重臣的身份执文坛牛耳近半个世纪,其故旧门生形成了活动持续数十年之久的茶陵派,对纠正馆阁文风,开拓明诗发展道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弘治、正德年间前七子登上文坛,文学复古运动继续发展,并出现了反对派,形成长达百余年的复古与反复古运动。作为明代文学史上第一个不依赖政治地位,而以自己的创作形成极大影响的流派,前七子对李东阳和茶陵诗派有所发展。《明史·李梦阳传》说李梦阳独讥李东阳萎弱不能算错,但他们之间并不是敌对的关系也是事实。这个流派以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为旗帜展开复古运动,结果由矫正时弊的初衷出发,在某种程度上反而使积弊更深;他们的乐府诗以面向当代社会现实为主旨,应该加以肯定,但其文学理论以宗法秦汉盛唐自设门限,却没有多少新意。对这些情况不作深入的探究,难以对前七子的文学复古作出符合实际的评价。
从嘉靖二十八年(1549)李攀龙、王世贞、谢榛三人初会于北京,到万历十八年(1590)王世贞病逝,后七子在晚明文坛活动长达四十年之久。
这个流派的形成和嬗变,是晚明文学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作为李攀龙之后的文坛领袖,王世贞自身的文学创作实际与他所获得的盛名并不相符。从通常的视角不能够解答后七子为什么在晚明兴起,并保持如此长久的地位这个问题,必须着眼于他们兴起的政治背景。这个流派的形成,实以不满严嵩专权为共同的政治立场。王世贞对严嵩的抗争以及他在作品中对严嵩和当代政治黑暗面的种种批判,是他在当时享有盛名的真正原因,而王氏父子和后七子其他成员在严嵩当权时的遭遇,也在无形中提高了他们的声望。诸子初集时谢榛与李攀龙就在诗歌创作理论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分歧主要是在复古法式上活用还是死学的问题,这与前七子中李梦阳与何景明的分歧有相似之处。然而不管他们之间的分歧有多大,其复古的方向是一致的。后七子中的一些人在模拟的格局中虽然有所突破,但文学创作总体成就并不高,这正是他们理论局限的反映。
嘉靖初年,以反对前后七子为出发点,王慎中、唐顺之导诗规盛唐,文宗欧(阳修)、曾(巩),掀起了反七子的浪潮,归有光、茅坤也是其中的重要人物,这就是文学史上的唐宋派。这个流派在时间上出现于前七子之后,延绵与后七子同时。他们的文学理论与前后七子相同而又相违:以复古的方式反复古,使他们在本质上均属复古派,只不过仿效的偶像和法式与前后七子有所不同罢了。唐宋派在理论上既继承了古文家道统的积极面,也继承了道学家的消极面。他们对“道”的重视并不意味着对“文”的否定。他们提明理、应世,包蕴了对现实的关注,而在以王阳明、李贽为代表的反理学进步思潮兴起之时推崇邵雍和曾巩,游移于天理和人欲之间,则是他们落后面的主要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