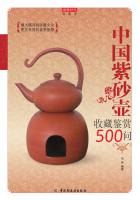“为人君者,行事自是光风霁月,墨氏一直为我大炎鞠躬尽瘁,恪守本分,将来的天子必定也会对墨家无比信任,恩宠不绝,阿诚你尽可安心。”
两人求学于贾和光门下时,偶尔谈及墨氏将来,都是殷谊这般安抚他那颗认为墨家或有隐忧的少年心。那时的殷谊遇事不避,直面挑战,胆大而心细,墨光远觉得这位齐王世子更担当得起光风霁月这四个字,却不料在太皇太后面前的败阵会给殷谊带来那样大的改变。
他看着殷谊收敛了态度,做了个在美色权势中陶醉放纵的太子,却暗中利用墨家商路勾结出权力网线,不动声色地将一切拢在自己掌心里。
有几个人知道,澹台太皇太后被逼下位来时,那几个带头慷慨陈词指责太后的御史和骤然反目的领兵镇将都有把柄落在皇帝手里?甚至是朝中大部分臣子的后宅家事、坐卧言行都逃不过殷谊的耳目眼线。
其实哪里来那么多本就存在的把柄呢?但殷谊却认为但凡是人就一定有弱点。一个人可以爱钱,却爱美人,或不爱美人,却爱诗书古董,就算这些都不为,还有沽名钓誉呢?而把柄,则是可以利用弱点生生地造出来的。
逼死老师的仇,同殷谊之间自小养成的情分,让墨光远选择了动用了墨氏的力量,然而殷谊所搭建出的一切,都不是当初他同墨光远描绘的模样,再没有什么光风霁月,即便有也只是表象。殷谊登基之后的大炎,无论宫中还是朝上都蒙上了一层权争谋夺的阴影。
执念太深,若不能成佛,便是要入魔了。天下之间,知道殷谊执念之可怕的人不少,但绝没有一路看来的墨光远这般深刻的感受,所以他才会在墨飞羽出生之后直接公开生下的是一子一女,只因他明白这孩子无论男女,但凡不是个瞎子聋儿,不是个白痴,就必然会被殷谊拉扯进权势漩涡。
即便……那天子只是为了成全自己的一份誓言一个执念,却也不会顾及这孩子真正向往的和顺生活,而是强硬地赐予。
伴君犹若伴虎啊!入了天子的眼,还有什么平安可言?若这孩子不足够聪明,没有十分的能耐,一旦老师的恩情有朝一日被消弭殆尽,等待一个没有自保之力又被圣眷宠坏的孩子的会是什么?退一万步讲,即便天子之恩一直维持到殷谊驾崩,谁又能保证新皇对墨飞羽还能继续宠爱绵延?就算是坐拥金钱无算的墨氏对自己氏族的将来,尚且不敢做下如此保证。
在久远的好几个前朝之前,那一朝的文帝梦见自己险些落水,一个拉宫船的黄头郎从背后撑住自己方才得救。后来竟真的偶遇爱那黄头郎,将其视为福星,一路提拔晋升至丞相,富甲天下无人能及。这人也十分感恩,皇帝腿上长了个脓疮竟毫不犹豫拿口吸吮脓液,而当时的皇太子尚且无法做到。
后来太子即位,这人被禁于府中,太子不允许任何人送他食物,生生饿死在堆积如山的金银玉石之间,那富贵家业也尽收归国有。
谁知今日恩宠不会是明日丧歌?这孩儿与他今生既然有父女之缘,他自然愿她当真能享一世富贵安乐,所以才打小将她当男儿来培育。需知一旦与权相关,其情势之惊涛暗涌,以后宅妇人的眼光只怕难以抵挡。
他不能指望女儿能自然而然长成澹台太皇太后那样目光远大的女人,只能不断强求。因为曾经在湍急暗流中挣扎的天子已然爬上了岸,却成了与那个被他击败的女人一样将人踢下暗流,冷眼旁观他人渐次没顶的人。
“至少……羽儿的确是个聪慧的。”楼凝烟久久才说得一句,她知道丈夫有的是玲珑心肝,日常里他总说是讨她的看法,到不如说是在借着同她谈话的功夫,整理着自己的思绪。
“正是,我看她是个有主意的,也算是拿定了方向不肯踩浑水。如今更觉悟了自己要干着身子上岸必须先识水性的道理,往后便是走一步看一步,如果有足够智慧,又得天意怜恤,合当能使得船到桥头自然直。你我的几个子女并没有羽儿的天资,我虽为人父,亦是存有一些私心,怕将来我墨氏中生出内乱来。届时只怕墨家平安还要靠羽儿……”
楼凝烟伸出纤纤玉指按在墨光远唇上,竟是不许他接着说下去。作为他的妻子,她太清楚丈夫身上的压力,要不是为了墨家,笑吟吟的墨次相只怕更愿意跟墨飞羽一个目标,富贵清闲的一世就好。然而墨光远到底是墨氏嫡系的当家,到底是族长,他的一切都跟墨家捆在一起,便也难免有不得已的作为。
墨飞羽若足够强,有朝一日可能会成为墨家未来的倚靠。墨飞羽若盛眷不衰,到底也有墨家的一份好。这或许让墨光远的父爱变得不那么单纯,但在楼凝烟看来,女儿好便墨氏好,从另一角度而言,却也让墨飞羽多了墨家这个强大支撑的底气,已经是墨光远能够做到的最好的打算了。
“不许你妄自菲薄了那份为人父亲的心意,羽儿亲爹已不在人世,她如今只有你一个爹。养儿方知父母恩,等她年岁渐大,便会知道你的用心了。”楼凝烟的话将墨光远的一声长叹堵在喉间。得妻如此,夫复何求?墨光远忍不住将妻子拥在怀里摩挲许久,方又接下去整理起自己心头盘算。
“我想再有三四年,羽儿十二岁时,便将那些人手都交给她,她要天高任鸟飞,身边总不能没有可用之人……”
声音渐渐低了下去,墨光远和楼凝烟夫妻盘算起数年之后的安排,此时还误会着父亲,觉得将自己当男孩养育是为了在圣人眼前争人气的墨飞羽,则半个小身子完全趴在桌上,拿墨笔一个又一个圈定眼前写在西南麻纸上的词儿。
细细看那纸上写着的竟然是“圣人”、“皇后”、“长公主”字样,墨飞羽圈好之后,又在不同的圈之间联线,写上一些蝇头小字作为关系注解,分明一行行是刚才她同墨光远之间得出的结论。
写了看,看了写,添添补补写满了一张又拿另一张来写,一直到夕阳洒金,画彩进屋来叫她为止。墨飞羽起身又看过一遍,将纸丢进焚练字纸的铜盆烧了,这才带了人赶着去父母那面与家人同吃晚饭。
墨家开起餐来,仍旧是一片你说我讲的温馨和谐景象,而宫中蓬莱殿西清辉阁里掐下的繁花插得到处姹紫嫣红,内里的气氛却似凝固了一般。整个阁中静谧非常,只有安定长公主那只水葱一般的手,在如冰似玉的翠色越瓷双耳瓶中满插的鲜黄迎春花上轻轻拂动。
殷迎春今日淡扫了娥眉,锥髻上簪着一朵新开浅紫芍药,外披着软红大袖明衣,下穿白底暗百蝶舞长裙,足踏一双石榴红缀东珠翘头软锦鞋,樱唇用鲜红口脂点成“露珠儿”式样,似含着一滴浓烈刺目的血,咄咄逼人地娇艳。
她樱唇微微轻启,问道:“阿赭,你可有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