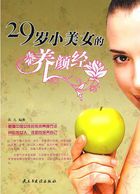“处处为舞台扮演着想,抑且为伶工预留地步”——这都是“他种传奇所不曾注意的事”。周贻白先生分析《桃花扇》剧目这种舞台演出艺术上的种种“排场”,也说明他对剧目在舞台演出中这类信息的关注。这对传统剧目创作与舞台搬演中的脱节状况,也是一种告诫。事实上,中国传统剧目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这种浸润于士大夫文人传统中的文学性很强的作者,与广大戏剧的普通观众和演出者之间的错位。这种错位,往往导致传统剧目的剧本创作缺失舞台性,一些有趣好玩的片段,反倒成为舞台演出的宠儿——“折子戏”。换个角度,从戏剧形态的角度看,颇为畸形。这其实是一种无奈之举。而有的折子戏,比如《春香闹学》,拿欧阳予倩的话说,都是跟本剧主干脱节的情节,是主干剧情的累赘,结果反倒成了重头戏。
周贻白先生也早就看到这一点,他在分析《桃花扇》剧目的上述四条“凡例”时说:这四条,在传奇的旧套里,都可说是新例,而在舞台上,却最合于搬演。因为伶工偷减词句,增加说白,已为戏场通例。
这种“偷减词句,增加说白”的“戏场通例”,一方面因着舞台演出者的“俗态恶谑”,一方面也更是因为具有士大夫文人传统的剧作者“只知自己发挥,不会顾及上演时情形”。两方面的短处合一,造成了这一弊端。周贻白先生就此论说道:其增白减曲的原因,便是表示剧作者命笔时,只知自己发挥,不会顾及上演时情形。一经粉墨登场,不免大感枘凿,乃不能不就事实加以增删。伶工们虽有充分的舞台经验,其去取是否恰当,便很难说,也许弄得失枝脱节,与原本所欲表达的意义完全不符,并非没有的事。
周贻白先生真的是读懂了孔尚任,对其内行的剧本形态予以较高的评价。他特别说明其“上演于舞台的通盘筹算”对于戏剧编剧的重要性,这是具有一定导演意识的编剧才能做到的。因为“上演于舞台”需要的不仅仅是文学性的思维,更是戏剧性的思维。孔尚任的时代已经是昆曲开始衰落的时代,周贻白先生对这个时代的昆曲剧目《桃花扇》作者的苦心也有所洞察,真的可谓孔尚任的知音:孔氏能看到这一点,足见其篝灯制曲时,已作上演于舞台的通盘筹算,虽非有心振兴“昆腔”,实欲弥补其已往的缺憾,而间接予以提携。
四、《桃花扇》剧目的文辞和音律
《桃花扇》是作为昆曲剧目出现的。周贻白先生分析《桃花扇》时,兼及到对昆曲及其存在的问题的分析,应该说这方面的分析更是入木三分。他的一些认识,到今天看来,依然很到位,而且他所提及的那些弊端,似乎依然还在。戏剧不够大众化或平民化,依然是当下剧目的弊端所在——没有“在民间具有深厚的基础的缘故”:换言之,“昆腔”的失败,首先是“腔”。词句的艰深,虽然也是重要原因,这使得看剧本的编制若何。如以《活捉》一剧为例,其所以能够流行,便只在关目的熟识和本事的流行,在民间具有深厚的基础的缘故。
可以说,20世纪以来的大众化、平民化潮流对戏曲的影响看起来似乎很大,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戏曲还是在传统中坚守下来。在20世纪初中期,中国戏曲曾经有过很多“改良”,其戏剧形态也有过多种多样的试验和变化。但是,戏曲剧作基本还是没有脱离文人腔文人调,正如周贻白先生多年前就指出的那样:除少数对词曲下过功夫的人能够知其佳处所在外,一般伶工们便未必完全懂得,普通观众则更不必说。
周贻白先生进一步分析道:
如今日向在风行的《春香闹学》(第七出《闺塾》),在舞台上带唱带做,何尝不有声有色?可是,百分之九十的观众,对于词句未必完全听清。除非他熟读《牡丹亭》,或带了曲本来参看。
连最通俗的《春香闹学》尚且如此,更别说那些文绉绉腔调的剧目了。但是,这个问题也已然成为戏曲剧目创作中的悖论:失却了这些文人腔调,那还是戏曲吗?周贻白先生看来也没有解决之道,虽然他依然看到了这样的事实:戏剧非专为唱曲而设,不管粗唱细唱,总须以剧本内容为转移。戏剧的声腔,无非为表明意绪,或诉述情由,不比茶酒之余,背墙面几地曼声低度。“水磨腔”、“冷板曲”,固由此而传,但经施之戏剧,舞台空气统因久唱而散漫,观众情绪亦因久唱而缓弛,“昆腔”之失败,实因其太耐唱了。《桃花扇》之能延续“昆腔”将终的命运,这一点实具有极大关系。排场之紧凑在此,关目之明白亦在此.至于文章之畅适与否,殊不在篇幅之长短及曲调之繁复,善编剧者,当明其理。
这番话,今天读来依然很到位很生动,且入木三分,看到了中国传统戏曲形态的关键所在。但从骨子里看,周贻白先生也是个传统文人,不能不欣赏《桃花扇》剧目中那些文气十足的文辞:且全本《桃花扇》,文笔极为酣饱,“气足神完”,原非自诩。其“试”、“闰”,“加”、“续”各出,看来虽似闲笔,其间实寓深意。以后张道所作《梅花梦》衍小青事,即全仿此种排场。
他还进一步举例说明《桃花扇》剧目文本中这种文辞及音律上的高妙之处:论文辞和音律,《桃花扇》一剧,似乎没人挑剔。虽不必即为尽善尽美纷表征,而论曲者不敢轻于置喙,亦可见其造诣不凡。恤就畅适而霄,其中亦有不少佳曲。如第十一出《投辕》,柳敬亭唱:
【北沽美酒带太平令】俺读些稗官词,寄牢骚,稗官词,寄牢骚,对江山喫一斗苦松醪。小鼓儿颤杖轻敲,寸板儿软手频摇;一字字臣忠子孝,一声声龙吟虎啸;快舌尖钢刀出鞘,响喉咙轰雷烈炮。呀!似这般冷嘲、热挑,用不着笔抄、墨描,劝英豪,一盘错账速勾了。
事实上,中国戏曲的生死之悖论,或拿捏之难度,都在这里:文人腔调没有了,它或许也就没有了;文人腔调太多了,它或许也就死定了。周贻白总结道:戏剧亦不外表现人生,传达情绪。……专管拍几案唱曲子的人,自然做不出排场上的好梦,“昆腔”之终于没落,自非偶然的事实了。
当然,从历史文化遗产的角度来看中国戏曲的这些风貌,那又是另一番光景了。
五、浅析中国戏曲史论及创作的立论基础
细细读进去,周贻白先生的《桃花扇》剧目分析似乎还有些缺失——比如对剧目主旨,人物及人物关系,剧情、剧情结构及中心动作等方面的分析。显然在当时的状况下,这些戏剧剧目分析所必需的要素,还没有被戏曲史史家所充分关注。特别是有关剧目主旨的分析,这里涉及有关中国戏曲史论及创作的立论基础的重大问题,值得一提。
解析剧目的创制和演出,是戏剧史的治史基础。剧目是治史中最主要的分析评判对象。其中尤以立论基础最为关键。现代中国戏曲史的治史和创作立论,颇受传统士大夫“以国为本”的意识形态所左右。中国传统戏曲剧目多以“精忠报国”为旨趣,以道德评判和政治至上为目标来创作、改编或评判剧目。《桃花扇》更是其中的登峰造极之作。这一剧目以爱国忠君为要旨,推政治道德到极致,直接无视人性本来,蔑视人间情爱,其结尾处的一段戏甚可说明这一特色。而现代史论之所以现代,恰恰是要跳出这样的局限,深掘剧目中的各种要素,讨论其观念意识形态,尤其是在其立论的基础方面,予以深入的分析。
从这个角度看,周贻白先生在“以人为本”还是“以国为本”的戏曲史治史立论上有所游移。一方面他已经有相当的现代意识,对传统的“正统”观念有所警觉,并已经开始关注人的因素,尤其是下层人物及角色在戏剧创作中的境况。但另一方面,由于受到特定时代和政局的左右,身陷其中,难以自拔,使其对《桃花扇》的剧目分析未能彻底跳出传统窠臼。这种游移,让他未能展开对《桃花扇》的深入剖析,似乎只触及到一些表层现象,而不能深入一探中国传统戏曲的深根。
一部剧目的结尾处往往是剧目中心动作或主题的最高体现。《桃花扇》的结尾就特别能说明其结症的所在。孔尚任《桃花扇》比较啰唆,为了不失其原来的风貌,也为使该剧目的中心动作能大致衔接,笔者尽量多摘录了一些,以便规避“断章取义”之嫌。下面就是该剧目结尾中一段重要的高潮戏:
[生遮扇看旦,惊介]那边站的是俺香君,如何来到此处?(急上前拉介)
[旦惊见介]你是侯郎,想杀奴也!……
[生指扇介]看这扇上桃花,叫小生如何报你!……
[生、旦同取扇看介]
[副净拉生,老旦拉旦介]]法师在坛,不可只顾诉情了。
[生、旦不理介]
[外怒拍案介]呔!何物儿女,敢到此处调情!(忙下坛,向生、旦手中裂扇掷地介)我这边清净道场,那容得狡童游女,戏谑混杂!
……
[副净]侯相公住在弟子采真观中。
[老旦]李香君住在弟子葆真庵中。
……
[生]待咱夫妻还乡,都要报答的。
[外]你们絮絮叨叨,说的俱是那里话!当此地覆天翻,还恋情根欲种,岂不可笑!
[生]此言差矣!从来男女室家,人之大伦,离合悲欢,情有所钟,先生如何管得?
[外怒介]呵呸!两个痴虫,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
[生揖介]几句话,说的小生冷汗淋漓,如梦忽醒。
……
[生]是,大道才知是,浓情悔认真。
……
[旦]是,回头皆幻景,对面是何人。
……
[外下座,大笑三声介](唱)【北尾声】你看他两分襟,不把临去秋波掉。亏了俺桃花扇扯碎一条条,再不许痴虫儿白吐柔丝缚万遭。
(念)白骨青灰长艾萧,桃花扇底送南朝;不因重做兴亡梦,儿女浓情何处消!
可以看到《桃花扇》结尾高潮处,将小小的桃花扇承载了何其重大的主题宏旨——政治、社会和伦理观覆盖了人性人情和常识常理。这位“大笑三声介”的“外”,不是作者又是谁?他把“桃花扇扯碎一条条”的快活,恐怕就是前述士大夫传统“以国为本”——“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巨手,扯碎“人”的个体性、主体性和独立性的快活。他大义凛然的“呵呸!”一声,怒斥那两个割不断“花月情根”的痴虫:“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在这一连串如雷贯耳的排比句轰炸下,不正是中国人个人的灵魂和肉体、欲望和精神的战栗么?“以国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恐怕就是这一正统思想意识形态的基础立论。
那个年轻而充满欲望和活力的“生”,虽然也挣扎着说:“此言差矣!从来男女室家,人之大伦,离合悲欢,情有所钟,先生如何管得?”可先生就是管得:“再不许痴虫儿白吐柔丝缚万遭”,“桃花扇底送南朝”。一把小小的桃花扇,却是断送南朝的祸根——政治、社会和伦理观覆盖了人性人情和常识常理,将流作源,将外部事物作为人的生命和生活的全部意义和价值所在。最后,孔尚任《桃花扇》在国不将国的前提下,把侯生与香君安排出家了事。正所谓:“白骨青灰长艾萧,桃花扇底送南朝;不因重做兴亡梦,儿女浓情何处消!”
中国戏曲的基本立论就在这里扭曲,中国艺术的主体精神就在这里失落。这就是中国戏剧从古至今的“正统”思想及戏剧观。在这个“正统”的统摄下,一切具有个体性、主体性和独立性的思想文化和文学艺术都将被改造,都将被其“正统化”。
这种正统化的意识形态,在现代艺术观念和审美意趣中,恰恰是对人性的个体性、独立性、主体性的反动,是对人的生命和生活的扭曲。中国戏曲史史家及戏曲作者们,包括现代戏曲史先驱周贻白先生在内,尚对此没有深切的认识,这不能不是一大遗憾。这也应该是阻碍中国戏曲史治史立论和深入分析剧目的魔障。在20世纪早中期,一些现代戏剧家们就已经意识到这一重大问题,比如欧阳予倩就曾经在1918年明确提出:“中国旧剧,非不可存,惟恶习惯太多,非汰洗净尽不可。”他推崇以“人情事理”来立论的戏剧观,特别强调要根据“人情事理”来作为创作和剧论的基础。他对于“真戏剧”的憧憬是:“真戏剧”剧本“贵能以浅显之文字,发挥优美之思想。无论其为歌曲,为科白,均以用白话,省去骈俪之句为宜。盖求人之易于领解,为效速也。”
欧阳予倩所说的“发挥优美之思想”当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国为本”的思想。在这一点上,现代中国戏剧史史家们和创作者都还当共勉之。
(中央戏剧学院艺术管理系,10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