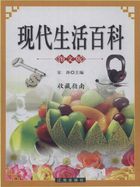晴窗忆昔
张光芳(江苏)
从1938年底到1946年初,除了中间有近两年时间(1941-1943)去了香港与桂林外,胡风在重庆战斗、工作、生活了五年。这是中华民族同仇敌忾抗击外侮的艰苦岁月,也是处在人生盛年的胡风携妻带子,在“天上有轰炸,地下有看不见的暗礁”的陪都意气风发、勇于斗争的岁月,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在斗争中求生存,在苦难中求欢乐,没有被炸弹消灭,没有被国民党击败,我们为民族解放战争尽了自己的力量。”的确,这里有胡风的欣慰,有胡风孜孜以求的事业、大展宏图的身影;然而,在与民族敌人斗争,与国民党斗争之外,文坛内部的论战、斗争,尤其是与解放区文艺思想、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摩擦,加之其性格的耿介、偏执,以及一定程度上的“非政治化倾向”与过于文人气,因之,“在混乱里面”诞生了重要思想的同时也埋下了祸患。
可以说,重庆是孕育并凸显了其思想观念、精神个性的历史性舞台,也是其个人命运的重要关口,正是在这里,胡风留下了思想的火花不少重要文本创作于此时(如《论民族形式问题》、《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方向》、《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等),不少他所看重的文学、理论文章编辑于此时(如舒芜《论主观》以及田间、路翎的文学作品等);尤其是凸显着胡风编辑理念与文艺观念的《七月》与《希望》也主要“活动”于此时,这两份颇有影响的同人杂志,正如有学者所言使“胡风集团”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公共领域”的一些特征,从而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但也由此留下了刺人的荆棘与恼人的杂草,得罪了人,埋下隐患,终至见风起火,酿成大劫。如果说此前的论战还多在文艺思想领域,重庆时期的论争则直接涉及到敏感的政治领域,这使得处于雏形中的“胡风集团”与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了尖锐的冲突和更为复杂的关系。作为建国后文坛第一大案,长达2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一度使数以千计的人人狱受审,其中不乏结识或来往于此时的同志;当然,也有不少其时的同志出于种种原因背道而驰,乃至反目成仇、倒打一耙——这种伤害往往是致命的。
对胡风而言,重庆,重庆,幸也非幸?
一、一片孤城万仞山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文化名流如老舍、郭沫若、巴金、冰心、梁实秋……从各地汇集到重庆,胡风也一路颠簸于1938年12月2日抵达重庆,“望着这从未见过的山城,那数不清的高台阶”,他在“总算是到了可以安身的地方”而长舒一口气的同时,立刻想到“今后会怎样?能如愿地工作吗?”为了一家老小的生计,胡风除了在北碚复旦大学代课,还要在国际宣传处兼职。开始时找不到房子,只能住在旅馆里,刚刚出生的女儿小风“半夜被老鼠咬得满头都是血”,直到翌年的2月2日才结束了两个月的旅居生涯。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胡风仍然满腔热情地投人到“文协”的工作中,而他“最中心的最急着要办的事就是继续编《七月》杂志”。《七月》创刊于1937年10月16日,出到第18期不得不停刊。虽然很辛苦,可是胡风一直努力坚持自己的办刊宗旨。在武汉时,胡愈之曾向他提议与《文艺阵地》合并出版,由他和茅盾合编,因茅盾去新疆了主要由胡风编,但是胡风不同意,认为“这两个刊物的性质和读者都不同,我无法合起来”。而此时要想恢复《七月》谈何容易!生活书店明确说不出,找胡愈之也没有解决;去求上海杂志公司的张静庐,未果;去找读书生活出版社的黄洛峰谈出版的事,他一人不敢做主。倒是沈钧儒老先生很关心此事,还说由他筹钱自办,胡风明白也不过是安慰自己而已。陷人了“深深的苦恼”之中的胡风不得不忍着“侮辱似的气愤”四处奔波化缘。后来有人告诉胡风华中图书公司的唐性天有意出版,虽然条件非常苛刻,等于白帮他编辑,可是为了《七月》的复活,胡风“无奈只能同意了他的条件”,他所痛惜的是“这时,它已搁浅快半年了!”
经过种种努力,《七月》终于复刊了,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复刊词《愿再和读者一起成长》。胡风希望能在《七月》上发表“有血有肉写出了真情实感的战地生活报告”,但对那类“空虚的所谓爱国主义的作品”明确表示了反感,认为这些“作者的感情并不是对人民性的生活内容感受到的内在的要求,而是一种浮在生活表面上的兴奋。或者,作品中的形象并不是他所深知的现实人物的性格溶化成的或生发出来的,而是为了表演某种概念而制造出来的。”
由于国民党的压制与挑衅,复刊后的工作绝非一帆风顺,而胡风也一直与国民党进行着顽强的斗争。1939年10月19日,胡风在纪念鲁迅先生的大会上怀着对国民党反动路线和反动措施的愤怒心情报告了鲁迅先生生平。国际宣传处有意整他,涨工资的时候故意剩下他一个。胡风一气之下辞职不干了,生活一下陷人困顿。后来他们又来找胡风,说是会计弄错了,“为了抗日嘛,希望老兄不要辞职”。重庆市卫戍司令部还给胡风下传讯的条子,恐吓胡风少说话少写文章。还有人传言胡风要加人国民党,加人了就可以当专任教授,胡风后来回忆说“问题的实质很明白,是想用复旦大学的专任教授这职位来拉我压我。我不能为这五斗米来和学阀党棍们打交道”。《七月》一、二期的合刊上,封面用的是王朝闻的墨画《被囚的民族战士》。之所以选这幅画,胡风自谓“是有意使广大读者知道,敌人是那么凶残,甚至用‘老虎凳’拷问我们的民族英雄。最近,从徐冰那里听说国民党又在蠢蠢欲动,经常有严重的摩擦。想到国民党只知残害自己人的反动行为,觉得用这幅画做封面很有揭发它阴谋的意义。”
作为抗日的大后方,重庆在集中了人力、物力资源的同时,也成了各种矛盾的聚焦地。除了抗日救国、与国民党斗争之外,由于自身性格、秉性以及历史渊源等诸多原因,胡风有意无意间陷人了与文艺界其他成员之间的摩擦与矛盾之中。
在“左联”的领导层,胡风一直很尊重鲁迅,深受鲁迅精神的影响,可是与周扬等则显得格格不人。鲁迅理解胡风的脾气秉性,对非议胡风者表示了反感:“胡风鲠直,容易招怨,是可以接近的”;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他说曾有人“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鲁迅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是不欢而散”。鲁迅对胡风的缺点也看得很明白:“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有些拘泥的倾向,文字不肯大众化”,然而他说“胡风并不‘左得可爱’,但我认为他的私敌,却实在是‘左得可怕’的”。1936年夏左翼文艺界内部发生的“两个口号”问题争论,更是把胡风推到了舆论的风口,这场文艺界内部的著名论争使胡风与周扬等人之间的成见与积怨日深,其后的不少恩恩怨怨便源于此。1939年5月24,周扬托人捎信,请胡风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做中文系主任。胡风“听了这话”的第一反应不是高兴,而是“有点吃惊:周扬怎么会想到请我?我应该答应吗?……”经过考虑之后,胡风还是留在了重庆。1943年从桂林返回山城后,胡风在冯乃超安排下见周恩来副主席,汇报了夏衍在香港的一些做法,“毫无顾忌的将看法都说了出来”,并且对在场的一向和夏衍不和的茅盾“一声不吭”感到不解。
在平常的交往中,胡风也一直坚持“实话实说”,不肯虚与委蛇,敷衍说好话,甚至常常让人下不来台。这里仅举两个例子。一次,宋之的请人观看其话剧《鞭》在重庆国泰影院的排演,胡风毫不客气地进行了批评。1945年12月22日,离开重庆前夕,在纪念萧红的大会上,胡风明明知道骆宾基有把萧红“美化成理想人物”的想法,还是照样说了“真话”:“萧红后来脱离了人民脱离了生活,毁灭自己的创作道路,应该把它当作沉重的教训。”这样自然令骆宾基非常生气,甚至认为他有意诋毁萧红。
但是胡风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怪物,他对国家、民族、家人、妻小都有着深切的爱。初到重庆时他因为儿子吃不惯当地的饭菜而难过,看到当地小孩子被大人长时期背在身上而担心对孩子的发育不好。他对朋友也一片真心。东平、柏山牺牲的消息让他“激奋难平”;洪深全家因为贫困交加而自杀,他深表同情。胡风和老舍更是在重庆结下了深厚情谊。接到撤退命令时,胡风到老舍的报馆打地铺,并毫不隐瞒自己的动向,胡风“相信他不是那种出卖朋友的人。后来,香港沦陷后听不到我们的消息,他和朋友谈话中提到我的时候,还掉了眼泪!他很珍视我对他的这种信任。”二人可谓是肝胆相照。
胡风对待普通的文学青年更是积极帮助,热心扶持。一个叫陈绪宗的学生因通信结识了胡风,到重庆后胡风经常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与他恳谈。青年诗人田间在当时遭到较多非议,虽然“说到田间,我们总是动辄得咎的,那罪名是‘乱吹’或者‘瞎捧’”但胡风仍然力排众议,积极支持他的创作。
他对以路翎为代表的“七月派”作家的创作的重要影响更是有目共睹。1940年,胡风在重庆第一次见到路翎,凭着文学的敏感和责任心,他给予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小青年热切的关爱与重视,认为“这是一个有着文学天赋的难得的青年,如果多读一些书,接受好的教育,是能够成为一个大作家的”,将他的小说《要塞退出以后》编入《七月》五集中,并一直关注路翎的创作,成为路翎文学道路上名副其实的领路人。始料不及的是,包括普普通通的陈宗绪在内,大多数人在日后都遭到牵连。
在1940年元宵节,胡风有感于时世,做诗一首以表达内心深处的各种感触:
几人欢笑几人悲,莽莽山河半劫灰。
酒酿值钱高价卖,文章招骂臭名垂。
侏儒眼媚姗姗舞,市侩油多得得肥。
知否从峰平野上,月华如海铁花飞。
他特意对诗句进行了解释,“酒酿”句指陪都重庆的社会生活;“文章”句指国民党对自己的不满;“侏儒”句指官僚们;“市侩”句指投机者们;最后两句指在北中国的山区和平原上,共产党正在领导着英勇的浴血游击战争。他对黑暗的憎恶与光明的热爱同样的深切,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文章招骂臭名垂”竟然一语成谶,在很长一段岁月中为他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二、不识庐山育面目
理论上的争论演化为政治上的把柄,这是时代的悲剧;而不擅处世却一直在风头浪尖,处处“授人以柄”,则是胡风个人性格的悲剧。这一点在其“重庆岁月”中得到凸显。要而言之,胡风的很多言行带有浓厚的非政治化色彩,这一点在当时是不被理解的。
晚年胡风在回忆录中对一些当时不太在意却演变为“事件”与“问题”的事情进行现场性的“历史还原”的同时,也进行了“剖析与反思”。郭沫若第三厅厅长被撤消后,由于周恩来的针锋相对,国民党在政治部下面设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胡风是成员之一。他认为冯乃超既然是文工会的党的负责人,“遇到和政治有关的个人行动上的问题,就可以问一问他,听听他的意见。但是文化工作的文艺问题上,除了个别的事如文协的工作,我有责任主动和他商量,听取他的意见外,我自己编刊物那是完全独立自主,不受任何人影响的。”
1943年,从桂林重返重庆的胡风在冯乃超安排下见周副主席。“他见到周副主席时,只简单地谈了从香港脱险的经过,没有把在香港的工作情况详细向周副主席汇报。他当时认为,既然我的重回重庆和回来后的行动都是在党的指示下做的,不会有问题,就没有必要向周副主席汇报了。”
张道藩曾经引茅盾、胡风、沈志远和钱纳水等人与蒋介石单独见面。轮到胡风时,蒋介石问了他的一些情况,比如懂哪种外文,在哪里留学,哪里人等,胡风做了简略回答,总共只有两三分钟。“我当时的心情是,他是统治者,我只是统一战线中的一分子。在这个原则下,他问什么我回答什么。不但没有想到说恭维的话,连谦虚的表情也做不出来。”而沈志远见了蒋介石之后则很兴奋,茅盾则对胡风说蒋介石当时问自己对《中国之命运》的意见,茅盾欠身回答:“委员长主持百年大计……”,胡风对此颇有反感,“怎么能这样说呢?”但是经过重重磨难之后,胡风终于明白“茅盾的回答是聪明的”,“愚蠢的是”他自己,“后来对周副主席提到这件事时,我只说了一句,‘我觉得蒋介石的表情像老太婆。’自以为其余的情况和心情可以不说的,其实我是应该向党汇报具体经过的。由于自己的自信和无知,十几年后又成了审问的重点!”
如果说这些事还有主观的原因,另外的一些事则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胡风为了工作和潘公展交往过几次,到了1955年成了严重问题,胡风被捕后,为了追问他和潘公展的关系,“审问了不下百余次!”1944年5月,有人介绍绿原去中美合作所做译员,他给胡风写信征求意见,胡风劝他不要去,就是因为这个问题,1955年被一口咬定是“中美合作所特务”,直到1980年才平反。
更为关键的问题是他对文艺理论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对党的文艺政策包括讲话精神进行了自己的理解,这一点被认为是有意与党的文艺政策、“讲话”精神以及“整风”运动作对。1938年10月,毛主席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提出要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同民族形式结合起来,延安和重庆文化思想界随即展开了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热烈讨论。向林冰提出“民间文艺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五四”时兴起的各种革命的新文艺只是“移植形式”,是从外国来的,不是民族的形式,对五四新文化传统进行质疑。这一观点引起了强烈争论。
胡风在1940年底编成了《民族形式讨论集》,把双方的文章分类编排起来,写了《论民族形式问题》的前记和《民族形式讨论集》的解题。又大约花费了三个月时间,写成了《论民族形式问题的提出、争点和实践意义》,写成后分成两篇,上篇为《论民族形式问题的提出和争点》,下篇为《论民族形式问题的实践意义》。在文章中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强调外来文艺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影响,并坚决捍卫这种新文艺的传统。向林冰虽然很快偃旗息鼓,但胡风却成了周扬、郭沫若、艾思奇等的论敌,并且由于其理论上的偏颇之处而被认定是否定无产阶级思想对五四文学革命的领导,反对毛泽东关于民族形式的理论。在后来的反思中,他说“在这篇文章中,我对一些党员作家、左翼作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论点都作了指名的批评,这就造成了很不好的后果。虽然我还是为讨论理论问题,但还是有人为此耿耿于怀,甚至到后来我出了问题被举国申讨时,揭发我在当时就骂尽了中国作家,这当然是我的一大罪状!”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重庆后,冯乃超组织了一次小型的座谈会。胡风发言时,提出“我们在国民党统治下面的任务应该是怎样和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和反动文艺以至反动社会进行斗争,还不是,也不可能是培养工农兵作家。”胡风后来终于明白“这个会当然是要看看大家对这部著作的认识和态度的。相比之下,我的态度就差多了。连蔡仪都还举出勤务兵提升为副官的例子,我却用‘环境和任务的区别’这一条说明了在国统区写工农兵为工农兵的困难性,一点也不懂得应该对此采取完全的拥护态度。我实话实说,结果,乡下的会不再开了,后来城里的文工会或曾家岩也许为此开过会,也没有邀请我参加”。他说:“虽然在当时,我认为在国统区是无法解决某些问题的,但我至少应该从我对党的态度和关系出发表态吧。我却没这样做,依然停留在旧知识分子独行其‘是’的老路上。这样,解放后就正式判定我为反对《讲话》了。”
长期以来,胡风一直倡导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这是胡风文艺理论的要点,也是他被诟病的基点:在1940年为吕荧译卢卡契的《叙述与描写》所写的《校完小记》上,他说:“在苏联,现在正爆发了一个文艺论争,论证底内容听说主要是针对着以卢卡契为首的‘潮流派’底理论家们抹煞了世界观在创作过程中的主导作用这一理论倾向的。但看这一篇,与其说抹杀了世界观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毋宁说是加强地指出了它的作用。问题也许不在于抹杀了世界观底作用,而是在于怎样解释了世界观底作用,或者说,是在于具体地从文艺史上怎样地理解了世界观底作用罢。”在《一个要点备忘录》,即文协小说晚会上的发言要点中,胡风再次强调作家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对客观主义、主观教条主义提出批评。
1945年1月,胡风在其主编的《希望》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舒芜的长篇哲学论文《论主观》。1月25日,文工会由冯乃超主持召开文艺座谈会,茅盾、以群等对《论主观》进行批评,对客观主义的说法很不满意。胡风在回忆录中说问题提到了周副主席那里,周副主席认为“‘客观主义’容易招误解”,问题暂时得到缓解。但胡风仍然在《希望》第二期上刊发了舒芜的《论中庸》,并在《编后记》中说本文是作者对《论主观》的补充,中心论点是个性解放。他天真地认为“我把我看到的‘错处’删去了一些”就行了,时人则把舒芜的文章同延安整风及《讲话》精神联系起来。在私下的谈话中,胡风也对整风运动表示了意见,如在与乔冠华谈话时,谈到整风运动,他说“现在出现了用教条主义反教条主义”,对乔所“表示的同感”感到“高兴”,“引为知己”。在这次争论中,他仍然天真地认为乔会支持他的观点。后来即1948年在香港创办的《大众文艺从刊》相继发表一系列批评胡风的文章,由之揭开了胡风受难的序幕。除了邵荃麟、胡绳、林默涵外,乔冠华也以《文艺创作与主观》一文赫然在目。
1946年初,胡风在即将离开重庆、前往离别八载的上海的前夕,向周副主席辞行。据胡风回忆,周恩来特意对他提到思想问题,“说延安反对主观主义时,我却在重庆反对客观主义……”,可是“愚不可及的我依然没有理会,没有重视,只觉得我的观点是针对文艺创作来谈的,与哲学和政治无关”。
就是带着这种固执,带着对新生活的无限向往和战斗激情,胡风依依不舍离开山城,踏上了新的征途。回首时他骄傲于战斗的经历;前瞻时他高呼着“时间开始了”迎接黎明的曙光,对身后即将到来的灾难则毫无知觉。
穿过漫长的磨难之后,一本《胡风回忆录》记录了他的思想历程,我们为其渗透于中的独立、伟毅的人格与品格感慨莫名,但同时,某些充满后知后觉、大彻大悟的叙述方式又颇让人心生感慨。我们不由追问,胡风与重庆的故事,以及胡风的其他故事,后人将以怎样的方式叙说呢?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胡风与重庆”已经化为重庆乃至中国人文历史中不可抹杀的一笔宝贵而催人深思的思想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