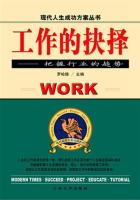王开志(四川)
散文是一种最能表达写作主体真实思想的文体,读者很容易从散文中把握作者的学识涵养与人格情怀。何立伟在不少的散文中经意或不经意、直接或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人生态度。在《生活的风景》中,他这样表白:“我知道,要跳脱开俗世的忧烦苦恼,并非一桩容易事。人沉迷在得失交关里,有如背负了一块大麻石,如何轻易就跳脱得了?好在这世上有另外的一种人,不求闻达,也不贪利禄,只将自己一颗平常心安顿在自足自乐的快悦里,也是生活的一道风景。”这里所说的“另外一种人”当然也包括了何立伟自己。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何立伟以小说《白色鸟》确立了自己的身份之后,便对文学充满了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执著。他的文学之路走得不急不躁,心无旁鹜,以文学悦己悦人,形成了独特的风景。何立伟搞文学的路数太像汪曾棋,对此,他本人供认不讳。在散文《关于汪先生》里,他饱含深情地写道:“我在面临文学的选择时,汪先生的文章是十字路上一道启示的光亮。我要感激他,虽然他根本不知道这份遥远的而且是偷偷的感激。”那么,何立伟从汪曾祺那儿究竟获得了什么呢?解读他们的小说与散文,不难发现,出世的思想和人世的情怀是撑持他们文学思想的哲学基础。出世的思想使何立伟能细心地发现和平静地讲述生活中的真善美,能于喧哗和躁动中深深浅浅地走属于自己的文学之路,轻功名、淡利禄、不矫揉,更不会搔首弄姿,始终坚持以最个体的方式,不温不火,从从容容,悠悠缓缓地讲述大千世界,宇宙人生。当代文坛,纯粹的文人有几人耶?汪曾祺是也,何立伟是也。出世的思想,帮助何立伟的散文达到了“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境界。这种“出世”,不可与封建士大夫的看破红尘,消极避世同日而语,而是看破红尘之后回过头来再看红尘。这一回头,却把红尘看得更透。这一回头,更理性,更惊世骇俗,他看到的世界更逼真,更立体。何立伟的散文篇幅短小,几百千把字,以写人叙事居多,依散文通行的类型标准,你很难将他的散文界定在某类型某风格流派中。就阅读体验,我以为他的散文大有“五四”小品文那种耐人咀嚼的青果味和橄榄味;就笔法,则远似丰子恺,近似汪曾祺;就神韵,则一个活生生的汪曾祺。出世的思想使何立伟对人生世象的参悟达到了一般作家难以企及的高度,他既能人乎其内深人到人物的精神底层作近距离透析,更能出乎其外,站在人生甚至宇宙的高度,对人物作俯瞰和打量。因此,何立伟笔下的人物带给人更多的是精神的震撼,智慧的启迪和人性价值的追寻。在《忽然想起韩少功》中,他这样写韩少功的文化人格:“我总隐隐有一种感觉:少功人格里出世的东西比人世的东西更多,也更真实。他对人生参悟得太透彻了,他知道生命的安息之地在哪里。”联系韩少功的文学创作以及人生走向,我们不能不叹服何立伟真正抓住了属于人物精神中最本质的东西,可谓一针见血,鞭辟人里。在《去看王老师》中,何立伟这样写自己的老师:“王老师名叫王俞,她的家非常简陋。冬天里,关门闭户,房间里显得很是灰黯。在这样的房间里,只有王老师的眼睛和金子样的童心在闪光,感动得我们只看到了自己的苍老。”对于自己的老师,要说的话应当很多很多,音容笑貌,言行举止,学识涵养,精神品格等都属于“说”的内容,但何立伟以简驭繁,寥寥几笔就活画出人物的精神世界,给人以“于无声处听惊雷”般的思想冲击。人世的情怀在何立伟笔下具体表现为一种人性关怀,他的小说和散文都于恬淡中弥溢着暖烘烘的人间温情,他对笔下的人物给予了最大程度的理解和关爱,他更注重对人性中真善美的整理和挖掘,不管这个人的身份地位如何,也不论这个人的行为举止是多么的怪异乖张和不合时宜。甚至可以这么说,宽容和理解已定型为何立伟最基本的人生态度。
若要寻根,何立伟的这种文学思想可以溯源至汪曾祺以及汪的老师沈从文。在沈从文的笔下,你几乎找不到一副狰狞丑陋的面孔和一具肮脏腐烂的灵魂。《边城》里的团总及其儿子们,若放在一般作家笔下,八成是恶霸地痞流氓无赖形象,沈从文却把他们写得那样温良敦厚。汪曾祺得老师真传,即便是一个普普通通甚至有许多毛病的勤杂工(《詹大胖子》),汪曾祺也能找到人性的亮点并投以满腔的热情。有不少人苛责沈从文师徒笔下的人物缺乏人性深度,太唯美理想。孰料,这正是他们对人性的理解达到了惊人的高度之后的大彻大悟。试想,倘若这个星球上的人们都怀揣着沈从文、汪曾棋般的宽厚与善良,我想这个世界注定少了许多血雨腥风弱肉强食坑蒙拐骗巧取豪夺,而呈现出一幅风和日丽天朗气清春暖花开姹紫嫣红的美丽图景。并非沈从文师徒不具备挖掘人性深度的艺术创造力,而是哲学思想和人生态度决定了他们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并非沈汪师徒的眼里澄如明镜纤尘不染,甚至没有丝毫的怒与愤,只是他们的怒与愤如冰山下的火焰一般深潜着,而蓄积的能量却比剑拔弩张电光石火更显出几多深沉的力量。如是而已。何立伟算是真正读懂了沈从文和汪曾棋,在思想和艺术的追求上与沈汪师徒有着明显的承传特征。他对人生世象的解读总是那么沉稳从容,不急不躁,就像沉淀已久的丹田之气从嘴里悠悠吐出。比如在《真正的好东西是流行不起来的》这篇散文中,何立伟向我们娓娓讲述了一个叫宋元的作家的人生与创作点滴,对宋元散文在语言质地上颇似汪曾棋的风格给予了热情的肯定。他这样评价宋元的文化人格:“宋元放弃种种而执著于写作,也不是为了虚名的流行。对于他来说,生活的美学就是娓娓地倾诉。”末尾处,冷不丁来一句:“这喧嚣的世界,也总该还是有些静静倾听的耳朵的吧。”在貌似平静的讲述中,传达出一种关注现实生活,关注人生世象的人世情怀。
对于一个成熟的作家,其创作风格具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并且贯穿在不同的文体之中。汪曾棋曾为何立伟的第一部小说集作序,称何立伟把小说当诗来写。我以为何立伟的散文也大多秉承了小说创作的风格,同样弥溢着浓郁的诗意:诗的意境、诗的情绪、诗的氛围、诗的语言。请欣赏这段文字:汪先生的文章行云流水,恬淡温馨,读它有如月下轻嗅着一朵淡紫的花,幽香沁人心脾。汪先生的文章除尽了火气,以极平静的心态面对广大世事,故一切纷扰经了他的文学过滤,皆成了仿佛草原的边缘渺渺飘来的一缕笛音,叫人也就安静下来,参悟着人生更深处的意味。(《关于汪先生》)一般的评论文字大都讲究用语的准确、深刻,而在何立伟的笔下,枯涩的评论语言却变得异常鲜活灵动,情状,音响,色彩参差交织,充满了诗情画意。何立伟散文的语言很别致,很立体很耐人寻味,诗歌常用的通感、移用被运用得出神人化,方块汉字在他的笔下驯服极了,听凭他驱遣使唤,拿捏玩弄,处处收到奇特的审美效果。如:他点燃一支烟,站起身,来来回回地走,影子在墙上不安地忽长忽短。他到底是恋着爱着情人一般的文学啊,于是就慌慌张张地丈量这烫烫的恋与爱。(《说一个人,叫老何》)影子无所谓安与不安,如此一写,人物的焦灼心理便跃然纸上;按现代汉语语法规范,“丈量”这一及物动词所带的宾语应当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何立伟“丈量”的却是一种情感,这分明是运用了诗歌中“移用”的手法,如此一写,笔下人物对文学刻骨铭心的爱便有了一种厚重感。当然,如果这样的句子连篇累牍,即使再美,也容易让人疲惫,何立伟把握得极有分寸,常于轻轻松松中陡然来上一两句,如黄沙漫漫的大漠突然出现的几块绿洲,给人以几多愉悦,几多惊喜。何立伟深谙语言的美学法则,他善于处理浓与淡,俗与雅,疏与密,庄与谐之间的关系。如:“屋外头是茶树林,席地而坐,茶花就开在脑壳上头。阳光如外婆的巴掌,慈祥地扇在我们的脸上。”(《这么一个人和这么一面镜子》)前一句极白极淡极俗,后一句极浓极雅极巧,不能不叫你放慢阅读速度,甚至驻足流连,缱绻低徊。在我看来,何立伟的散文简直就是功夫茶,读他的散文自然需要品功夫茶的功夫。信吗?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