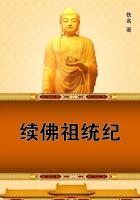“文革”后,中国评剧院恢复建制,复排的头一出保留剧目就是《向阳商店》。1978年7月20日在王府井的东风剧场(吉祥戏院)演出的时候观众,十分踊跃,气氛格外热烈,场面非常感人。当时的演出人员中,除魏荣元已故外,马泰、喜彩莲(因年事已高演出几场后即由刘淑萍饰傅桂香)、张桂祥(接替魏荣元饰王永祥)、张淑桂、花月仙、刘淑萍、鸿云霞、陈少舫、纪月亭、新艳琴、李大生等原班人马悉数登场。
《向阳商店》历经风雨,经过多次加工改造,终成中国评剧院现代戏的保留剧目。它的成功归功于原剧作者来自基层,他们有生活历练,也有一定的创作能力。演员(先由业余演员排演)是来自商业战线的售货员。因此,该剧的演出充满了生活气息。比如那朝气蓬勃的居民大院,送货上门的货车,骑着自行车(虚拟动作)满街跑的老来乐等等。正是因为有了生活基础扎实的《生活的凯歌》,才有了后来的《向阳商店》。
三、非常年代,非常之人
20世纪60年代,在白塔寺十字路口西南角,有个坐西朝东的大院子,就是中国评剧院的办公地。别看这座院子不大,却是藏龙卧虎,汇聚了众多中国评剧界优秀的创作者和深受观众喜爱的优秀演员。
在1967年“文革”岁月中,有两位评剧爱好者忽发奇想,从学校开了张大串联证明,目的就是想到中国评剧院一看究竟。当时接待他们的是剧院革委会副主任张连喜,他曾经在《杨三姐告状》中饰演杨厅长。当时的红卫兵小将到访,可不能慢待。在张连喜的陪同下,不仅参观了剧院,而且还见到了马泰、魏荣元。虽然是在非常岁月,但马泰是新中国培养的评剧演员,他和魏荣元老早就解放了,没什么大事。两位红卫兵小将与心中崇拜的艺术家近距离接触、寒暄,评剧家们的平易近人为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在评剧院内的假山上,意外发现了这样一组镜头。假山上搭建着现在已经很难见到的窝棚,一个个熟悉的身影蹲坐在窝棚里写交代材料。记得有张德福、新凤霞、花月仙、花砚茹、小白玉霜等众多观众喜爱的艺术家。谁能想到,这些最优秀的中国评剧演员,却离开了心爱的舞台,窝在这里写所谓的交代材料,令人感叹。
在那个全国只有“八个革命样板戏”的年代,中国评剧院将《智取威虎山》移植为评剧,在政协礼堂首演。尽管是移植京剧,观众还是能为看到久违的评剧激动不已。当马泰饰演的参谋长出现在舞台上,还没开唱,全场就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紧接着张德福饰演的杨子荣上场了,魏荣元饰演的李勇奇也亮相了。就连陈少舫饰演的匪参谋长,席宝昆饰演的座山雕,观众都是不遗余力地使劲鼓掌。通过观众的掌声,不难体会到人们对于评剧的热爱和渴望。可惜没有新凤霞,那时她还在被关押改造之中,不然很可能会饰演李勇奇的母亲。
当时,中国评剧院把储煤的仓库腾空,用木板将窗户和门钉死。被关押的人只能从门上留下的空隙爬进爬出。小白玉霜、新凤霞就关押在这间地上垫着稻草的屋子里,接受所谓的监督和审查。
这些被单独关押的重点人物,不准相互说话。还有专门的看管人员在门外“三班倒”,累得也够呛。夜里睡觉,不许关灯,脸朝窗户不许朝里。因关押的人员中有男有女,还得配备男女看管,且都是中国评剧院的同事,新凤霞就跟看管人员说:“你们也闭一会儿眼睛,休息休息,我们不会出事。你们怕我自杀,可以把我身上的钥匙、手表都拿走。我没有罪,你如果相信我,可以睡会儿。不然我睡我的,你就站在外边为我站岗吧。”
其实看管人员也是形势所迫,为了完成工作而已。听了新凤霞的“关切”话语,真的就坐在椅子上睡了一觉。
新凤霞回忆说,当时工资也停发了,每月只给12块钱生活费,吃饭都困难,还要开忆苦会,然后让这些被看押人员吃忆苦饭。全是麸子和糠,说是不知旧社会的苦,就不知今日的甜。旁边有人看着,谁不吃就批斗谁。新凤霞有胃溃疡病,但也不敢不吃,硬是就着凉水,吃下大半碗。吃了麸子皮和糠,连大便都解不下来,最终胃出血。疼得昏过去也没人管,演员杜洪昆当着看管人员说:“凤霞,我作主了,上人民医院,走!”说着背起新凤霞到了人民医院。医生说:“她胃出了血,本应当住院,可她是‘黑五类’。”无奈,只给了点药,打发回去了。
从白塔寺中国评剧院往南不远就是全国政协,在被关押期间人们最高兴的就是出去劳动。比如下大雪扫马路,扫着扫着就能遇到政协里被关押的人也出来扫马路。新凤霞就和沈醉、溥仪凑在一起扫,溥仪根本不会干活儿,大家就替他多扫几下。溥仪就说:“谢谢您了。”
即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新凤霞依旧没有忘记自己的本职工作。在关押期间,天天练功,练腿、腰、胳膊、手。看管人员出面阻止,并用绳子将新凤霞的双手倒捆着。无奈之下,新凤霞就一出戏一出戏地背戏词。看管人员不知她在嘟囔什么,就诬陷说新凤霞咒骂共产党。军宣队有位人员是个评剧迷,借审查新凤霞时让她唱评剧。新凤霞就唱了两段《刘巧儿》和《花为媒》。军宣队听完后说:“汇报说,你已疯傻了,整天自己跟自己讲话,神经病了。”新凤霞说:“我没有傻,我就是怕放我出去不能唱戏了,那比关押我还要痛苦。”这位军宣队说:“你回去吧,你很快就会上台演出的,可不许对别人讲……”
同样失去人身自由的还有小白玉霜,这位评剧“白派”传人,天生就是块演戏的材料,其他什么都不灵通。在接受管制期间,小白玉霜每天机械地跟着大伙儿早请示、晚汇报,背语录、学文件,却完不成劳动指标,更交不出认罪材料,被公认为是公开反党、反革命的坏分子。所以经常强制干一些重体力劳动,致使每天伤痕累累,不是扎了手,就是砸了脚。更为荒唐的是,造反派要她承认,在1952年在朝鲜前线慰问志愿军演出《秦香莲》,是贩卖封资修的黑货,是故意瓦解军心,破坏抗美援朝等。耿直的小白玉霜坚决不承认,又被认为是认罪态度顽固。最终,小白玉霜含冤自杀。
着名剧作家胡沙写道:“前几年我到京郊农村去,一些贫下中农偷偷地对我说,他们爱听小白玉霜的评剧,可是听不到了。当时正是‘四人帮’独霸文坛的时候,我也无言以对。但我总不相信小白玉霜和她的艺术会永远埋没。因为她曾经为人民做过好事,人民不会忘记她。”
四、浩然与评剧失之交臂
浩然是北京市文联的专业作家,被人们誉为农民作家。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我的根在农村,我要为农民而写作。”这也是浩然的创作宗旨。在那样一个文化凋零的年代中,他创作的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深入人心,是当时发行量最大、读者群最多的作品。特别是《艳阳天》问世之后,立即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浩然的名字家喻户晓,收到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一万多封。
长篇小说《艳阳天》,通过京郊东山坞农业生产合作社麦收前后发生的一系列矛盾冲突,勾勒出农业合作化时期蓬蓬勃勃的生活画卷,精细地刻画了农村各阶层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性格,热情地歌颂了在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新生力量。小说的情节曲折丰富,结构完整紧凑,人物形象生动传神,语言朴素晓畅,显示出鲜明的艺术特色。小说不可避免的带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色彩,可贵的是《艳阳天》里塑造了众多可信可爱的贫苦农民的形象和真实生动的落后农民的形象,更为可贵的是,浩然通过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表达了社会主义永远是“艳阳天”的坚强信念。不论是描写、叙事还是抒情,对社会主义的赞美都由衷地流诸笔端,全书自始至终洋溢着一种乐观主义精神。
1965年,中国评剧院拟将《艳阳天》改编成评剧,当联系到浩然之后,他非常高兴并积极响应和支持。评剧起源于农村,接近普通民众,而浩然也来自于河北农村,而且是长年生活在农民中间的当代作家。在浩然出版的自传体小说《乐土》中,他用了不少篇幅,生动地记述了从小看评剧,乃至想当评剧演员,以及和姐姐一起偷偷学戏的趣事。所以说,浩然对评剧从小就有感情,也特别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搬上评剧舞台。在与中国评剧院达成改编共识之后,他就带领评剧院的主创人员,来到顺义县焦庄户村体验生活,改编剧本。
当时中国评剧院选定了着名演员杜宝宇、张德福、李忆兰等担纲主要角色。经过几个月的剧本改编和舞台排练,大型现代评剧《艳阳天》终于就要彩排公演了,浩然自己也十分高兴。然而,此时已到了1966年的春天,“文革”风暴就要来临了。在那个非常敏感的时期,形势瞬息万变,无人能够把握,更别说文艺创作,这个人人都拿捏不准的烫手山芋。剧院负责审查剧目的领导,最终没有批准《艳阳天》这个戏上演,而是提出了修改意见。剧本越改越难,最终未能公演。浩然对此非常失望,但也无可奈何,他理解评剧院的难处。《艳阳天》没能与广大观众见面,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197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将《艳阳天》改编拍摄成同名电影公映,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深受观众的喜爱。在街头巷尾,甭管大人孩子都对电影中的人物萧长春、弯弯绕、马小辫等品头论足。
1975年,浩然出版了中篇小说《三把火》,中国评剧院再次接洽浩然,愿意将该作品搬上评剧舞台,并为此再次组成了强大的创作阵容。虽然说此前《艳阳天》留下了遗憾,但大家彼此之间的感情并没有伤,特别是对评剧的热爱始终如一。然而1975年正是动荡不安的年代,文艺创作异常敏感,稍有不慎,就会上纲上线。几经波折,《三把火》易名为《百花川》,剧目修改审查一年之久,最终还是没能与观众见面。浩然再次与评剧失之交臂,未能实现与中国评剧院的第二次合作。浩然在聊天中说道,1949年10月,为庆祝新中国成立,他曾写过一个小戏《小两口唱国庆》,还自告奋勇,男扮女装,登台饰演戏中的小媳妇。几十年过去了,浩然回忆说:“由于我没有保留那个剧本的底稿,又因为经过的年代久远,我已经不能全部背诵下来,但有些唱段还牢牢地记着。”由此可见,浩然心中对评剧的情结和热爱。
2008年,浩然因病在北京逝世。他的作品最终也没能搬上评剧舞台上,这对于热爱评剧的浩然来说,成为一桩未了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