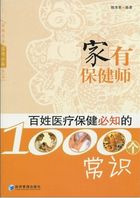在阿克拉省,前往医疗门诊所就医的人中有25%的女性及7%的男性肥胖。40多岁的女性肥胖比例达50%。加纳医学院的一位副教授写道:“有理由认定,30岁到60岁的女性普遍严重肥胖。”此外,“在西非的沿海城镇中,肥胖的女商贩极其寻常。”
1970年——尼日利亚:拉各斯
5%的男性和30%的女性肥胖。在55岁到65岁的女性中,有40%非常胖。
1971年——南太平洋:拉罗通加
40%的成年女性肥胖,其中25%极其肥胖。
1974年——牙买加:金斯顿
罗尔夫·理查兹(Rolf Richards)在英国受训成为了一位医生,之后他在西印度大学经营着一家糖尿病诊所。他的报告称,在金斯顿,10%的成年男性以及三分之二的女性肥胖。
1974年——智利(第二次)
一位来自圣地亚哥天主教大学营养学家的报告称,根据对3300名工厂工人(绝大多数从事重体力劳动)的调查,“仅有”11%的男性和9%的女性属于“严重营养不良”,“仅有”14%的男性和15%的女性属于“严重超重”。45岁以上的人群中,近40%的男性和50%的女性肥胖。他还提到了智利从20世纪60年代起的调查研究,注明“农场工人中(肥胖)发生率最低,办公室职员最胖,但贫民区的居民一般也很胖”。
1978年——俄克拉荷马州
当时著名的糖尿病流行病学家凯里·维斯特(Kelly West)的报告称,当地的美国土著部落“男人很胖,女人更胖”。
1981-1983年——得克萨斯州:斯塔尔县
该县毗邻墨西哥,位于圣安东尼奥市以南约320千米。得克萨斯大学的威廉·缪勒(William Mueller)及其同事对当地1100多名墨西哥裔美国人的体重和身高进行了测量。结果表明,30多岁的男性中约有40%的人肥胖,虽然他们绝大多数人从事农业劳动或在乡下的油田工作。50多岁的女性中超过半数都很肥胖。至于生活条件,缪勒后来描写道:“非常简单,(整个斯塔尔县)只有一家墨西哥饭店,其他一无所有。”
那么,他们到底为何发胖?过度饮食、卡路里摄入及卡路里消耗的理论总能非常方便地对这个问题做出解答。如果这个群体是如此贫穷,营养极其不良,以至于即便是那些极其信奉“过度饮食造成肥胖”的支持者,也很难想象他们有充足的食物——比如20世纪初及50年代的皮马人、20年代的苏族人、特立尼达人或60年代居住在智利贫民区里的人——那么就可以宣称:他们肯定运动太少。如果这个群体明显是体力劳动者——比如皮马女性、智利的工厂工人或墨西哥裔美国籍农民和油田工人——那么就可以宣称:他们吃得太多。
同样的理论也适用于个案。假如我们很胖,但饮食适当——就是说,我们吃得不比那些纤瘦的朋友和兄弟姐妹多——那么这些专家就会很自信地认定我们肯定缺乏运动。如果我们体重超标但又经常进行体育锻炼,那么这些专家会同样自信地认定我们吃太多了。
所以,专家认定:如果我们不贪食,那么我们必定犯有懒惰的原罪;如果我们不懒惰,那么暴饮暴食就是我们的原罪。
之所以会得出这些结论,通常是因为忽视了有关群体或个人息息相关的某些其他事实。实际上,专家们经常不太愿意去了解更多的情况。
20世纪70年代初,一些富有研究精神的营养学家和医生对贫困人群中高度肥胖的现象展开了讨论,对于造成肥胖的原因,他们偶尔也持开放的态度。正如我们应该做的那样,他们充满了求知欲,对那些被坚信不疑的理论也并非毫无保留地支持。
当时,肥胖仍然被认定为营养失调问题,而不是营养过度问题,与今天的情况如出一辙。例如,1971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项调查披露,近10%的男性及三分之一的女性肥胖。数年后,当这些数据被发表在学术文献上时,该调查的研究者在开头是这么声明的:“即使对捷克斯洛伐克只进行了短暂的访问,你也会发现,与其他工业化国家一样,在捷克斯洛伐克,肥胖司空见惯。这也许是营养失调最普遍的表现形式。”
把肥胖当作营养失调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与附加的道德标准无关,与信仰无关,与贪食懒惰的含蓄暗示也无关。这只能说明某些食品供给出了问题,我们理应去发现这些问题。
1974年,在英国受教育的牙买加糖尿病专家罗尔夫·理查兹(Rolf Richards)对肥胖和贫困的窘境进行了没有偏见的论述:“用现有的营养标准,很难解释在诸如西印度群岛之类与发达国家享有的生活标准相比相当贫困的社会中,肥胖的发生率还是如此之高。在这些地区出生的儿童,2岁左右就发生营养失调或营养不良的现象非常普遍,几乎占牙买加入院儿童的25%。从幼儿到青春期的少年,营养不良的情况一直持续着。而女性从25岁起开始显现肥胖,30岁后肥胖的概率逐渐增大。”
理查兹所说的营养不良,指的是没有足够的食物。西印度群岛的儿童从一出生到十几岁都异常消瘦,发育普遍不良。他们需要更多的食物,不只是更多有营养的食物。当他们成年后,肥胖就在这些个体中(尤其是女性)蔓延开来。我们在1928年的苏族人和之后的智利人中,都看到了这样的现象,在同一人群甚至同一个家庭中,营养不良或营养失调与肥胖问题共存。
以下是最近被反复讨论的情况,它被夸大为“过度饮食导致肥胖”的范例。这个观测来自于2005年一篇刊登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文章《营养学上的悖论——发展中国家的体重过轻和肥胖》,作者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人类营养中心主任本杰明·卡巴列罗(Benjamin Caballero)。卡巴列罗描述了他在巴西圣保罗贫民区一家诊所内的所见所闻。他写道:“候诊室中到处都是带着幼童的母亲,这些儿童大都发育不良,有着慢性营养不足的典型症状。不幸的是,发展中国家贫困城区的人很少对这些儿童的境况感到诧异。他们可能会诧异的是,许多怀抱营养不良婴儿的母亲却身体肥胖。”
随后,卡巴列罗说出了这一现象呈现出的困境:“体重过轻与超重共存的局面对公共健康提出了挑战。”简而言之,如果我们想要预防肥胖,那就必须让人们少吃点;但如果我们想要预防营养不良,我们就必须提供更多的食物。减肥和预防营养不良,我们到底该何去何从?
按照卡巴列罗的观点,发育不良并且伴随慢性营养不足之典型症状的儿童,与超重的母亲这两者共存的局面并不会对公共健康形成挑战,而是对我们的“信仰”——我们认定的健康标准产生挑战。
我们相信,这些母亲之所以体重超标是因为吃得太多,我们也知道儿童之所以发育不良是因为得不到足够的食物。那么,我们就可以假设母亲消耗了多余的卡路里,这些卡路里原本可以让她们的孩子茁壮成长。换句话说,你会得出一个奇怪的结论:母亲情愿让孩子挨饿,这样她们自己就能大吃大喝。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再说一遍:同一群体甚至同一家庭中体重过轻与肥胖共存的局面并不会对公共健康形成挑战,而是对我们关于造成肥胖的原因的“信仰”形成挑战。请大家接着往下看,我们会发现这不是唯一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