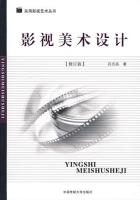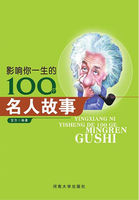近人任中敏曾言:“元人作曲,完全以嬉笑怒骂出之,盖纯以文字供游戏也。惟其为游戏,故选题措语,无往不可,绝无从来文人一切顾忌。宏大可也,琐屑亦可也。渊雅可也,猥鄙亦可也。故咏物如‘佳人黑痣’、‘秃指甲’等,皆是好题目,了不觉其纤小。所描写者,下至佣走粗愚、倡优淫烂,皆所弗禁,而设想污秽之处,有时绝非寻常意念所能及者。”可以说,“以文字供游戏”,酣畅自由地抒发胸中的喜怒哀乐之情正是元曲艺术家从事艺术创作的动力和归宿。在游戏笔墨,进而游戏人生的创作活动中,元代艺术家们阐扬了生命的美学与生存的艺术,呈示出元代艺术创作观念的时代风采。
元代艺术创作观念中“游戏”的内蕴
元末画家王冕曾对“以墨为戏”的创作观念作出理论上的概括:
戏墨,发墨成形,动之于兴,得之于心,应之于手。
古人以画为无声诗,诗乃有声画,是以画之得意,犹诗之得句,有喜乐忧愁而得之者,有感慨愤怒而得之者,此皆一时之兴耳。
凡欲作画,须寄心物外,意在笔先,正所谓有诸内必形于外也。王冕从“内”和“外”两个方面,对元代“游戏翰墨”的艺术创作观念作了说明:“内”是对创作主体审美心境的要求,发墨为戏乃是出于创作主体的意兴感发,此即谓“有诸内”,创作主体或者喜乐忧愁、或者感慨愤怒,内心激情的触发是艺术创作的动力所在,也就是“意在笔先”,创作主体的审美心境是笔墨游戏得以进行的前提;“外”是对创作主体笔墨技巧的要求,内心的情志只有付诸笔墨才能以感性的形式表现出来,此所谓“形于外”,创作主体内在意兴或者付诸诗,或者付诸画,只有通过“应之于手”的游戏之笔才能酣畅淋漓地抒泄主观情志,创作主体的得心应手的笔墨技巧是艺术创作得以实现的条件。
王冕以文人画艺术为观照对象,对于“以墨为戏”创作观念的理论内涵的阐释,可以看作元代艺术创作观念时代内蕴的集中呈现,而对于元代诸种艺术门类所共有的艺术创作观念中“游戏”内蕴的阐发,都可以借鉴“有诸内”而“形于外”理论模式进行考察,这样,本书将元代艺术创作“游戏”观念的时代内蕴归纳为自由游戏的审美心境与游戏法度的笔墨技艺两个方面。
一、自由心境
德国美学家席勒将审美自由称为“游戏冲动”,在他看来,“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伽达默尔在席勒艺术美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只有当游戏者全神贯注于游戏时,游戏活动才会实现它所具有的目的”,也就是说,只有达到了人性的高度自由,全神贯注于审美对象,艺术才成为游戏。中国元代的文人画艺术家们正是在寄情大化而心物交融的审美自由状态下讲求“游戏笔墨”的,正如吴镇所言“图画书之绪,毫素寄所适。垂垂岁月久,残断争宝惜。始由笔砚成,渐次忘笔墨。心手两相忘,融化同造物”,“我爱晚风清,新篁动清节。咢咢空洞手,抱此岁寒叶。相对两忘言,只可自怡悦”。在吴镇看来,只有达到了心手两忘的自由境界,才能实现真正自由的笔墨游戏。
吴镇的《晴江列岫图》就是这样一幅“得于心而发于外”的经典画作。画面自识“镇僻处穷居,寡营敛迹,孑立独行,谢绝世事。非有意存乎其间,懒性使然也。暇则焚香诵书,游戏翰墨。时作短幅小方,稍不惬意,即投之水火。或交知见爱之,遂以相赠。当于人心者,十有八九矣。往岁嘉遁先生,以长缣数幅索画,岂以余画为足重乎。予何敢辞,不谓淹滞二载,而先生亦不我咎,真有以知我也。今年秋,乃竟其卷,为书若此,惟先生略其妍媸而并忘其罪愆,则镇幸甚。八月下浣,梅花庵吴镇识。”直接表述出了游戏翰墨的创作心境。无怪乎元代著名道士吴全节对此大为赞赏,“仲圭此卷,神凝智解,得于心而发于外,解衣磅礴时,正与山林泉石相遇,故能揽须弥心尽于一芥,气振而有余,尽得山川之精蕴耳。彼含墨咀毫,受捐入趋者,可执工而随其后耶。”
将自由游戏的审美心境作为艺术创作的内在前提,是元代的文人画艺术家们的普遍观念。张退公《墨竹记》有言:“得之心,应之手,心手相迎,则无不妙矣。”李衎《竹谱》提倡“握笔时澄心静虑,意在笔先,神思专一,不杂不乱,然后落笔”,都强调了艺术创作过程中审美心境的重要作用。倪瓒更将这种全神贯注的自由境界称为“游戏入三昧”。方闻在解读倪瓒《疏林小笔图》时曾经坦言:“山石造型似用潦草数笔与横卧的点子随意涂染,体现出很有教养的稚拙趣味。这里,倪瓒的用笔是极其愉悦的嬉戏,各式各样笔法融合而成的画,不仅表现出真实的山水,而且还流露出画家的渴望心情。”三株稀疏的小树紧靠在荒凉的河岸边上,显得宁静而孤傲,画面题诗“疏林小笔聊娱戏,画与金华张隐君。好为林间横玉篴,秋风吹度碧山云。”高的意境与游戏的点染相互筹措,张扬着艺术家的自尊与不屈,呈示出创作主体高度自由的审美心境。
在元代文人画艺术家的思想观念中,用自由游戏的笔墨抒写内心激荡的情志,是一种在心手相忘、神思专一的审美心境中所进行“不杂不乱”的创作活动。彭修银将这种高度自由的审美心境称为“超越的和谐”:“中国文人画家无论是文同、苏东坡、米氏父子,还是温日观、王冕、黄公望、倪云林,他们的墨戏之作都把他们的人生带到一个很高的精神境界。超越表示精神升进中的自出状态;和谐则象征精神自由之极致,超越与和谐,都是在人类渴望自由的一瞬间产生的。”元代的文人画艺术家们正是在超越现实世界的苦难与羁绊的过程中,洒脱地抒写着内心的积郁与高洁的情致,从而获得了精神世界的和谐与自由。
对于如何达到这种自由游戏的和谐境界,元代文人画家也有自己的看法。在元代文人画家看来,要在艺术创作中实现自由游戏的审美境界,首先要以一种严肃的态度“师造化”,正如赵孟頫所言,“久知图画非儿戏,到处云山是我师”,在元代文人画艺术家的创作观念中,对于造化自然的学习与模拟乃是进行绘画创作的第一步。
黄公望学画之初曾“皮袋中置描笔在内,或于好景处,见树有怪异,便当模写记之”,开始于对自然景物的反复摹写。明人李日华记载了吴镇的事迹,“黄子久终日只在荒山乱石、丛木深筿中坐,意态忽忽,人不测其为何。又每往泖中通海处看急流轰浪,虽风雨骤至,水怪悲诧而不顾”,观察自然,感受自然,描摹自然,也是吴镇进行绘画创作的根基所在。可以看出,在元代文人画家的普遍观念中,“师造化”之功正是进行艺术创作的基本出发点。
进而,元代文人画艺术家更强调创作主体陶养于主观情志的审美心胸在创作实践中的重要作用,正如高居翰所言:“一个完善的人对自然的启迪会有反应,但并不总受其影响,因为这些启迪没有改变他的自我本质;文人画家只是利用自然之物来‘寄寓其心胸’,并不听任自然物体或他对自然物体喜好的感情来决定绘画作品的意蕴。”元代文人画艺术家们正是在摹写自然的过程中寄寓着内心的情感,张扬着主体的精神,从而呈示出对陶养着主体情志的审美心胸的无限眷恋。
元代文人画家将审美的心胸称为“胸次”。倪瓒在探讨艺术创作问题时就曾指明:“下笔能形消散趣,要须胸次有筼筜。”汤垕也曾强调,“盖胸次萧洒,意之所至,落笔便有与庸史不同”,都强调审美的心胸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黄公望从画史中总结出“古人作画胸次宽阔,布景自然,合古人意趣,画法尽矣”,柯九思也曾感叹宋人所临《辋川图》曰:“苟非胸次磊落,指掌神奇,恐未易臻此也”,他们纷纷指出审美心胸是历史上优秀作品得以为人们所认可的根本所在。生活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中,社会现实的纷乱与自身地位的下沉,使得元代文人画艺术家们更加孤傲地坚守着传统文人内心深处的情感与志趣,在历史的契机下,陶养于主观精神的审美心胸,更加突出地成为元代艺术家们从事艺术活动的主体要求。
元人也多以“胸次”为审美标准鉴赏他人画作。吴海称赞米友仁的《海岳庵图》,“是图山峰隐映,林木惨淡,长江千里之势,宛然目中。胸次非有万斛风雨,不能下笔”;王冕题柯九思画竹:“长缣大楮纵挥洒,高堂六月惊秋声,人传学士手有竹,我知学士琅玕腹。”吴镇《题王叔明卷》亦称:“短缣几许容丘壑,郁郁乔林更著山。应识王郎胸次好,未教消得此身闲。”纷纷提出“胸次”在形成优秀艺术作品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将艺术家的审美心胸作为了重要的品评标准。
可以看出,在“师造化”与蕴“胸次”二者之间,元代文人更加重视“胸次”的作用。正如元初理学家郝经在其《内游》一文中所言:“身不离于衽席之上,而游于六合之外,生乎千古之下,而游于千古之上,岂区区于足迹之余、观览之末者所能也?持心御气,明正精一,游于内而不滞于内,应于外而不逐于外。”元代三教合一中对于禅宗心性修行的重视,与元代人学转向中对于人的心性本体的张扬,形成了元代重视主体心灵的精神气候。这种时代精神与元代文人的现实境遇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元代的艺术创作,促成了元代文人画艺术家们对“胸次”的重视。
吴镇就从绘画艺术创作的实践出发,阐述以胸臆为重的艺术观念:“夫画竹之法,当先师意,然后以笔法求之可也。倘得意在笔前,则所作有天趣自然之妙”,“墨竹虽一艺,而欲精之,非心力之到者不能”。黄公望更坦率直言:“画不过意思而已”。可以见出,在“造化”与“胸次”之间,元代的文人画艺术家们在肯定“师造化”的基础作用的同时,往往更加强调“胸次”与“心意”在艺术创作活动中的主导作用。于此,方闻在《心印》中将元代山水画的风格概括为“一种表现艺术家主观心灵世界的新型书法性山水画”,他强调,“整个宋代,艺术家通过一般化的自我,有针对性地格物以认识客观事物,而元代画家却愈来愈普遍地专注于个体内在的自我。由于元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自我表现,或称为”言志“日益明确地成为诗学与绘画的主要宗旨。元代山水画的首要主题就是艺术家的内心感情,实际自然景致被摆到了次要的位置。”可以看出,元代的文人画创作观念凝定了中国艺术重视主体个人情感、重视主观内心自我表征的时代特质。
张扬主观的心灵世界,重视审美心境于艺术创作中重要作用的思想观念,也存在于元代其他门类的艺术创作者心中。
就诗文艺术而言,吴澄在《皮达观诗序》中即曾以“游戏”为赞,他认为:“偶然游戏于诗,盖其声迹之仿佛所到,可涯涘哉。”吴澄论诗强调“物我俱泯”的“真诗境界”:“诗人网罗走飞草木之情,疑若受役于物。客尝问焉,予应之曰:江边一笑,东坡之于水马;出门一笑,山谷之于水仙。此虫此花,诗人付之一笑而已,果役于物乎?夫役于物者未也,而役物者亦未也,心与景融,物我俱泯,是为真诗境界。”“网罗走飞草木之情”,即要求对造化自然的详细体认,亦即师造化,但却不能“受役于物”,被笔下描绘的物象所驱遣,也不能“役物”,仅仅执著于对物象的描写,“心与景融,物我俱泯”才是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
提倡融造化自然与“吾心”为一体的审美心境,进而更重视“吾心”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也是元代著名诗文理论家刘将孙的主要观念。刘将孙强调以“悠然得于人心”为诗歌创作基点:“目之于视,口之于言,耳之于听,类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有得于情性者,亦如是而已。夫言亦孰非浮辞哉,惟发之真者不泯,惟遇之神者不传,惟悠然得于人心者必传而不朽。”在刘将孙的艺术观念中,“哀乐俯仰,各尽其性”是诗歌艺术的本质追求,因此,“人间好语,无非悠然自得于幽闲之表”。比之于对外物的摹写,悠然自得于内心的本真性情才是不朽的艺术创作。而所谓“悠然自得”亦可看作摆脱现实羁绊,主体精神高度自由的游戏状态,主体心灵徜徉于物我之间的和谐境界。
进而,刘将孙特别重视“心”,强调艺术创作乃是“得之于心”:“道与艺一也,未有得之于心而繇师传者,非其至也。传之于人者,无非效人者也,于吾心何有哉?效人者,极于其人,则无以加矣。心不可极,艺亦不可极也。”在刘将孙看来,真正的艺术不是得自师传和仿效他人,而是得自“吾心”。因此,对于艺术创作来说,最为宝贵的就是心之独创:“莫神者,心也;莫巧者,心也。心之所向,必求所以如吾心,何事之不能,而何能之不妙哉!矧画物求其似而已?粲乎吾目者,横斜高下,皆吾画本也;参乎吾前者,精神谈笑,皆吾画意也……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然吾之心则一而已。”对于眼前所见的缤纷各异的物象的描绘自然是绘画艺术的创作根本,但是只有“吾之心”才能把握物象的精神,突破形似而达到神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