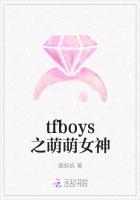第二十届澳门国际音乐节,依然秉承了兼容并蓄、雅俗并重的一贯举措,恰与澳门这座城市的文化性格相配。笔者有幸观赏了最后四场演出——10月28日的“为情而歌——中国民歌新天地”(大炮台露天广场),10月29日的“琴胡笛笙韵凝香”(澳门中乐团室内乐,岗顶剧院),10月30日的“古典与爵士——维也纳名家组合”(岗顶剧院),以及11月2日的“百老汇经典音乐剧《红男绿女》”(文化中心综合剧院),确乎印证了上述的“多元”理念。这四台节目,风格各异,样式不同,古典、流行、民间、爵士,中西合璧,古今杂陈,多路元素各显神通,俨然是一幅“全球化”条件下的多元化人文景观。
然而,在这些看来杂多纷呈的节目编排中,隐约却透出一个具有全局性的核心文化命题:如何在当下的文化生态中,继续保持乃至推进古典(经典)的、传统的音乐的生命力。或者说,怎样使古典(经典)的传统以更为切实的方式,融入令人眼花缭乱的当代社会——其典型特征,借用一句著名的流行语,即所谓“不是我不明白,而是这个世界变得太快”。显然,如此严肃的命题并不是写在每台节目的宣言告示中,参与演出的艺术家和观众也不一定在理智上明确意识到这个命题的存在,但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实际上我们就面临着一些共同的文化课题。经济学中时常论及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文化、艺术、音乐的运作中,同样也存在种种“看不见的手”——其中一只手,就是某种秘而不宣但却发生实际效用的文化理念。
例如,在“古典与爵士”那场别具特色的演出中,艺术家将维也纳的古典曲目与当代的爵士风格并置共处,其用意可谓昭然若揭:古典音乐中,也存在通俗的因子和娱乐的元素,恰如现代爵士曲目中,同样不乏深刻的抒情与高度的创意。可以说,面对“古典音乐的当下性”这一文化命题,这场音乐会的艺术家自有主见,只是,他们的处理方案在某些时候或许显得简单和随意。上半场演出,大多为单薄、轻盈的“前古典”或“泛古典”的一般性曲目,音乐分量和思想内涵都显不足,令观众感到不太过瘾,而在“为情而歌——中国民歌新天地”的节目安排中,“古典时尚女子动感组合”最后出场,只见一组妙龄摩登女子,身着鲜艳服饰,手持电子弦乐器,在台上亦奏、亦舞、亦歌,音乐的背景是带有疯狂意味的流行打击拍点,而凸显在音乐前景的则是刺激、华丽的“古典式”曲调。这是古典音乐的当代出路吗?或许。至少已被证明是方案之一。不过,就笔者的个人趣味而言,这种较为屈就底层市场的商业性理念,提供的更多是疑问,而不是解答。
无疑,古典和传统必然要被带入现代和当代,但如何处理这其中的纠葛和关系,有多种立场和路数的抉择。如上所见,一种策略可以是迎合式的,其优势在于具有大众效应,其危险在于容易滑入浅薄。与之相对,存在另一种方略——以学院派的前卫姿态引领大众,引导市场。如澳门中乐团的中国乐器室内乐音乐会“琴胡笛笙韵凝香”,不少曲目出自“新潮”作曲家群体(以谭盾、郭文景、陈怡、唐建平等为代表),用“现代作曲技法”改造和转化中国传统的和民间的音乐元素。技术上的创新,音响上的创意,自然是这些曲目的题中要义。但平心而论,整场音乐会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却是那首古琴传世杰作《流水》(古琴独奏:乔珊女士):正宗的古中国气派,典型的古文人气度,全然不见日后西方影响带来的种种“火气”,音调一咏三叹,句法收放自如。是否可以认为,这样的传统经典,给当前转型社会中偏于浮躁的现代中国人,带来心的宁静,灵的慰藉,反而获得了某种别具意味的“当下性”。看来,如何在当前的社会文化条件中,为中国音乐找到它应有的文化身份和艺术品格,尚需有识之士进一步寻访和探索。
相比较,如何在当代环境中妥贴地融入古典和传统,倒是具有流行偏向但并不流俗的音乐处理显得更为轻松自在。在“为情而歌——中国民歌新天地”音乐会中,两组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男声歌唱组合,为观众带来不少惊喜。由五位蒙古族小伙子组成的“黑骏马”,将蒙古的民间歌调与现代欧美的多声思维、流行节奏熔为一炉。《嘎达梅林》《敖包相会》,这些脍炙人口的熟悉旋律,经重新编配,给人的感觉是似曾相识,却又焕然一新。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彝人制造”,吸收美国乡村音乐的“西部”风味,作风显得更为出奇与“另类”,三位男声的演唱,忘情投入,技艺熟稔,多声部的音准控制和相互间的默契配合均达到相当高的水准。这确乎是有品位的流行音乐,或者说是艺术化的“跨界”音乐,可贵的是,其中置入强烈的中国民间音乐元素,但并不就此显得生硬或生涩。民间与流行,艺术与大众,在这里达成和谐共处,其间的思路令人回味。
音乐节最后以“百老汇经典音乐剧《红男绿女》”作为“压轴”。从上述有关古典传统如何获得当代生命的角度看,这部音乐剧也提供了一份独特的解答。而此剧的情节以劝导人们远离赌博、回归传统价值为中心展开,针对澳门这样一个以“博彩业”著称的城市,不免具有一丝温情而有趣的讽刺。这部初演于1950年的经典剧目,音乐风格具有典型的二十世纪中叶美国百老汇气质,和声语汇、分曲结构和乐队编配均以传统为基础,但旋律、节奏和演唱则大量吸收美国本土的舞厅音乐、爵士音乐以及流行音乐元素,由此显得生动、悦耳、鲜明而活泼。虽然该剧的人物塑造、戏剧冲突和矛盾解决以传统的戏剧(或歌剧)的标准衡量,未免显得有些简单,但好听的音乐与地道的百老汇风味足以弥补一切,令观众在微笑乃至欢笑中心满意足。
当然,音乐留给人的,也许不仅仅是欢笑和愉悦。如果音乐在提供娱乐的同时,还升华为文化与艺术,那就可能要面对一些并不轻松的话题。如何面对,又怎样处置,可能并不仅仅是音乐家的课题,从某种角度看,其实这是全社会共同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