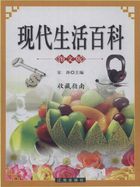也许是上述多少显得“另类”的节目给笔者的刺激较为强烈,音乐节中往往最为抢眼、为普通乐迷最为看好的几场大牌交响乐团音乐会,在我听来却“兴奋度”偏低。最具号召力的乐团当推来自汉堡的北德广播交响乐团。11月1日,这支大名鼎鼎的乐队在世界级指挥大师埃申巴赫棒下献演一场典型的交响音乐会——一首序曲(贝多芬《爱格蒙特》)、一首协奏曲(拉赫玛尼诺夫第三)、一部交响曲(勃拉姆斯第一)。曲目相当保守,均属重磅杰作,反倒显得表演在总体上平淡无奇。演出过程中乐队还出现不少细节问题(如圆号在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第一乐章第二主题处“冒泡”,弦乐的起音多处不齐等等),让人扼腕。这应验了老一辈德国钢琴大师施纳贝尔的名言:“伟大的音乐杰作总让所有具体的演奏相形见绌。”比较而言,名不见经传的卢森堡爱乐乐团和其首席指挥托维的表现更有可圈可点之处。该团地处法语文化圈,为配合2003年世界范围内纪念著名法国作曲家柏辽兹诞辰二百周年,两场音乐会均以纪念柏辽兹冠名,自然也都包括柏辽兹的大作。10月28日晚的音乐会以柏辽兹的《罗马狂欢节序曲》打头,次日的音乐会以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收尾。该乐队音响平衡、音色细腻,显示了很高的专业素质。托维显然是一个精于排练、头脑清醒的“学者型”指挥家,完全知道需要什么效果以及如何带动乐队实现所要的效果。不过,面对经典曲目,仅以职业乐队的水准顺利完成,相对缺乏独特风格和诠释力度,在笔者听来总觉过瘾不足。特别让人大跌眼镜的是,10月29日晚享有国际盛誉的大提琴家麦斯基与卢森堡爱乐乐团合作演出舒曼的大提琴协奏曲。该作品写于作曲家晚年精神失常之前,尽管某些局部富于舒曼特有的诗意,但灵感水平高低不匀,音乐气息连贯欠佳,必须依靠演奏家和乐队的协同努力才能达成有说服力的演释。但遗憾的是,麦斯基当晚似乎不在状态,心理紧张,技术变形。从演奏难度说,舒曼这部协奏曲对于大提琴独奏的要求并不过分,然而麦斯基完成得相当勉强,不仅“吃掉”很多经过音,而且音色干涩嘶哑,令人“憋气”。
整个音乐节中,10月31日的音乐会是中国器乐的唯一专场,由澳门中乐团和中国歌剧舞剧院民族乐团联手推出。或许是个人偏见,笔者一直对所谓“民乐队”的组团原则和理念持有异议,对民乐队的整体审美追求也有保留。指挥彭加鹏先生看来是恪尽职守,两团合并的民乐队在他的调教下,音准、平衡和协作都当刮目相看。所演曲目几乎全部出自现当代大陆作曲家之手,有些已进入“经典”行列,如前辈名家彭修文改编的《瑶族舞曲》。笔者较感兴趣的自然是较新近的创作——如王建民的《第一二胡狂想曲》和赵季平的交响组曲《大红灯笼高高挂》。前者其实已得到专业圈的公认,因其具有突出性格的乐思运作和对独奏乐器性能的出色发挥(尽管在结构布局上此曲掉入似曾相识的套路——引子、入题、发展变奏、推向高潮、收尾等等),后者改编自作曲家本人的电影配乐,极有创意和“想法”,但因原来是非“纯音乐”构思,难免有些先天不足(尤其体现在结构欠完整,乐章段落的转换和结束略嫌粗疏)。其他作品或多或少都属于原有民乐队曲目的传统审美范畴,或是渲染热闹音响,或是改编民歌音调,艺术思考上未免显得过分简单。
以当今世界上炙手可热的华人作曲家谭盾的合唱剧《复活之旅》作为最后的压轴演出,这是本届音乐节的一个突出亮点。有关这部作品的深度评说,笔者另有专文理论(请见“跨时空对话:谭盾的《复活之旅》观后”,载《人民音乐》2004年第1期)。该作完成于2000年,原为纪念巴赫逝世二百五十周年而作,系由德国斯图加特的巴赫学术院委约,剧词由谭盾本人根据《圣经·新约》中的《马太福音》改写,叙述耶稣受难随后复活的传奇,是为谭盾笔下的《马太受难曲》(此即作品的英文原名)。作曲家考虑到国人的接受习惯,在此次澳门演出时更名为《复活之旅》。主办方选择这部奇特作品的中国首演来为本届音乐节收尾,无论从什么方面考虑都是极其恰当的举措。如笔者所言,“澳门作为西方宗教文化传入中国的‘桥头堡’,作为国内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重镇,首演谭盾这部以东方人视角体察西方宗教故事的新作,确乎再合适不过了。”作曲家再次有意凸现他近年来刻意追求的“多文化对位”和“跨时空对话”原则,以佛教的超脱和轮回理念诠释基督教中有关“耶稣受难”这个处于中心地位的叙事和寓意,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作曲家所选择的音响手法和视觉手段并不刻意复杂,有些甚至是似曾相识——如几乎已成为谭盾近年创作标志性风格要素的“石歌”(石块敲击的节奏运用)、“水乐”(对水声表现力潜能的多方位挖掘)以及“多媒体”(视觉屏幕对音乐的支持和渲染)等等,但对观众造成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由于该作品具有实质性的戏剧内容,加之基督受难故事中隐含的“普遍人性”意义仍具有强大的心理效应,因而使谭盾历年来常遭人非议的形式处理手法和音响效果获得了有力的内在支撑。11月2日夜,该作在澳门标志性建筑“大三巴”教堂遗址前举行露天免费公演,大获成功。谭盾的这部重头戏为整个第十七届澳门国际音乐节的“曲线造型”画上了圆满而漂亮的句号。
音乐节的盛筵过后,留下一些让人不吐不快的感慨。以澳门原本的音乐基础和文化储备,很难想象由这座小城所创办的音乐节会达到今天这样的规模和水准。自1987年开始,每年一届,坚持不懈,这其中体现出的是对城市内涵的关怀,对音乐文化的承诺,以及对市民素质的呼唤。
回到本文开头的话题。都市文明的形成以及成长,依靠的是人口的聚集、利益的驱使以及随之而来的商业、贸易、交通、房产等方面的拉动。但是,当白日的喧哗散去,工作的劳顿停息,都市人的精神和心灵在何处寻觅休憩?都市人的烦闷和困惑又在何处获得慰藉?难道只是依赖酒楼茶肆的觥筹交错?或者仅是企盼电视机屏幕中的感伤或嬉闹?当然,尚有“博彩”的刺激和灯红酒绿的消遣可供选择,但在内心深处的终极支持上,现代的都市人其实面临着巨大的真空。
正是在这一点上,文化建设和文化事业,特别是所谓“严肃”文化和“高雅”艺术品种的培育与发展,对于一个城市的精神塑造几乎是性命交关的。没有文化内涵的城市,必然堕入浅薄乃至畸形;缺乏艺术生活的都市,必定走向庸俗乃至腐败。人们常以“俗不可耐”形容缺乏文化教养的“小市民”,而一个城市如果缺少文化底蕴,不知又该用什么词语予以写真?
故此,举办澳门国际音乐节的用意和主旨昭然若揭。“为澳门居民提供高雅的文化艺术,提高澳门的整体文化素质,提升澳门文化城市的形象”——澳门国际音乐节的宣传资料如是说。通过连续十七年的努力,澳门国际音乐节现已成为中国乃至亚洲最有影响的音乐节品牌之一,值得庆贺。听主办方介绍,最初举行音乐节时,出票非常困难,因为本地居民当时尚无出席音乐会的爱好和习惯。如今,平均出票率已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且在一般情况下均不设赠票。澳门国际音乐节已经步入良性循环。
应该特别指出,政府部门——特别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在这其中发挥了中心的主导作用。整个音乐节由澳门文化局全权操办,每年斥资上千万之巨。由此保证了该音乐节在节目质量上的高品位、高规格,保证了音乐节管理运作的专业化、职业化,此外还保证了整个音乐节演出票价的低价位以吸引普通市民观众。走在澳门的街头巷尾,随处可见国际音乐节的广告牌和招贴画,统一设计的图案,朴素大方的标示,给这座城市增添浓郁的音乐气氛。开演之前步入演出场馆,所有座椅上摆放着精良的节目单介绍,以中、葡、英三种语言印制,免费赠予观众。尤其令笔者感叹的是,本次音乐节充分利用澳门的教堂建筑资源,所有教堂中的演出一律免费向公众开放(提前排队领票)。本届音乐节的免费演出居然高达九场,占音乐节所有节目的整整一半——这意味着澳门文化局对这些演出场次成本的“大包大揽”。凡此种种,反映出澳门政府的全力投入,反映出管理部门的精心策划和细致操作,更反映出澳门人对音乐节的珍视与呵护。
在澳门期间,每当音乐会结束,在返回住所的路途中,总远远望见闻名遐迩的大赌场“葡京大酒店”华灯齐放,光怪陆离的霓虹灯将半空映得透亮妖娆。我每每生出一丝困惑,不知何处才是真切的现实,是刚才听到的音乐声,还是眼前的花花世界?或许这恰是现代都市文明的真实写照——人性潜能的立体展开和多重文化的复合叠置。笔者不敢妄言,音乐能够给澳门带来什么,澳门人在聆听音乐之后又会得到什么。音乐可能只是一种希望,一个暂时可以摆脱凡俗缠绕的“乌托邦”,一座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但又时时刻刻伴随着我们的寄托“神龛”。或许只有当人的内在生命苏醒时,他(她)才真正需要音乐雨露的滋润。同理,或许只有当一座城市的精神生命进入某种自省境界时,它才会觉悟音乐(以及艺术和文化)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