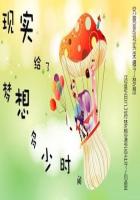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问世至今已整整五十年。一曲“蝴蝶”,飞遍全球(特别是华人世界),不仅是作曲家(何占豪、陈钢)和首演者(俞丽拿)的骄傲,也是上海音乐学院的荣耀,更成为上海城市和中国文化的品牌。前些天,有记者来电采访,希望谈谈该曲风行不衰的原因。暗自思忖,这倒是个值得谈论的话题。
“梁祝”成功的原因也许可分内在与外在两个方面。内在方面大约指该曲自身的素质,可圈可点之处很多。最突出的即是恰如其分的“中西合璧”。从体裁上看,该曲属小提琴协奏曲——一种出自西方的典范类型,但在此却化为讲述中国民间传说的叙事体。以主奏乐器象征主人公的特别用法,在西方音乐的协奏曲中倒并不多见(柏辽兹那首表现浪漫派主人公彷徨心态的“准”中提琴协奏曲《哈罗尔德在意大利》是否可算作先例?),但用在这里显得非常得体合适。从结构上说,这首作品在近半个小时的过程中,采用所谓“奏鸣曲式”这种西方器乐音乐的典型思维架构,甚至还在其中嵌入各个不同乐章类型(慢板、谐谑曲等)的“模板”,其音乐的运思逻辑和梁祝故事的发展脉络之间,的确达至水乳交融,给人以非常“顺”的直感。最令中国听众感到“舒心”和“悦耳”的,是贯穿全曲的中国江南音乐元素——这主要体现为来自越剧的优美、温软曲调,以及众多戏曲音乐中的唱腔和手法,诸如“紧拉慢唱”、“哭腔”、“滑音”等等。总之,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可谓艺术创造领域里“西体中用”的成功范例——如同那首著名流行歌所唱,“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这,保证了这首作品一方面在现当代华人圈中获得认同,另一方面则有可能藉此超越华人世界而迈入更广大的时空。
以外在原因论,“梁祝”的成功取决于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现实,也取决于国人常道的“天时、地利、人和”。该曲诞生的年代,是新中国环境中民族自豪感和集体意识处于高涨澎湃的时代。民间的传说,民间的素材——“民间”作为“人民”和“群众”的化身和符号,它本身就带有某种不言而喻的正确性和优越性。常听说,“梁祝”的创作应该归功于集体的智慧和集体的力量——当时的主创人员何占豪、陈钢,当时的上音领导如孟波、丁善德等,当时的上音师生如刘品、丁芷诺等,均在“梁祝”诞生的功臣之列。这恐怕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也是当时那种特有的创作氛围的真切写照。“梁祝”成于斯,长于斯,它的清纯和烂漫,它的率真和深切,其实不自觉间深深镌刻着五十年前那个时代特有的印迹。就这样,“梁祝”的优雅乐声带着时代的特殊烙印,一路走来,即便在“文革”十年中,它也没有真正消失过——通过各类“地下”的流传,通过人们心中的记忆。
五十年之后,“梁祝”依然风行,但催生“梁祝”的时代环境和文化条件已经改变。因此,有针对性的问题,可能就不是为何不能再出现另一个“梁祝”,而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中,如何催生能够代表中国、又具有世界意义的优秀创作。应该指出,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同时具备中国气派和国际号召力的优秀音乐新作其实已经而且正在出现,尽管数量可能并不太多。但由于各种复杂的社会文化原因,这些优秀的中国音乐创作尚未达到(恐怕也不可能达到)“梁祝”的风行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梁祝”的成功是无法复制的,因为我们已经无法再回到五十年前的时代。但正如“梁祝”是时代的产物,如何感悟、认识和理解我们自己的时代,可能这是当代优秀创作之所以产生的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