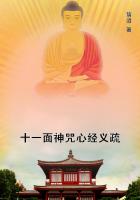笔者在本书的研究过程中,愈发认识到中国古典舞手舞的丰富性。它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下,形成了形式独特、内涵丰富的风格。兰花指、单指、掌等等与戏曲文化、宗教文化密切相关的手形,在中国古典舞的训练及表演过程中被大量的使用,反映出戏曲文化、宗教文化与中国古典舞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引发了笔者对文化演变、艺术融合的深入思索,对这些问题,本书试做一个分析。
一、石窟造像及出土文物中手舞动作的分析
敦煌石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宝藏,也是人类文明的珍贵财产。自公元111年,汉武帝派霍去病率大军击败匈奴,开通了河西走廊,从此,开启了敦煌文明的大门。到了唐代,敦煌地区民族交融、商贸发达、人文荟萃,当地聚居着汉、藏、印度、波斯、朝鲜等各民族的人,他们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惯、文化背景、宗教信仰,但在敦煌大家和睦共处,这也为敦煌特有的文化资源提供了有利条件。敦煌特有的人文环境和地理位置,为中原与西域的乐舞交融提供了一片沃土。当时在敦煌地区,因特殊的人文环境,歌舞除了吸取汉朝改编自民间的清商乐舞外,也融合了当地的民族民间舞蹈。这种特殊的文化背景产生的舞蹈风格在我国的舞蹈史上成为极其夺目的一个部分,许多学者在敦煌乐舞的研究上都投入了许多努力,我们可以在前辈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思考与探索。
敦煌研究院的郑汝中,多年来投入在对敦煌壁画乐舞形象的研究中,据他多年来的调研统计,仅莫高窟绘有乐舞形象的洞窟有240个,乐舞形象有3400多身(其中乐伎形象居多)。根据敦煌艺术史学家研究,敦煌壁画舞蹈图像大致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早期——北凉及北朝时期,中期——隋、唐时期,晚期——五代、西夏、宋、元时期。三个时期的壁画中的舞蹈形象在同一风格的基础上又各有其特点,早期舞蹈形象多为单身的乐舞动作,很少有多人协作式的场景,构图比较单一,人物形象体态较粗壮、动作较奔放,与中原人物穿着、体态、姿势有很大不同,呈现出西域及北方游牧民和印度这样的混合风格。中期随着隋、唐经济贸易的发达,带动人文文化的变化,壁画上的舞蹈大多气势宏博,以巨幅经变画居多,题材不再像早期那样单一,多民族的元素体现在这一时期的壁画创作中。到了晚期,总体在创作上是呈现衰败趋势的,在画工、构图、形象上是沿用中期的,并无创新,以致艺术感染力降低,但是在今天看来仍旧具有一定的观赏性。关于敦煌壁画舞蹈形象中手舞的部分现今并无专门研究,本节筛选了部分壁画中手部比较清晰的图片进行个案分析研究。在历经岁月的磨砺之后,壁画中舞蹈形象的留存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资料。在进行手舞专门研究时发现许多部分已经不太清晰,手部本身在壁画整体中就是极其细腻的一个局部,经多年风化和其他原因,可以完整保留下来的并不是很多。但是从现存的可以辨析的资料中,仍旧能够发现敦煌壁画中手舞研究的无限空间。在现有相对完整的舞蹈形象和通过线描还原的舞蹈形象中,可以看到敦煌壁画中手舞的几个基本状况。
敦煌壁画中的舞蹈丰富多彩、风格统一却种类繁多。由于地域文化的特殊性,使舞蹈种类较为丰富,本书大概将其分为四大类:一、经变画中的天宫乐舞(菩萨如宫娃);二、壁画中的民间、民俗歌舞表演;三、特色鲜明的民族舞蹈(胡舞);四、童子舞。在这些舞蹈种类中不难发现整个敦煌的艺术创作受到佛教文化的巨大影响,对其中内容的理解很难与佛教文化割裂来看。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也是其重要特点,如印度、波斯、藏族、朝鲜族等等,使得壁画中的舞蹈形象与当时中原地区的舞蹈形态、服饰、动作、意蕴都有着较大的差别,从而形成了敦煌舞蹈文化独树一帜的风格特色。晚唐时期所绘的,这是整图的一部分,为莫高窟第85窟有大型乐队伴奏的巾舞。此舞人在中间翩翩起舞,两侧各有八人的伴奏乐队,演奏的十六种不同的乐器。正在表演巾舞的舞人身体呈现S型,服饰与中原舞伎截然不同,带有强烈的印度佛教色彩,看似赤裸的上身、包括头部的头饰都显然不是中原文化的产物。整体看来,除了佛教文化元素以外,还带有强烈的西域少数民族的风格特色。舞人双臂挽搭长巾,右臂抬举,左臂侧展,形成一个自右至左由上至下的流线线条。再来细看舞人的双手,双手各自有不同的手形,都持有长巾。关于敦煌壁画中的长巾舞,笔者一直觉得像谜一样神奇。其中特别能引起注意的是,它与中国古典舞中所见的长绸舞不同,敦煌舞人都是双手直接持巾,而中国古典舞继承的是中国戏曲中的方式方法,看似长绸直接在手,可是舞者手中持的是一根短小的木棒上连接着一个几公分长的麻绳鞭子,因为木棒和鞭子被隐藏在长绸中,这个部分观众是看不到的。这个木棒和鞭子起到舞动绸子的技术性功能,三米多甚至更长的绸子有了木棒鞭子的辅助,在舞台上就可舞动自如,如虹般美丽。专业舞者可以很容易就辨识出敦煌壁画中的长巾舞形象是双手持巾,巾中没有木棒和鞭子,只是长长的长绸。壁画中舞人的舞动相当自如,舞人双手直接抓着长巾,长巾除了有一部分在舞人的身体上披搭,从手到两端的末梢都被舞人舞动了起来,好似祥云一般。舞人右手的手形,大拇指与中指相应但不完全捏合,无名指向手心方向弯曲,小拇指翘起,食指放松弯曲。这个手形可以在佛教手印的千手观音印中看到,即“杨柳枝手”,与莫高窟第85窟舞人的右手手形是一样的。舞人左手,手心向上,大拇指伸直,食指、中指、无名指依次向手心方向弯曲,无名指最接近手心,小拇指翘起。此手形与千手观音手印中的“白莲花手”手形相同。这张壁画中舞人的手形在佛教手印中可以找到。在此可以做一个推断,在画师创作壁画中乐舞形象的过程中,一定有现实的资料进行描摹,所以,这幅乐舞的壁画当中舞人形象可以说是有史料或其他途径记载,通过画师再创作产生而来的。这张壁画是在动态当中的,所以舞人的动作一定是随着舞曲的节奏在变化的,包括手形和手舞的部分都是这样。可是在这幅壁画中可以看出舞人的动作是一个舞姿,也就是说是带有停顿性质的一种姿态,笔者判断姿态停留时间极短,是通过地面绸子的状态,如果不是短时间的舞姿,绸子不会是在舞动状态。这样又可以进一步说明一个问题,在舞动的过程中,舞人的手舞不但起到功能作用,即完成舞动绸子的技术,还带有很强的审美作用,即手臂线条流线给观者带来的美感;手形的细节带有一定的符号性与语义性传达,这个特点也明显地体现出来。当然,在敦煌壁画舞人的形象当中,也可以看到不是完全以符号化出现的手舞部分,有些壁画当中舞人的手部是在动作过程中,介乎于有形和无形之间,可是仍旧不乏传达特有文化内涵的意义。
再来分析榆林窟南壁第25窟的腰鼓舞。鼓乐是祭祀、宴乐歌舞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腰鼓是传自少数民族地区的乐器,在民间腰鼓舞由来已久,《旧唐书·音乐志》记载“九部乐”、“十部乐”,其中的《西凉乐》、《高丽乐》、《疏勒乐》、《高昌乐》,均有腰鼓做伴奏乐器,虽然中原出土的舞俑和墓室壁画中没有出现“腰鼓舞”的形象遗存,但是在这部分文献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腰鼓舞久远的“身影”。敦煌壁画中,唐代经变画中各式腰鼓舞的形象是出现比较多的,榆林窟第25窟的腰鼓舞形象就是其中之一。这幅壁画是中唐时期所绘的《无量寿经变画》中单人的鼓舞场面。舞者两侧有八人伴奏,分别使用箫、横笛、排箫、方响、海螺、筚篥、笙、琵琶八种不同的乐器奏乐,想必旋律与节奏都会相当丰富,为腰鼓舞者的舞蹈提供了极其有利的因素。有趣的是在舞者左脚下方有一人首鸟身的伽陵频迦在弹奏琵琶,并且舞者的眼睛好像正看向它,整个画面和谐生动、不失灵性。腰鼓舞者动感十足,身上除了腹部挂着一只腰鼓外,双臂自肩而下一对长绸,长绸虽不在手中,但自肩而下自行舞动。舞者右脚着地,左脚吸起,并且左脚拇指是与画中手部动态协调用力翘起,形成手舞足蹈之式。舞者似男性,体态稍显臃肿但不失舞者气质,他身穿收腿宽裤,赤裸上身,手臂与颈部有所装饰,手舞的姿势急剧动感,双手十指张开。好似要再次击鼓,手臂在对称鼓面的高度平行拉开自肩至手是一个稍许的弧形,这个上身舞动的姿态很具少数民族舞蹈的动态特征,比如蒙族舞蹈、藏族舞蹈等等,在这个舞者的动作上好像可以找到同样的动作元素。在这幅壁画舞者的手舞中,首先看到的是动势所带来的一个舞姿的状态,舞姿也是在动作过程中的,所以无法不去将壁画中舞动动作的瞬间与舞蹈本身联系起来看。舞者的双手姿势是相同的,在画面中可以分析出这段舞蹈的表演一定伴随着击鼓,那么这个舞姿就好似舞者连续击鼓当中的一个动作,从手臂的动势来看,舞者双臂张开应该是上一个击鼓结束正准备下一次击鼓,手形呈现出张开的动势和击鼓动作的用力很有关系,所以手部的姿态一定不是摆出来的,而是在完成连贯性动作当中的一个手舞状态。
再分析莫高窟第156窟南壁,与长鼓者对舞的反弹琵琶的舞伎。在敦煌壁画中,反弹琵琶的舞伎形象是十分著名的。在20世纪80年代舞剧《丝路花雨》中,编导抓住这一特色的舞蹈形象在舞台上创造了标志性的舞段与舞蹈风格,而在敦煌壁画中的这些反弹琵琶的舞蹈形象,今日看来还是值得我们去再次深入研究探索的。在莫高窟第156窟中反弹琵琶舞伎的形象是半蹲姿势,所以足蹈的部分省去,集中关注手舞。画师绘出的是舞者的背面,舞者半蹲反背琵琶的正面与伸臂按弦的左手,还有正在拨动琴弦的右手是在画中极其凸显的部分,手舞的部分在整幅壁画中占据的是首要的位置,舞者就是在呈现反弹琵琶而舞的状态。画面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的手形是与榆林窟第25窟舞者双手动势的缘由相同,这幅壁画中的舞者手舞呈现出动作功能性同样是首要的,舞者在弹奏琵琶,所以手部的动作是因弹奏所形成的姿态,不是刻意的符号或语义性表达的手印或手姿。反弹琵琶呈现出其他地方少见的舞姿形态,是以舞者背部角度去赏析舞姿的方式,这幅壁画中的舞者倒持琵琶,半遮面,垂目淡然的表情更是增加了观者无限的想象空间。与常态舞者状态不同的是,半蹲的反弹琵琶舞伎在此处更具静态舞姿的独特风格,再加上手舞反弹琵琶姿势带来的别样舞蹈风格,这幅壁画呈现的内容是在众多敦煌反弹琵琶形象中的一个特例,值得观者细品。舞者手持琵琶常态是在身前的位置,以便弹奏;反弹琵琶的动作除了带有极浓郁的西域风格之外,让人更多想到的是画面本身给观者带来的生动感受。反弹琵琶的舞者弹奏琵琶的技能一定是技高一筹,才可把琵琶放在脑后的位置,不必眼睛看弦也可准确无误地弹奏,并且我们看到琵琶的琴头朝下,琴尾略高,想必在乐舞过程中,舞者尽兴表演手舞的姿态并不是通常可以看到的。除了在这幅壁画看到反弹琵琶的舞姿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壁画中有反弹琵琶的形象,比如莫高窟第5窟中与长巾舞对舞的反弹琵琶舞伎,与莫高窟第156窟南壁的这个反弹琵琶的舞伎就不同。首先,第5窟的舞伎是站着起舞的;其次,第5窟的舞伎琵琶琴头朝上,琴尾略低。从这两幅不同反弹琵琶壁画舞者手舞所持琵琶的琴头就可以看得出来,壁画当中所绘的舞伎形象都是动态中形象地捕捉。
敦煌壁画中的舞蹈形象琳琅满目,手舞也可做深入研究。相关资料显示:“其中招、摇、送、令、挼、头等,应是代表某种舞蹈动作的术语或程式:犹如现今所谓‘云手’、‘山膀’、‘顺风旗’、‘花梆步’等,敦煌记录舞蹈的写卷,主要是由这类舞蹈的术语组成的。”在此分析三幅比较有代表性的舞蹈形象,这三幅也是手舞部分比较具有特点的,并且画质保存很好,现在还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手部的动作。笔者在查阅敦煌壁画资料的过程中发现,壁画中舞者手舞的线条基本上全部是流线或弧线形的,很少有一个壁画中的舞者手臂出现直线型的动作。另外,在壁画中舞者手舞部分的手形可以在佛教手印中找得到,这点当然和敦煌文化与佛教文化密不可分的渊源有关联,“在敦煌壁画中有一些手势表达着各自不同的含义,……手印代表着某种特殊的寓意,同经文的主题思想相互呼应。”这些不同手形、手印背后隐藏着丰富的文化历史内容,笔者认为每一个手形都如同一个“密码”,它在等待着研究者进一步解读。这些“手舞密码”中蕴含着大量的文化内容与语义传达,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
二、唐代寺庙讲唱文化
研究中国古典舞手舞,唐代的寺庙讲唱文化是不得不提的。因为,中国古典舞中极其重要的一个流派——身韵流派,源自中国戏曲。而中国戏曲的形成,在多种元素的汇流过程中,唐代寺庙讲唱文化带给中国戏曲的影响则是不容忽略的。
佛教进入中国以后,到唐代进入一个快速的发展阶段。初入中国时,僧人诵经模仿的是印度僧人使用梵语,但是使用梵音诵经终觉不畅。所以许多有才气的名师开始思考,将其加以变化,让诵经者更为便利,将从前“用汉曲诵梵文,梵音咏汉语”改为新声,就是吸取中国民间歌曲的调子,这样一来中国化的诵经调,就以其优美的旋律和通俗的形式很快被中国的僧侣与信徒接受并喜爱。佛教文化的传播,诵经是极为重要的一个途径。唐代的寺院为了更好地诵经传教,专门在寺庙中设立了“戏场”,寺院里会经常组织讲唱,一为“僧讲”,一为“俗讲”。这两种讲唱都是官办的,甚至是要经过皇家批准的,是典型的官办宗教宣传集会。中唐之后,寺庙中的宗教虔诚渐渐在淡化,而世俗艺术的氛围在逐渐转浓,音乐舞蹈在唐代以至随后的宋代得到充分地发展,“唐宋大曲的某些名目在宋杂剧、金院本中出现,可以看出杂剧、院本,继承、吸收唐宋歌舞大曲的痕迹”。这时,寺院里出现许多知音善歌的和尚。宋代赞宁《续高僧传·读诵篇》说道:唐代贞元时,和尚少康“所述倡赞,皆附会郑卫之声,变体而作。非哀非乐,不怨不怒,得处中曲韵”。正是唐代寺庙讲唱文化的发展,最终使得中国民俗文化融入其中,广泛吸取民间音乐的营养,为中国戏曲的形成开辟了一条途径。敦煌石室留下了一批话本、词文、变文、讲经文等讲唱本子。而关于唐代寺院讲唱文化的历史记载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线索就是敦煌。公元前60年,西汉在西域设置都护府进行管理,西域从此正式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到了唐代这种经济文化的交融更加频繁,除了经济上的繁荣出现了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在文化上以“龟兹乐”为代表的敦煌乐舞,以其独特的魅力风靡了宫廷和民间。据研究人员在新疆文物中发现,远在中原地区戏曲流行之前,西域已有戏剧在当地流行。德国考古队在我国新疆地区发现了三部梵语戏剧的残破贝叶写本。同时,德国考古队在新疆找到了甲种吐火罗文的《弥勒会见记》残篇,是公元6世纪至8世纪的抄本。1954年4月,哈密县脱米尔维吾尔族牧民牙合亚热衣木在山坡放牧时,发现了石碓中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后经季羡林先生解读鉴定,它是《弥勒会见记》剧本。多个吐火罗文和回鹘文剧本的发现,而且可以推断出,在敦煌文化盛行的西域很早就出现了戏曲文化的雏形。中外学者研究表明《弥勒会见记》的吐火罗文和回鹘文的文献不仅是剧本,而且可以从中看出与中国戏曲十分相近的特点。剧本中有出场人物及演唱曲调,剧中的韵文旁有些标注曲名或调名,甚至标出“马”、“羚”等表示舞蹈的名称。在这种种记载和考证中可以相信11世纪以前,敦煌已经广泛流传弥勒信仰的佛教戏曲,这点毋庸置疑。虽然还原那个时期关于戏曲的完整形态非常困难,但是可以通过分析这种种现象,认识到中国戏曲的形成与中国佛教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中国古典舞手舞的研究不只是看其现象,而是要通过现象看到其背后所承载的文化。在现今中国古典舞手舞中,手形的运用相对比较固定,比如男班训练中多用“掌式”,女班多用“兰花指”,这两个手形都是从京剧中的“生”、“旦”两个行当来的,那么再深究下去,京剧中的“兰花指”又是从何而来呢?本文通过以上的文献梳理暂且推断京剧的兰花指和佛教手印有直接关系,并从中可以看到中国戏曲形成的另一个脉络线索。在11世纪的西域,已有《弥勒会见记》这样的戏剧文本,唐代寺院讲唱过程中是否也融入了戏剧戏曲的表演方式?为了可以更为广泛的传教,从起初用梵文诵经到融入中国民间曲调诵经是产生巨大变化的,这在当时对于信徒来说也是一件很实惠的事情,越来越多的人都可以听得懂,并且一旦融入音乐,动作就会自然而然的随之产生。试想一个僧人在诵经的过程中,有说、有唱,要表意时,经文通常会讲和宗教有关的故事,为了让信徒更加明白,自然会加一些艺术化了的生活动作,而最先产生的动作应该是手部的,即最初的手舞。大唐文化繁荣昌盛,当时由于经济贸易的繁荣,各地区民族之间的交流是十分频繁的,这一点西域地区可称典范,尤其是敦煌地区更是如此。西域的音乐舞蹈涌入中原,当时对中原的乐舞影响颇深,一些胡人的胡旋舞、鼓舞、包括西域地区的服饰都使得中原文化在那样一个历史时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戏剧艺术随着这股浪潮也流入中原,并且随着佛教文化的到来,寺院讲唱文化的本土化深入使得中国戏曲在此生根。西域学、敦煌学的研究成果证明,许地山先生和郑振铎先生等提出的中国戏曲文化来自梵剧的观点,是有一定根据的。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有许多是在很多地方常见的,比如飞天的形象、佛陀的形象、胡人起舞的形象、百人乐舞娱佛的场景等等,还可以在这里查找到戏曲文化的踪迹。在莫高窟的经变绘画中,尤其是“净土变”,可以清晰地看得到表演歌舞伎乐的平台,形状与传统的戏台十分接近。如莫高窟第61窟,是10世纪中期(五代后期)所绘的一座一面观的戏台。戏台上绘有三人正在表演,演员着汉装,正中一人双臂张开,平行伸出的手臂上穿有长出手臂的汉服袖子(手臂平伸,袖子垂下,看不到双手)。右侧一人汉服为腕收口,可见双手,此人左手轻轻抚左耳,右手与右肩位置,好似作出在“听”的动作。左侧一人汉服与右侧人的相同,无长袖,可见双手,此人好似双手合十,举至胸前。在莫高窟的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这样的舞台上表演在中唐以后的寺院已经是有据可寻的事,而且看到这样一个舞台表演的内容与形式一定是相对固定或受限的,很难想象汉代的百戏在此上演,因为演员在这个舞台施展不开,那么适合在这样一个舞台表演的可能就是寺院讲唱过程中所形成的表演性的歌舞和戏曲。讲唱的目的是为了传播佛教文化,虽然后来“俗化”过程中也产生其他内容,可是起初是以诵经为目的的。僧人在诵经过程中起初都是坐姿,到了后期“边讲边唱”,也就不完全都是坐姿。发展到有一定“戏剧结构”和“戏曲元素”的阶段,手舞的动作自然而然就会产生。
就好像平时的表达中,为了更加生动地把故事讲出来让他人理解,讲的时候手部会不自觉地跟着语言“比划”,而这时手部的动作是配合语言表述所产生的,并带有一定的“肢体语言表意性”。在寺院讲唱文化中,这种手舞的存在是无法否定的,并且在诵经表演过程中,僧人或说唱表演者们渐渐地会像修饰语言和选择音乐一样来考量自己该做什么样的动作。那么,在这个前提下,生活形态的动作加以艺术化的处理,再加上诵经传教的特定意义,在寺庙中佛陀泥雕和各种壁画当中的形象就会成为他们模仿的对象。所能分析的第一位就是关于“手舞”的模仿与再创造,因为边讲边歌的表演形式决定表演者不可能有大量足下的步伐与跳跃动作,同时寺院佛陀形象多半为坐姿和直立站立姿态、足下无太多变化,而手部的手形却是极其丰富;表演者有了讲唱的内容、视觉上可参照的模仿对象,在讲唱的过程中自然也就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动作风格与形态,在当时一定是少见或说是首创的一种舞蹈形式,只是放在寺院讲唱过程中,无人把讲唱过程中所出现的舞蹈动作独立开来看。而这种不同于中原宫廷舞蹈、不同于民族民间舞蹈、不同于西域外来国家舞蹈的舞蹈形式,可能就是中国戏曲中戏曲舞蹈的雏形。这种舞蹈以上肢动作为主,配合下肢步伐;带有审美性的同时,注重手姿动作的语义性表达,在部分手舞动作的过程中,可以看到许多生活常态元素的艺术化表达,还可以看到佛教文化中特有的、生活中不会出现的手形与手臂姿态,这两大元素共同构成寺院讲唱表演中的舞蹈特性。今天虽然无法去完全还原唐代寺院讲唱文化当中的“手舞”动作,但是通过种种分析与历史记载不难看出,在唐代寺院讲唱文化中已经蕴含着的手部动作元素,这对后来中国戏曲的形成,进而对中国古典舞的形成都是不可不问的重要历史脉络。在探寻舞蹈肢体语言所蕴含的文化时,要注意不能要只看已形成的动作,还要去探究动作从何而来,具有怎样的动作符号体系。在中国古典舞的形成过程中,戏曲舞蹈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中国古典舞动作元素的文化含义是需要探索和开发的,而不是局限在戏曲的框架当中。中国古典舞手舞的研究是以点带面,通过探讨诸如“唐代寺院讲唱文化”这样的脉络,展开眼界,发现关于中国古典舞手舞的更多文化根基与发展空间。
三、《千手观音》的个案分析
在开始关注到中国古典舞手舞这个研究方向时,除了舞蹈教材中现有的手形之外,佛教中的手印也是一个重要的线索。2005年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千手观音》使很少关注舞蹈的百姓将目光聚焦在了舞蹈上。在第三届国际芭蕾舞邀请赛的开幕式上,看到之前由高金荣编创的《千手观音》后,进一步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与思考。“千手观音”这个题材被许多艺术创作者所关注着,而如何将其呈现在舞台上却有着不同的方式。在佛教中有十三宗,每一宗中都有相同并异同的佛教文化,在收集佛教手印的过程中发现,佛教手印的资料不计其数,决定筛选资料的原则,是佛教手印中哪个部分可以与中国古典舞现有的资源有最直接联系。所以,在遴选了大量资料以后,锁定了“观音千手的印象”即“千手观音”。
“观音”,这个称谓相信很多人都不会觉得陌生。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观音菩萨”最早是以男性形象被中国的信徒所认知,也有观点认为“观音”是雌雄同体。佛教《悲华经》记载,观世音是古印度删提岚国转轮圣王无诤念的长子,名叫不旬,与文书菩萨、普贤菩萨是亲兄弟。“观世音”的称谓得来是他向佛祖许下宏愿,望生下大悲心,断绝众生苦难和烦恼,使众生常享安乐。但佛教文化由印度传入中国后,经过中国文化的“洗礼”逐渐形成了颇具中国意味的佛教文化体系,与印度佛教虽然是一脉相承,但是却有不同。在这个逐渐变化的过程中,“观音”的形象也就由男性转为了女性。“观音菩萨”在中国人心中时常会被称为“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在百姓心中,有任何事都要去祭拜观音以求平安,并且观音在中国人的佛教文化中承载着求子的意向,在印度的佛教中观音是不具有这样的符号功能的。自东汉初年,观音被中国信徒冠以劝善救人、行医送子的菩萨,在印度佛教中,观音有三十三种化身,在中国文化与礼教的同化过程中最终由三十三个化身中的女性形象落定,而且在中国“大多时候,观音以女性的面貌出现,有时她代表着强大的力量,以千手观音的姿态出现,有时被孩童围绕,有时在如雨的花瓣中漫步,手持柳枝和玉净瓶,裙摆飘逸,身后跟随着那些虔诚的灵魂,观音引导着他们去往西方净土”。中国佛教中“观音”的形象除了菩萨特有的神性特征外,还具有女性特征所特有的美感。观音手中是常持物的,很少有全徒手的时候。观音左手持白色长颈瓷瓶,内放绿色柳条一支;右手常以五指并拢指尖立起向上,放置胸前,施法时会用右手拿起瓶中柳条,故左手持瓶,右手持柳。关于“千手观音”的传说,宋末元初,《观音大士传》出台:观世音出生在西土,名妙音,为父亲妙庄王的第三个女儿,因不同意父亲为她择偶被逐出家门。后来,父亲妙庄王得了重病,危在旦夕,妙音化作老僧指点父亲:“非至亲手眼方可医治。”父亲恳求长女和二女儿为他治病献手献眼,可两个女儿无一答应,父亲遭到拒绝。老僧说:“香山仙长济度生灵,求她助你。”果然,香山仙长(实为妙音)慷慨献出手眼治愈了妙庄王的病。妙庄王病愈后发现仙长没了手眼,便请求天地让她再生手眼。妙庄王的愿实现了,仙长真的长出了手眼,并且不是一只手、一只眼,而是一千只手、一千只眼。这就是中国传说中“千手观音”的由来。在“千手观音”的形象中,大多见到的都是以坐姿为主,如山西平遥双林寺的千手观音彩塑。塑像清晰可见观音在多手臂形象中特有的手姿、手势,并且值得注意的是手形没有重复姿态。
在多手臂的观音形象中,首先手臂的空间没有重叠,所以在视觉上会以“圆”型“团”状为大体印象,也就是说,多手臂在伸出的位置上由身体的胯部起始,一直排列到头顶,在排列过程中手臂没有重叠。另外,聚焦手部,没有任何一个手部姿态是一样的。在众多手部动作中,手持法器和其他物件的居多,也有少许是徒手动作。在“千手观音的手印”中,被最终确立为“手印”的有四十一种。每一种都有自己的称谓,并有特指的寓意。在四十一种手印中,可以看到手持宝珠的“如意宝珠手”,手持宝剑的“宝剑手”,手持玉环的“玉环手”等等。虽然都是持物手,但在手形上都不同。在佛教中,每一个手印不只是一个手部动作,它们都有自己的功能性。比如“如意宝珠手”,所指若为富饶种种功德资具者,当于如意宝珠手。“索手”,所指若为种种不安求安稳者,当于索手。“宝镜手”,所指若为成就广大智慧者,当于宝镜手。在这四十一种手印中,动作本身可以看到动作背后的所指,这点是十分珍贵的。在佛教手印当中,不止是手部动作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更多地从一个肢体语言的符号上了解到关于佛教文化的内容,这是给笔者最大的启示。中国古典舞手舞,如何在审美之外给观者更多的语言性传达和文化性的熏染,是值得投入更多时间、精力思考的问题。在张继刚创作的《千手观音》中,舞蹈的前半部分,充分发挥演员手部动作,即手舞的表现形式,将舞蹈演员身体的局部运用到极致,也就是说,在无“足蹈”的前提下完成“手舞”。为了突出演员手部的动作与线条,导演给每一位演员带上了长达几厘米的假指甲,当二十几位演员排列成一行同时伸出手臂时,已经具有了一般性舞蹈所不具备的特殊符号特征。编导在前半段的手舞中巧妙地运用了演员手臂的顺序排列和节奏处理的变化来使得单一的舞蹈动作被强化。在肯定其舞台效果与美感的同时,不难发现手部本身是没有进行深度开发的。在《千手观音》这个舞蹈作品中,使用最多的仍旧是兰花指。但是,在千手观音的四十一个手印中,实际上并没有兰花指这一手形。但是,如果以开放的思维,考虑到兰花指是中国古典舞女性舞蹈中出现最多的手形这一特殊原因,在创作中使用兰花指是没有问题的,可能是为了追求舞台上的演出效果,强调手臂线条的美感与运动节奏带来的视觉冲击,而在手的局部变化上选择忽略不计。但是,就一个舞蹈作品的文化性上,保证审美的同时,也可以做到一种文化语义的传达。千手观音四十一种手印当中,徒手手印只有三种,即“施无畏手”、“合掌手”、“顶上化佛手”,后面两个手印都是双手势,这是千手观音手印四十一种当中仅有两个双手势的手印。四十一种手印中方位的变化不是特别多,有四十种手印都是掌心向上,以“托式”居多,手腕的用折腕,也有少许立腕,如“葡萄手”、“合掌手”、“宝镜手”。在这些手印中唯一掌心方位向下的是“青莲花手”,也是它独具变化的方位,使得“青莲花手”在四十一种千手观音手印中别具一格。在千手观音的手印中有三个莲花手,分别是“白莲花手”、“青莲花手”、“紫莲花手”。三个莲花手,三个不同的手形,在不同手形的背后,它们各有所指。所指若为各种功德者,当属“白莲花手”。所指若为面见一切十方诸佛者,当于“紫莲花手”。
手形方位与其他手印不同的“青莲花手”所指为求生十方净土者。与“白莲花手”和“紫莲花手”不同的是,在寓意中“青莲花手”有“求生”旨意在其中,与“为功德”、“见诸佛”的寓意更具切实的生命性质在其中,“白莲花手”、“紫莲花手”掌心向上更具对佛陀的崇敬仰望之意,掌心向上的肢体语言更多传达的是顺从、敬仰、赞美,手部方位可看出是完全无防卫状态的一种肢体语言传达。而“青莲花手”掌心方位是向下方的,在这样的方向动势下会出现一种压迫的状态,关于寓意“求生”这一核心所指,不难理解生存是人类的基本需要,所以在青莲花手的手形呈现上所看到的是与其他千手观音手印中所不同的一个状态,当然方位的不同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手形方位具有传达语义的作用而言,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存在的,比如在两个国家在进行外交谈判时,双方的手部动作是十分讲究的,外交过程中手部动作的细节,很少会出现双手掌心向上的时候,很多在谈判过程中都会是双手掌心向下按着身前的桌子,呈现的是一种防卫的状态。如果双手掌心摊开向上,在肢体语言上我们就可以判断是一种妥协、顺从的状态。再分析四十一种手印的“甘露手”,这是在掌心向上的四十个手印中又稍有不同的一个手印,“甘露手”掌心向上,指尖向下。在这个手印的动作动势上,很容易发现“给”这个动词的意思。“甘露手”是指若为一切饥渴有情及诸饿鬼得清凉者,当于“甘露手”。在佛教中,常听一词“施舍”,甘露手的寓意具“施”这一动机。在《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姥陀罗尼身经》则说有十八臂之说,经中说:“面有三眼,臂有千手,于千手掌各有一眼,首戴宝冠,冠有化佛。其正大手有十八臂,先以两手当心合掌,一手把金刚杵,一手把二戟叉,一手把梵夹,一手把宝印,一手把锡杖,一手把宝珠,一手把宝轮,一手把开放莲花,一手把罗,一手把扬枝,一手把数珠,一手把澡罐,一手施甘露,一手施出种种宝雨,施之无畏,又以两手当脐,右押左仰掌,其余九百八十二手,皆于手中各执种种器杖等印,或单结手印。”在经文记载中,千手观音的手印是十分具体和细致的,观音手印中无一完全相同的手印,使笔者愈发觉得手舞的空间一定是巨大的。就一个千手观音手印内容就足以让我们震撼。图片中手印的呈现上是二维的方式,而舞蹈的呈现是一个四维空间的综合方式,也就是说会比图片本身更丰富并且可发挥创作的空间也更大。张继刚老师创作的舞蹈《千手观音》是在兰花指这一基本手形上展开的,如果有千手观音四十一种手印作为手的基本姿势来进行创作,首先在动作元素上就会产生更多的可能性,并且在舞蹈本身的文化传达上会迈进另一个层面。肢体的运用有不同的方式,而且这些方式都有其存留的意义,文化因素就是尤为重要的一种,“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来看,我们的运动人体在各自的文化语境中,都具有了某种情感信息甚至是具有了确定无疑的‘语义’。从完形心理学的视角来看,我们的运动人体又可能与历史文化陶塑的人类心理结构产生某种对应”。在中国古典舞手舞的资源与开发上,应敞开思维去考虑创作当中、教学当中对学科发展有利的元素。在教材训练精进、提纯的前提下,如何使得中国古典舞的动作素材、文化积累丰富起来,也是不可忽视的研究内容。以张继刚老师创作的《千手观音》为例,思考、收集整理佛教手印中千手观音四十一种手印,不难发现,动作的素材、文化的依据不是创作者个人凭空想象出来的,如何发现与创作题材吻合的资料与素材是对创作产生直接影响的一大因素。
仔细观察千手观音四十一种手印,有许多持物手形十分相似,但又各自不同,在手印的动作细节上相当细腻。以“如意宝珠手”与“宝钵手”为例,这两个手印看起来很相似,可区别也十分明显,关键就在大拇指。都是手持宝珠,所以掌心向上,食指、中指、无名指略弯,小拇指翘起近乎伸直,“如意宝珠手”的大拇指是弯曲与食指、中指、无名指一起握住宝珠;“宝钵手”的大拇指是与小拇指对称,基本伸直的姿势。在两个手印的寓意上也是完全不同的,“如意宝珠手”是与愿观音,丰饶资具。“宝钵手”,若为腹中诸病苦者,除腹中病。再来看“金刚杵手”与“宝弓手”,手形都是后三指曲回握住,大拇指和食指相捏,使得大拇指和食指中间有半圆形的空间。不同的是“金刚杵手”食指捏合在大拇指的指关节上,“宝弓手”则捏合在两指的指尖位置。“化佛手”与“化宫殿手”这两个手印也十分相似,同样是掌心向上,五指张开呈托掌姿态;不同是“化佛手”五指基本是伸直的,而“化宫殿手”食指和无名指是略弯的。“化佛手”是指若为生生之处不离诸佛边者。“化宫殿手”是若为生生世世常在佛宫殿中,不处胎藏中受身者。在上述三组手印的比较中可以发现,四十一种手印有十分相似的之处,关于手印细节的不同产生的细腻的区别,才形成的千手观音四十一种手印。掌心向上是这组手印的一大特质,向上摊开的掌心更能感受到关于佛教文化千手观音的宗教寓意。没有手背向上的压迫式手印,而以一种豁达、和谐、施与、救济的手势姿态为手印的核心寓意,这也正是千手观音手印的大体动作风格与意向传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