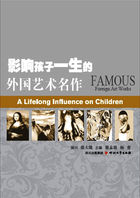一切使人受屈不幸的遭遇都是悲剧性的,这种不幸多发生在人们开新弃旧的过程中。悲剧的发生因人们在这种时候的盲目。开新时因人们对自身及客体不甚解而遭挫折,弃旧时因人们对自身及客体不甚解而受损害。
在这里,受屈不幸之发生审美价值,是因为悲剧人物所遭受的痛苦并非寻常痛苦,乃是阵痛性质的。悲剧属于壮美而美,它是壮美的前奏曲,因而是一种特殊的壮美。
壮美是人克服艰难的直观对象性,也即成其事者现在直观回顾此前自己克服艰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的正戏部分,主体与客体已是势均力敌。观赏壮美,正是观赏人们在克服艰难过程中主体与客体间势均力敌的冲突。在主体与客体的冲突之前是前壮美部分。在这个阶段,主体与客体的冲突为不均衡冲突,主体弱而客体强。对这个阶段的直观回顾即悲剧,这是成其事者直观回顾自己此前克服艰难时弱不敌强的不均衡冲突过程。不用说,在弱不敌强的不均衡冲突中主体是要遭受挫折而付出牺牲的。基于此,我们便说悲剧即成其事者直观回顾自己克服艰难之际的牺牲。
对开新弃旧间的悲剧故事我们可以界分为两种悲剧,一为开新型悲剧,一为弃旧型悲剧。
人们最多讨论的是开新型悲剧。马克思所说的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即为开新型悲剧。就这种悲剧的实际,我们可以据马克思的说法这样说:凡人们生打生面临第一次的奋斗遭遇都是作为悲剧出现的。
在今在古,人们生打生第一次应对某件事时都是受挫折不遂心的。这是必然的,因为其时人们对自身及客体方面的情况还很陌生。在这种情况下,事情便显得很艰难。无形中客体就显得很强大,主体则显弱小而处于极被动境地,要以弱对强。黑格尔说悲剧的原因在于悲剧人物的片面性,这是有道理的,主体对于自身及客体不甚解很陌生的情况正说明他的局限性、片面性。人在生疏盲目的情况下行动,出错失误是不用说的,受挫致败是自然的事情。
观赏悲剧,这是成其事者直观回顾自己此前克服艰难时的挫折、不幸。于是,主体当时的愿望要求便取得了合理的意义。在这里,主体当时的愿望要求虽然不伸,但现在的评价者是终伸这愿望要求的功成事就者。主体现在的功成事就无疑见得其初衷的合理,乃“历史的必然要求”,是可以张扬在阳光下的人生中美好的东西。在成功胜利面前,主体初衷之不伸受挫非但不辱,反见得很值,乃是取得目前成功胜利的必要代价。原来,悲剧人物正是成功胜利的评价者自己。在这种视野下,悲剧人物当然与“我们相似”,当然是好人,而且是“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他的受难当然是不幸的,是“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从而是可怜悯的。观赏悲剧的所有观众并不知自己正是这样的评价者,他们的心里自然向着悲剧人物,自然同情悲剧人物,为他流泪抱屈。岂不知,他们正是同情倾向自己,是为自己伤心流泪。
可以设想,把一个人刚才失败的过程搬演复现在他面前的情形,对他来说,这就不是让他观赏悲剧,而是向他展示耻剧。这种直观不是自我欣赏,而是自我出丑。没有成功胜利的设定,他的初衷便不能亮在阳光下,只能压在黑暗中,而不具合理性。现在,他的遭遇还是不堪回首的,还是见不得人的。他的失误、盲目不是可原谅的,而是愚蠢的表现,他无法同情自己,只有一再地自责。
开新同时就是破旧,这是同一事情的两个方面。学术界对弃旧型悲剧的关注开始于马克思的论断,他的意思是说当旧制度还没有完全丧失自己存在的合理性时,坚持这一合理性的人物的毁灭是悲剧性的。旧并不等于腐朽污垢,只要是合理的就不该被毁灭。但它却被毁灭了,为什么呢?
一位刚上大学的学生穿着母亲为他新做的布鞋,这被周围的同学指斥为土气落伍。为这件事他一时很苦恼,心里激烈斗争着。在老家,他母亲的心灵手巧是出了名的,她做的鞋常被姑娘媳妇们传着欣赏学习。穿着母亲做的鞋让他有说不出的精神,多年来他一直以此自豪。但是现在,他的这种自豪却受到了强烈挑战。看看周围,同学们一律穿着工业制鞋,没有一双手工自制的。他们的鞋样式丰富,也精致些,还有种种品牌。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他的自豪感开始动摇了。进进出出间,他老感觉所有的人都盯着自己的脚,那眼光都是不屑的,这让他极不自在,不知所措。他坚持着自己的自豪,极力抗拒着。这份信念里包含着对母亲的热爱敬仰,甚至维系着他以往建立的全部价值观念。他“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他本应该这样。但压力太大了,他太孤单了。理性地分析,明显见得这位年轻人对所谓落伍和时尚并不甚了解,他不甚了解自己原来自豪而现在失落的真正意味。终于,他顶不住了,也认为自己土气了。于是他脱下了布鞋,跟上了潮流,洋气时髦了。
但是放假回家后他又换鞋了。让他想不到的是,他的母亲更有名了,几乎成了名人。原来老家的文化部门正在挖掘民间工艺,大兴特色产业,母亲做的鞋被推为艺术鞋样,母亲也被聘为手工艺术制鞋培训班教授师傅。在鞋艺设计人员的指导下,母亲的鞋已被推为出口品牌,售价比他的同学那些品牌贵几倍不止。
鞋艺设计人员告诉他,手工自制布鞋最本色自然,体现着亲和自然的精神、健康朴素的情趣。布鞋轻便舒适、吸汗透气、冬暖夏凉,不像工业化学制品那样硬板,不透气不吸汗,冬冷夏热甚至还有对人体的副作用。
回家这一课让他省悟良多,他觉得所获要比自己上半年大学大多了。同时,他深为自己曾脱下布鞋惭愧。现在他觉悟到:破旧弃旧应是改革更新,而不应是草率否定过去,简单割裂历史。牺牲人类以往创造的优秀文化不是与时俱进,而是盲目冒进,野性发展。
返校后他继续穿布鞋,这布鞋更显精神了。不过,他也穿皮鞋,不管穿什么,他是要天然材料的。
可以想见,他返校后再见被自己扔在角落的布鞋时一定感慨系之,这就是欣赏悲剧。在这种时刻,他当初的痛苦获得了审美价值,他当时的坚持抗争显示着壮美色彩。
观赏这种悲剧,这是已经前进者直观反省自己此前破旧弃旧时的失误损失。这时候,主体才深刻觉悟曾被自己弃置的东西的美好,而不尽惋惜它的受屈牺牲。在这里,主体当时的信念虽然受制,但现在的评价者是终于平反昭雪这信念的觉悟者。主体现在的觉悟无疑可见其初衷的合理,乃“历史的必然要求”,是可以张扬在阳光下的人生中美好的东西。在觉悟面前,主体初衷之受制牺牲非但不辱,反见必要,乃是取得目前觉悟的必要代价。原来,悲剧人物正是觉悟的评价者自己,在这种视野下,悲剧人物当然“与我们相似”,当然是好人,而且是“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他的受难当然是不幸的,是“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从而是可怜悯的。观赏悲剧的所有观众并不知自己正是这样的评价者,他们自然站在悲剧人物一边,自然同情悲剧人物,为他们流泪抱屈。岂不知,他们正是同情倾向自己,是为自己伤心流泪。
还说那位大学生,如果在放假回家前将他当初双脚无所适从之状搬演复现在他面前,对他来说,这就不是让他观赏悲剧,而是向他展示耻剧。这种直观不是自我欣赏,而是自我出丑。没有后来觉悟的设定,他当初的痛苦抗争便不能亮在阳光下,只能压在黑暗中,而不具合理性。其时,他的遭遇还是不堪回首的,还是见不得人的。他的盲目失落不是可原谅的,而是愚蠢的表现,他无法同情自己,只有自卑自丧。
这一切,都必以扬弃外化为前提才有意义。不然,一切落水狗的历史都要搬上悲剧舞台了。鲁迅说“悲剧将人生中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但是有价值无价值、合理不合理由何界定呢?我国学术界如此界定:合乎历史发展方向的,体现积极进步意义的要求是合理的。这种说法还是笼统的,还是表面直观的,会将外在自然界自觉的历史和内在人类自觉的历史等同起来而混为一谈。因为张勋也可以说自己搞复辟是合乎历史要求的,希特勒也可以说自己残害犹太人是合乎历史要求的。在扬弃外化的视野下,唯表现人类自我觉悟的要求是合理的,唯就“人的感觉”而言的人们的恻隐之心、好奇之心和爱美之心是合理的,而所有成其事而不成此心,悟其道而不悟此义的要求则不合理,它的合理性乃是外在自然界自觉史下的。
我们说凡使人受屈不幸的遭遇都是悲剧性的,这必以表现人类自我觉悟的要求为前提。只有在这一界定下,马克思、恩格斯和鲁迅关于悲剧的论断才获得真正意义。
表面地看,悲剧即人们自我牺牲的直观对象性,观赏悲剧会“引起怜悯与恐惧”,从而我们说悲剧即人们自我同情的直观对象性。观赏悲剧在于给人以“净化作用”,其本质是激发人的同情心,促人同情生活中那些悲剧人物的不幸遭遇。
悲剧属于壮美,壮美即人们自我初步觉悟的直观对象性。作为壮美的前奏部分,悲剧有其独立的意义。壮美的正戏部分展示的是初步觉悟的状态,作为壮美的前奏部分,悲剧所展示的应为其准备阶段。悲剧作为人们自我牺牲的直观对象性,其自我牺牲意义正在于此。相对而言,我们便说:悲剧即人们自我尝试觉悟的直观对象性。
到目前为止,人类的觉悟还极有限。总体看来所谓人类历史还像是外在自然界自觉的历史,真正作为人类自己自我觉悟的表现还是不经意的偶然的,这种表现大多时候都是尝试性的。它卑微不彰,时时遭挫折受伤害,在阵阵痛苦中为自己开辟道路。
到目前为止,悲剧还是正常的。只要历史还是尝试性的,悲剧便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