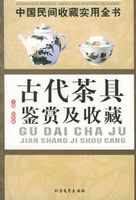在美学史上,人们通常都把壮美和优美放在一起讨论,但在具体作结论时却把它们割裂对立起来。在这种割裂对立下,人们只能做一些表面的直观的区别工作。扬弃表面的直观的视野,真实就在眼前。必须着眼它们的相对性,将它们统一起来。
在表面直观之下,人们所见的是先优美后壮美,常有人把优美界定为古代人类唯一的审美类型。其理由是:一方面,古代人类的审美意识还不复杂,审美经验还不丰富。他们说这种情况直到近代,这时候人们征服自然已达到一定程度,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断复杂丰富起来,其审美领域不断扩大,这才产生了与优美相对的壮美审美范畴。这种看法直接受古希腊人和谐说的影响。古希腊人崇尚和谐,甚至把美与和谐等同起来。壮美伴有痛感,是不和谐的,古希腊人似不愿把它放在审美范畴。但是,我们却不能把古希腊发达的悲剧和宏伟的巴特农神庙等归在优美之列。在表面直观之下,先优美论者看不到田园牧歌和谐表面下古代人类的艰难奋斗,看不到古代人类横空出世开天辟地的一幕幕壮举。
扬弃表面的直观的视野,我们分明看到的是先壮美而后优美。马克思就说,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普罗米修斯盗火的悲壮故事所展示的正是先民“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壮举。火作为审美对象,先是作壮美观的。直到今天,它仍然壮观。今人已能较好地控制从而熟练运用它,它已可作优美观了。
按这种顺序,本文先从壮美说起。但是,壮美已经被反理性主义者消解掉了。在反理性主义者看来,壮美是近代理性主义的东西,是理性主义二元对立的产物。在这种视野下,壮美被视为虚幻的东西,是建立在人的割裂对立之上的理性迷误。反理性主义者以消解理性价值而非壮美为己任,他们推出了“新感性”,许诺带领人类走出割裂对立之境。在表面直观下,反理性主义者看到的自然界是无对抗而一元同一的,动物与自然的关系即是。不言而喻,他们认为人只有摒弃理性而一任本能,才能不逆自然而与之同一。难得有人用心观察动物世界无为表面下外化的现实,动物世界并不是和谐宁静的理想国,动物与世界更是严重的割裂对立。“新感觉”并不能使人类走出割裂对立之境,反将使人们陷入更强烈的外化。在反理性思潮的背后,人类进入了“散文化”时代。尼采曾宣告上帝死了,他来不及宣告人死了。
在反理性美学家那里无所谓壮美,在后现代文化的“肉体”世界中已无所谓美。在外化范围内,人类历史正像自然界自发表现的历史,正是“散文化”的。扬弃外化,我们所见的则是人类豪迈向前的自觉史,乃是“壮美”之史。在扬弃外化的情况下,不是“散文化”消解壮美,而是壮美批判“散文化”。
研究壮美是从近代开始的。柏克将崇高与恐惧联系起来,康德认为崇高感在于人心能抗拒外界威力所引起的先惧后喜的愉快,狄德罗认为崇高感是一种“英雄激情”或“胜利感”。人面对恐惧之感到能抗拒恐惧之感,再到战胜恐惧得胜之感,这正是壮美的诞生史。鲍申葵一言道破,他说壮美即艰难的美。
表面直观之下,凡使人作壮美观的事物都必是形象巨大、形态粗粝、力量强大、冲突激烈之类。在这里,原因似乎只在客体方面,分明只决定于客体的固有属性,这正是说美在客观的原因。
鲍申葵的说法打破了这一层,他不管什么巨大、粗粝、强大、激烈,只说它们使人感到艰难。此说分明向我们传出了壮美发生的消息。但把他的说法直接放在审美范畴却是不妥的,美感是愉快的,艰难似不合美感。鲍申葵的说法是笼统直观的,还需进一步界定。此艰难该是贯穿壮美发生的全过程:首先,它是针对审美发生前的情况来说的,它是指人们面对不甚解而难应对的事情的感受;其次,它又是就审美发生时而言。现在,它指壮美感中的压迫感、撑胀感,此压迫感或撑胀感却并非寻常痛感,它是归属于美感范畴的。
到这时候,鲍申葵和柏克站在一条线上。柏克仅把崇高与恐惧联系起来,我们还是从鲍申葵出发进行探讨。
在今在古,人们面对不甚解而初应对的事情时的感受都是艰难。《黔之驴》故事中虎初见驴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只因它对驴“莫相知”,所以但见其庞然大物矣,而“以为神”。对蒙昧时代的人类来说,雷电、地震、冰雹、狂风等等事体都是凶虐、狂暴、怪异、不可捉摸的。在他们看来必是妖魔鬼怪作祟,使他们极感困惑、压抑、恐惧、迷惘。于是,他们转而神化这些事物,把它们抬举起来顶礼膜拜,认为那是一种超现实的力量,只有把它们推向非现实世界。孔子不言神、怪、力、乱,不论生死。
对先民而言不甚解而难应对的事物不唯山崩地裂、翻江倒海之类。可以说,凡超出其内在尺度的事物都会使他们为难。蛇蝎之类形小而力微,却很少有人等闲视之。它们至今都令人畏怯三分,还难以作为人的审美对象。
当一只猿手超越其内在尺度打制一把石刀时,这决不是在我们手里的举手之劳,而是极艰难的事情;决不是在我们眼里的等闲小事,乃是石破天惊的壮举。可以设想原始人猎狼或运动员登山的情景:他们要面临艰难、经历挑战,要冒危险、临恐惧。这就需他们全力挣扎,挺身苦斗,往往使他们头破血流,遍体鳞伤。最后,狼在脚下,山在脚下,那一时刻,其人定是豪情满怀、踌躇满志。猎狼人豪气冲天,运动员“一览众山小”。
这就是夸父追日,这就是大禹治水,这就是愚公移山……这就是人类开天辟地的创世纪。人从这里开始,审美从这里开始。在这种时候,人们唯观壮美,他们还不优美。
正是这样,在这种时候人们还不优美。当狼在脚下山在脚下时,因竭尽全力挣扎苦斗,那猎狼人或运动员已是衣破血流、气微力衰,正是一副狼狈模样。不用说,他们的豪情盛气之中是夹着余悸的。一时间里,眼前的胜利还不是很真实,使人反应不过来,那艰难仿佛还在继续。其人手脚虽停止了活动,心里却仍在抗拒着、挣扎着。在表面直观之下,这就是壮美感:一方面是豪情满怀、豪气冲天,另一方面是余悸在心、紧张阵痛。
人的生育是伟大的,人的生育又是动物里面最艰难痛苦的,因为人要反自然地生出不断增大的头颅。正像这样,人类的诞生创世是破天荒的事,须从自然界惯常行程的铜墙铁壁中打开一个缺口。这就要以非常之举,不惜以骨铺路,以血行船,用巨大的代价涌起一股铁流,杀开一条血路,横空出世石破天惊般冲突出来。这就意味着大出血、大阵痛。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竟磨褪了腿上的毛。愚公移山搬运一次土石要经千里迢迢,“寒暑易节”。夸父追日灼烤而死,普罗米修斯盗火被铐悬崖,忍受神鹰反复的撕心裂肺。“为有牺牲多壮志”,“战旗为什么这样美?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母亲生育后在感受欣慰自豪之际还要忍受余痛虚乏之苦,在表面直观之下,这就是壮美感:一面感受着热烈,一面被灼烤着;一面领略着险峰之无限风光,一面承受着“高处不胜寒”的无奈。
康德所说或同这些情况,这正是主体从抗拒艰难到战胜艰难先惧后喜的过程。
扬弃表面直观的视野,这里真正发生的故事是:将一个久在黑暗中的人拉在阳光下,他必觉阳光太刺眼炽热,一切都太刺激,这会让他头晕目眩、极不自在。但这是促醒了他的眼睛,促他进入新生活、新天地,使他生活在阳光下。愚昧狭隘的心理本能地拒绝觉醒放眼,壮美正在于有力地打破这种状态,将把强烈的文明之光大放进来。突然间强行地将愚昧狭隘的心理惊醒拓张,而铺天盖地充进对它而言异质的自由空气,它所承受的压迫感、撑胀感可以想象,它的不自在而抗拒可以想象。这时候,强烈的充实使它激动、振奋而鼓荡浩然之气是主要的,虽然还夹着不自在,虽然还有抗拒。很明显,对原来愚昧狭隘的世界来说,这是一场惊扰、破坏,使它痛苦。但更应看到,这是一场革命、建设,使它新生。正是这样,壮美是人观赏自己经历阵痛而绽放觉悟之花的状态,是人大开眼界大长精神而大步觉悟脱胎换骨的故事。
前面已经说过,壮美观感中的痛感仍属审美范畴,它不同于寻常痛苦感觉,不会使人灰心丧气,它倒是一种特别的愉悦,痛而快,苦而甘。人们观赏悲剧时所流的泪水该是苦涩而清香的,那是愉悦之泪、幸福之泪。
这一切,必以扬弃外化为前提才有意义,脱开这一点,鲍申葵等人的说法等于空谈。万里长城在今人看来是何等雄伟,但在孟姜女眼里却是最丑。当初万里长城只有少数人以为壮美,今天全人类皆可以同怀视之。
国内学术界引入矛盾的观点研究壮美,其结论是:壮美所展示的是主体和客体相冲突和对立的状态。此论并不能使我们超越柏克和康德,将被反理性主义者指斥为二元对立。这种观点还是表面直观的视野,还是在外化范围内说话。在这里,正像康德所说的主体对抗外界威力的情形,还不等生产的对象化完成。在这种观点下,似乎今人打虎也像武松打虎一样可作壮美观,即凡冲突和对立皆有可观。
现在,我们如此说:表面直观之下,壮美即人们克服艰难的直观对象性,或为人们开拓创世的直观对象性。在这里,人们所欣赏的是自己开天辟地的豪迈气概,所自豪的是对自己信心志气的有力确证。欣赏壮美,就是感受把艰难险阻踩在脚下,就是感受“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可以想象,这将使人大长志气、大增信心。扬弃表面直观,壮美即人们发端觉悟的直观对象性,或为人们草创自我的直观对象性。壮美书写的是人类初步觉悟先行觉悟的故事,是人类自我生成发展的草稿、提纲。
相比之下,人们研究优美的兴趣就淡多了,独立的专门的研究几乎没有。只是作为壮美的陪衬,为了说明壮美,人们才偶尔涉及优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得的信息是:关于优美对象的特征,它们表现为形象小巧、形态柔和、力量微弱、冲突平和等;关于优美美感的特征,它们表现为平缓、轻松、闲适、宁静等;关于优美的本质特征,优美是主体和客体矛盾双方暂时处于统一、平衡、和谐的状态。
很明显,这种情况正是相对于壮美表面直观而作的一番比较区别。在表面直观之下,这种比较只是在客体之间进行,外化了比较参照系,排除了比较主体。事物的大小强弱是参照人的感受而言的,因人的内在尺度而区分,以人的觉悟程度而见得。
排除了人这一比较主体,相对性便成为对立性,壮美和优美便显现割裂对立关系。排除了人的内在尺度,排除了人的觉悟程度,便无所谓壮美和优美。
能把我们引向前去的还是鲍申葵,他不管什么小巧、柔和、微弱、平和,将我们的眼光从客体固有属性上收回来,只说优美即平易的美。
鲍申葵的平易说真正将优美和壮美统一了起来。平易还是艰难,这是相对而言的,是相对于人的内在尺度从而是相对于人的觉悟程度比较感受而言的。
在今在古,人们面对不甚了解初应对的事情时的感受都是艰难。但在人们对这些事情有所了解再应对的时候,就会感觉平易轻松。对一个初学游泳的人来说,其第一感觉必是紧张、恐惧,使他极感艰难。在这个过程中,被灌几口水是常有的事,直呛得人鼻子酸痛,眼冒金星。最后,当他稍习水性学会游泳时,壮美于是发生。这里最重要的故事是:他已习水性而“增益其所不能”,这就是变一种外在尺度为内在尺度,即增长了人的觉悟程度。不用说,这个人再次下水游泳时,便少感紧张恐惧了,对他来说,游泳已不是艰难的事情了。这时候,他的感觉是平易轻松的。水还是原来的水,人已不是原来的人。对觉悟程度提高了的人来说,才发生平易轻松的故事。应该看到,所谓学会游泳,只是初习水性,特对游泳一事而言,其人只是初步觉悟,还不是高度觉悟。接下来,在其人多次平易轻松的游泳中,他将渐习水性、益习水性,而趋向如鱼得水、游刃有余的境界。在平易轻松的游泳中真正发生的故事是:游泳者将渐习水性、益习水性,即将渐益化水性这一外在尺度为主体内在尺度,从而是渐益增长着主体的觉悟程度。
一个乡下人第一次进县城,县城在他眼里是壮大的。但当他见阅过省城,回头再看县城时,县城便显犹小了。当他见阅过都城而回头再看省城时,省城也显犹小了。如果他回头再看县城时,县城就更显犹小了。在这里,县城或者省城还是原来的,只是他的眼界大了。在这个过程中,在他原来初见县城或省城而觉壮大时,这种感觉是初步的、粗略的。当他回头再看县城或省城而觉犹小时,其认识已趋细致、深化。对他来说,感觉壮大时是开眼界,感觉犹小时则是去熟悉。也就是说,无论感觉壮大或犹小,只是方式境界不同,但都是增长见识,增长觉悟。
庄子《养生主》里说庖丁解牛游刃有余,可以想见,庖丁初学解牛时一定没有这般自如。其游刃有余是经历十九年,所解数千牛才达到的。十九年前的他是如何解牛的呢?我们尽可以想象一种艰难狼狈的情景。这一时期,他解牛非割而折,每月更刀。在这一阶段,因对解牛之技知之甚微,更不必说深悟其道了,于是在他的感觉里,牛与他存在着强烈冲突对立。牛虽然杀倒了,解开了,他甚至感觉兴奋、自豪,但解牛之际所感觉的艰难紧张,人与牛之间强烈的冲突对立却还在他的心头隐隐保留。正是对这种情况的表面直观,学者们才说壮美即主体与客体相冲突对立的状态。其实,真正的冲突对立状态发生在观赏壮美者的内心。当此时也,那新觉悟的其他物的类的尺度是强充进来的,一时间里,这种新闯进来的异质的东西与他原在的内在尺度还很陌生,关系紧张。于是旧质抗拒新质,双方矛盾冲突。生硬的充实将使主体内心不谐,说明主体的觉悟还是粗糙的。初步觉悟正是这样,虽然还粗糙不谐,但就终使它超越愚昧狭隘前进了。
在以后的时间里,庖丁解牛时渐不感艰难,已感平易轻松,当初解牛时的紧张为难感渐渐消失。这时候,在他的感觉里,牛与自己已不存在冲突对立关系。同样是把牛杀倒了,解开了,他已不像当初那般兴奋、自豪,只觉得轻松、愉快。这时候,在他的感觉里,牛与自己之间已不存在冲突对立,而是熟悉如贴身衣服,左右手脚,熟悉如面对朋友。他的感觉是自然的、自在的,这时的牛是他可以自由对待的生产对象。在解牛的过程中,他已不紧张吃力,而是得心应手,只管顺手运刀就是,甚至自如到“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感觉是自如自在的,解牛这时候已成为他自由的生命表现。很明显,庖丁解牛后的心境与他面对牛及解牛时的感受是一致的。这里唯有他现在解牛的自由自在感受的继续,已没有他当初解牛时紧张不谐心情的遗留。在对这种情况的表面直观下,学者们于是说优美即主体与客体冲突对立暂时处于统一、平衡的状态。同样,真正的统一、平衡、和谐的状态表现在观赏优美者的内心。这时候,新觉悟的其他物的类的尺度是自然而然充进来的,因为主体内在尺度中原有跟他同质的东西原本就存在。也就是说,有认同迎接的因素,情况就像熟人见面,毫无陌生紧张感,于是新质旧质自然融合,并无对抗冲突。如此的充实将使主体内心丰富,说明主体的觉悟已趋精致,这叫细致觉悟,是觉悟丰富完善,而显有机和谐状态。
人初做一件事时总是粗糙的,正像写文章初打的草稿。表面上,这表现为主客体之间关系的牵强、生硬、矛盾冲突、不自然、不和谐。实质上,这体现出主体内心还不甚觉悟、躁动、浮躁、狂妄、迷惘。人干经熟的事时就细致了,这正像写文章时的润色修改。表面上,这表现为主客体之间关系的自然有致,有机统一,和谐天成。实质上,这体现出主体内心更其觉悟,显得宁静、热忱而淡泊。自然界在局部看起来可能是残酷的无情的,但在整体上自然界是有机和谐的,自然一词本意正在和谐。人类的终极理想就是在更高的意义上再造、复活这种状态,使人们生活在这种状态。觉悟和谐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只有觉悟和谐的人才能创造和谐的世界,才能和谐自由地生活。
同样是增长觉悟,将壮美和优美统一起来,其方式境界随可严格界定,但不能笼统界分其真实的表现。往往是壮美中有优美,优美中有壮美。惟其如此,才是觉悟的真实历史。纯就理论界定,人初应对一件事时克服艰难后将纯感壮美。接下来就不纯然了。当他继续干这种事时,该是还有艰难,只是不像第一次,而是稍感平易些。在成其事的感觉里,将是壮美中有优美。或者,他能够较平易地应对一件事,但其中还稍有艰难。在成其事的感受里,将会是优美中有壮美。平常情况下我们说壮美或优美,看主要方面即可。
美学史上有界定壮美和优美优劣之说,这是误导人生。唯壮美主义,将不能明心见性、觉悟和谐,将走向虚幻人生。唯优美主义将不能放眼解怀,即玩物丧志,这便是消极人生。爱壮美也享优美,方是觉悟人生。
这一切,必以扬弃外化为前提才有意义。强盗第一次杀人时也该是紧张恐惧的,我们似不能把他们杀人的狂笑当做壮美境界。惯偷行窃时已经平易轻松,我们也似不能把他们的窃喜当做优美状态。
现在,我们如此说:优美即人们细致觉悟的直观对象性,或为人们精致觉悟的直观对象性。欣赏优美将使人消解历险苦斗后隐隐的紧张余悸,将使人洗除前驱冲突时荡起的红尘浊气,使躁动化为热忱,使浮躁化为宁静,使狂妄化为淡泊,使迷惘化为澄明。没有平心静气,人不能明心见性;没有虚室淡泊,人不能返璞归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