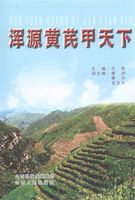素食者若使用皮制品,诸如皮鞋或皮带(即使是在他们成为素食者之前就有的),通常会碰到带有敌意的批评者,他们急躁地抓住这些东西来作为素食者表里不一与虚伪的证据。假如你是个为自己信仰发言的植物素食者(或许只有在受迫时才这样做),人们便期望你在道德上无瑕疵,因为只有道德上无瑕疵的人才能作别人的楷模。如果你在道德上没有百分之百的一致性,那么人们便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你的讯息可以被(而且应当被)大大地加以怀疑。
这种对素食者的不满不只不公平,并且也展现了一个不实际的世界观。没有人在道德上是完美的,完美也不应该是我们评判别人人格与行为的标准。我认为上述的批评来自良心上的不安,是那些对素食者有特定怨愤的人的特殊论调。萨特(Jean-PaulSartre,1905-1980)简明地指出,我们在道德与政治生活上全都存在“介入坏事”。萨特的陈述在现今似乎特别真确。现今,我们的消费品来自一些世界角落,那些角落充斥着血汗工厂与童工;只有很少或根本没有环保法规的存在;人权与动物权被明目张胆地糟蹋;多国公司剥削许多人,并使他们一贫如洗;还有,在我们的社会里,许多人从事危险而令人屈辱的行业,以此满足我们的需求。或许,如果素食者——特别是那些致力于使别人改变饮食习惯的素食者——的言语、穿着、行为,能给人一个统一而无懈可击的讯息:“我不从事或支持任何剥削或摧毁动物的活动”,那将会更好。不过,如果每个人都能说这句话,而且事实上能将这声明扩充到冲击其他人和整个环境的话,将会更好得多。虽然是如此,我们必须承认,和其他所有人一样,素食者会而且有时确实会在伦理生活上有区隔化的作为,而因为这样,他们便也有不一致的道德思考。
然而,我们必须补充四点。第一,任何认为帮助他者(不论这“他者”是人类或非人动物)是他或她道德责任之一部分的人,会把一定的时间和能量奉献给这样的行动。但,不论花多少时间与力量企图改善他者的命运,更进一步的奉献仍然是有可能的。当然,这种推论思路的合理结果是,有良心的人为了做到可能的一切,他或她就必须全心全力地为他者而自我牺牲。因此,道德一致性的代价是不享受娱乐、家庭时光及其他爱好,甚或没有照顾到像吃饭、睡觉的生理机能,每时每刻的利他主义与自我克制,甚至忽视自己。这个显然很荒谬的结果被满宁(RitaManning)适恰地称为“为爱自毁”(caringburnout)。要维持每时每刻的关爱态度所需要的努力很容易被忽视,特别当人们为了不管什么原因而对素食没有同情心时。正如斯柏龄(SusanSperling)的一个受访者所说的:
这里的重点不在于,素食者应该被免除为动物付出更多心力的所有责任,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自己决定,要把帮助动物的义务发挥到什么地步,这不只就自然产生的机会而言,并且就可使用的时间、力量及资源而言。虽然就界限在哪里的问题,我们总是有和别人及自己争论的余地,但在大体上具奉献精神的生活中,虚伪和不一致并不像某些人所声称的那么容易辨识。不管如何,素食主义是一个会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一个时时面对的生活方式的选择,它不会也不需要遵循一个固定的模式。
第二,如亚当斯(CarolJ.Adams)所指出的,“吃肉行为是对动物最具压迫、最广泛的制度性暴力。”如果这是正确的——确实就数量而言,食品业造成动物的死亡、痛苦、折磨,比其他和动物有关的任何企业所引起的都大得多——那么素我努力想做个纯素食者——亦即完全不使用任何动物制品。那是不可能的。我拥有一台钢琴,它有毛毡。这是橡胶,它的硬化处理过程使用到某种动物制品。一张打上亮光剂的漂亮桌子,使用了某种动物油。
我给我的宠物吃不含凝乳酶的脱脂奶酪。凝乳酶是一种来自牛犊的胃、用来加工处理乳酪的酵素。所以这是不含凝乳酶的,但它还是牛乳制成的。这件事很难,所以你和自己争论,你可以做个彻头彻尾的纯素食者,但它占去你许多时间,而你应该拿那些时间来做别的事,对吗?
食者透过饮食选择来减少对动物的伤害,这作为比他们可能以任何其他单一方式所做的,都更有好处。根据美国农业部,1994年美国人平均每人消费114.8磅红肉,15.1磅鱼肉,以及63.7磅禽肉,总共是193.6磅。虽然要把这些统计数字转换成被宰杀动物的数目很困难,但很清楚地,特别在禽肉方面,每个人平均所造成的动物死亡数目是很可观的。素食者也在若干方面减轻他们对地球的冲击。素食的方式越严谨,其好处就越大。
第三,虽然素食甚至全素食的饮食就能提供完整的营养,那些批评素食者不一致的肉食者本身,却还不愿意用既有效、又不需牺牲其基本需求的方式,来减轻动物的痛苦与折磨。改吃素食的唯一损失是饮食偏好以及某些快感,它们说得好也不过是非基本需求,说得坏则只是贪求,而且,一旦作了改变,大概能以变通的方式得到完全的满足。所以,看起来那些只作很少的努力、或根本没有努力帮助动物的人,在批评那些已经做了很多的人做得还不够时,就道德上而言,其立场是非常站不住脚的。这又算立下了什么样的榜样?
第四,如泰尔菲(ElizabethTelfer)所指出的,“由于大部分人都偶尔会疏于遵守他们的原则,所以,不一致的指控实在很难说足以否定任何一般的教条,或特定的素食主义。”叔本华写道:“……就像哲学家没什么必要也是圣徒,圣徒也不太有必要也是哲学家;就好像一个十足美丽的人没有必要是个伟大的雕塑家,或一个伟大的雕塑家本身毋须是个美丽的人。一般而言,要求一个道德家不得赞扬他本身未具备的美德,乃是个奇怪的要求。”然而,提出不一致性批评的人不必让步这么多。把自己构想成一个积极的道德改革者,或至少采取一个不随波逐流之道德立场的人,当然必须在别人眼中,或至少在自己眼中具有可信性。而这就需要企图做到言行一致——这个企图也不无可能无法完全达成。虽然叔本华可能是出于不自觉的原因而言过其实,我们却也很难反驳泰尔菲的立场。如果我们对信仰体系采取一个谨慎的态度,我们应该会说,许多(譬如说)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并未一贯地实践他们的信念;但即使这就多数人来说是正确的,它不应被拿来否定这些宗教的教义。同样的,素食的基本讯息要是很有说服力的话,也不应因我们在此讨论的这种不彻底的遵守而有所减损。
一些观察
毋庸置疑,还有许多会让我们注意的反对素食的论证。但此处所讨论的是目前所碰到的最重要的一些。我已试图证明,对我所支持的饮食与生活方式的改变,它们无一是无法克服的障碍。我们所检视的某些批判性观点,触及支持素食的某一个别论点,但我们必须记住,素食立场并非只有一个面向。追根究底,要紧的是所有支持素食之论点结合起来的力量。但,这话用在反对素食的论证上不也成立?它们岂不也有累积的力量和效力?如果它们没有遭到任何驳斥的话,当然,它们会有,我们若不是会有一个僵局,就是会目睹素食观点的瓦解。且不管我们在上文是如何面对并反驳了这些辩驳,也让我们承认我们了解到并在某种程度上同意导致这些辩驳的某些忧虑,但我们可以不用再讨论它们了。
产生这些辩驳的部分原因,是对未知的恐惧。未来总是属于未知的领域,不管我们多么常听见(并使用)像“可见的未来”这样的陈词滥调。我们无法否认,素食主义为世界设想了一个和它目前所朝向的非常不同的未来。在大部分食肉者及其他许多人的心中,这是一个颠覆性的想法,因此自然的反应就是取笑或想办法阻挡这样一个他们心目中的威胁。思考未来的可能性,不是我们人类这个物种的最大长处。我们不必然会以开放的心胸认同有创意的未来新方向。如布尔丁(EliseBoulding)曾写道的,“如果我们只根据现状去设想未来,那么,已知的事实便会像卷须般吸附在每个新观念上,以因为事情是如此所以某事不会成功的认知,去扼杀新观念。”要证实这项观察,只需比较一下,会急切地告诉你某件事做不到的人,以及会帮你寻找法子来做那件事的人各有多少即可。所以,在面对许多经常是强烈反对素食的论证之下为素食主义辩护的努力,我们不妨将之视为扫除障碍过程的一部分;这些障碍会阻挡我们展望一个有助于修护我们自己、我们的地球,以及我们和地球之关系的变通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