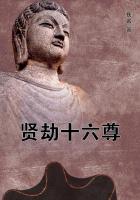弧月高悬,星子棋布。
一只老鸦栖居在枯枝上,寒风卷起残叶,乱石呜嚎。
树下,两个黑色的身影相依在一起,厚重的狼裘覆在两个人的身上,遮风阻沙。
沈晴头枕着他宽阔的胸膛,仰着脸,一双眼睛亮的像是落入凡尘的星子。北野寒被她盯得不自在地动了动肩膀,那人反倒直接无赖地将手探进他的衣襟里搂住他的腰,“今天好冷,还是这儿暖和。”
北野寒面上一烫,扼住沈晴的手腕将她的胳膊拽了出来。沈晴委屈地望着他黑曜石般闪亮的双眸,“怎么,我沈晴今天可算得是为你出生入死了,二王子怎么连舍身取个暖都不肯?”说罢也不顾那人的挣扎直接抱住往那宽阔的怀里一钻,猫儿一样舒服地喟叹出声。
北野寒皱紧了眉,冷道,“你怎么就没个正经的时候?”
沈晴在他怀里寻了个舒服的姿势躺下,道,“都是一只脚迈进阎罗殿的人了,哪个管他正不正经。”
北野寒低下头,压低嗓音沉声道,“你不会死。”
沈晴身子一震,感觉流回心里的血比冬日里的热茶还暖乎,禁不住鼻头酸了些,微咳了两声,却重又恢复之前那副无赖的样子,往那人怀里拱了拱说,“这话听着真舒坦,有二王子这句话,我沈晴黄泉路都乐得能蹦着走完。”
北野寒愣了愣神,眉头皱的更是紧了几分。一双暗眸闪烁不定,却终究还是再次开口道,“你不会死,你中的是软绝散,过些日子就自行消去了。”听闻此言,沈晴方才还扬着的嘴角瞬间松弛了下来,“什么意思?”
北野寒低头望着她的眼睛沉声道,“大齐的人在北庭也安插了眼线,那人身份暴露被包围后便用的此种毒药脱身。你的症状跟那些中毒的士卒很相像。莫不是,莫不是大齐那边也有人想要对你不利?”
沈晴心下一沉,眉头不由地蹙紧。
北野寒低头望着沈晴皱紧的眉,眼眸深了几分,禁不住伸手将狼裘往沈晴的那边多挪了些去,揽过她的肩,沉声,“算了,别想太多,早些睡吧。明天,也许会起风。”
沈晴中断思绪,回过神来又将狼裘推了些过去,“你也早点休息,你中的毒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解。”
北野寒听话地躺下,背过了身子,免得触了背后的箭伤。
沈晴说的没错,他确实中了毒,北庭的毒,一切还尚在他的计划之中。可他的心里莫名有些烦躁,尤其是念道沈晴听闻软绝散时的神情,竟让他的心下一窒。不想,背后沈晴却翻了个身子,直接将一条腿横在他身上,揽着他的腰冲着他的脖颈吹了口气,佻声道,“趁着你还没死,赶紧让我再多抱两天。”
另一边,凛冽的寒风吹过狼营,焦黑的木杆卷着烟,未熄的野火在远离营涨的地方喘息蔓延。
帐内,拓跋燕坐在虎案旁,面色阴鸷,半晌,一个军士掀开帐门进来跪地行礼。
拓跋燕恭腰问道“左统领伤势如何?”
军士低头抱拳,“回将军,尚在昏迷,若能熬过今夜便无大碍。”
拓跋燕沉声点头,再抬头已是一脸狠厉,“好个沈晴,竟然重伤我军将士。带我去看。”
军士将拓跋燕引至左统领账前,拓跋燕掀开左统领的床被,却见被里都被他的血给浸成深红。拓跋燕面上怒意更深,“去喊军医!快!”
军士有些犹豫,“将军,左统领的伤口已经止住,那是之前...”
“去他的之前!”拓跋燕张口喝骂,脸上的刀疤在火光下更显狰狞,“血流成这样叫也止住?去唤军医!”
军士被吓得够呛,惊惶出了营帐去传唤军医。帐内,拓跋燕却换了脸色,低下头来看着左统领失血过多苍白的脸,沉声道,“统领别怪我无情。你我都是大王子的,今日我拓跋燕送你一程,你也好最后为大王子出一把力,左统领,意下如何?”
说罢便抽出腰间的佩剑,刺进了沈晴之前留下的伤口。
与此同时,就在这座营帐外面,军师于江正站在帐外,一字不漏地将这些话收进耳朵,然后轻轻地甩甩衣袖,面色不改地转身回了自己的帐子。
不消多久,一个传令军士掀开帐门,“于军师,将军请您前去议事。”
于江皱紧了眉,问,“将军可有交待是何事相商?”
“回军师,是左统领适才伤势恶化,咽了气,拓跋将军发了怒,现正在帐中召集众将士前去商议诛杀叛贼沈晴的事。”
于江佯装惊讶,“哦?还有这等事?快,引我前去!”
方至帐中,见一众将士密密麻麻地挤在帐中,一把马刀横立虎案,拓跋燕正一脸怒容,见自己来了,方起身恭请,“劳烦军师深夜前来,燕某有愧。”
于江摆手道,“将军客气,不知此番邀我是有何事相商?”
“说来惭愧,燕某无能,竟让那叛贼沈晴将二王子挟下了悬崖,还损失了一员猛将。只是不知,依军师所见...”拓跋燕微眯着眼,低声道,“从山上冲下来的黑衣贼究竟是何人安排?”也不怪拓跋燕多心,大王子识人一向不会有误,只是这个于江......他看不透,这人面目亲和,举止文雅,却也因此与人隔了层雾,令人捉摸不透他的真实想法。
山上黑衣贼的突袭除了左统领,他未与任何人提起,即便是与他一样久经沙场的木德将军都慌了心神,可一介区区书生竟悠然泰若着实惹人生疑。他信大王子,却也相信自己行军多年阅人无数的直觉,权衡之下,他拿定主意,若此人不知黑衣人的来历,留着用也不大,若知道,那更是留他不得。
于江皱着眉思量了一番,说,“这,怕是难为在下了。”
“哦?”拓跋燕向前一步,沉声道“于师知也不知?”
于江坦然一笑,恭敬地弯腰垂首,“将军真知我者。于江知,也不知。”
东方未晞,红色的云霞染透群山,一行黑色的雁阵从天边徐徐飞过。
沈晴睡梦中往旁边摸了一把,那人却不在身边,于是揉着眼睛起了身子张望,却见那人正在背对着自己站在一旁的树下,于是出声,“二王子果然勤勉,起的倒真早。”
不想那人却吓了一跳,浑身一哆嗦,险些摔在地上,顾不得转过身来骂自己便又多走远了些系上衣带。
沈晴倒没心没肺地笑开了,“二王子不必拘谨,我沈晴在军中什么没见过。”
那人面红耳赤地摆着一张冰脸过来话也不说地扯起地上的狼裘转身离开。沈晴赶紧爬起来追上,“原来北庭的人那么容易脸红,早知道当初跟你们打仗就不必动武了,只消讲些荤段子你们不就羞回家里去了。”
北野寒冷哼一声,反口讥讽,“我倒是觉得大齐的女人礼教还真是淑雅得体。”
沈晴也不反驳,追上去拽他的胳膊,“哎,我怎么瞧着你不像是中了毒的样子。昨晚为何要我被你逃生?”说罢又勾着唇角,俏眉横挑,拿肩去搡他,“莫不是...二王子喜欢让女人背着?”
北野寒挣脱她的膏药手,皱紧了一双剑眉,目不斜视地向前走去。
沈晴也不再跟上,只是在原地站着,等北野寒走远了些,她才负着手悠悠地出口,“哎,二王子,知道该往那边走吗?”
北野寒闻言身子一僵,然后扭头看了看两旁的杂草丛生的山路,步子动了动,却终究没有迈出去。
“不知道就回来喽。不认识路还走在前面,北庭的男人倒还真是勇武。”
北野寒的脸色绿了几分,昂着头在原地站了会儿,终究还是一言不发地原路回到沈晴身边,沈晴也不顾他的冰霜脸,一把勾过他的胳膊仰着脸冲他笑,“这就对了,跟着我沈晴混,包你全须全尾儿的回到北庭,到时候你做你的北庭王,我做我的沈王妃,然后再给你生一堆娃娃,让......”
北野寒身子又一僵,用力抽回胳膊,将沈晴推远了些,厉声道,“你想得太多了。”
沈晴又不管不顾地缠上来,仰着脸瞪他道,“如何就多了。”
然后又恍然,于是应和地低头,笑脸盈盈,道“是想多了。那只生一个娃娃好了,免得像多了将来还得争王位。”
北野寒听的脸都绿了,一张冷脸绷得更紧,恨不能凝出一层冰霜。那边沈晴非但没有停下,反倒寻思起给那八字没一撇的娃娃取些什么名字才好。正数着,北野寒忽然停下脚步,握住手腕的虎口一紧,拉她蹲下,“嘘,有人!”
话音未落,便看到远处的山脊尘土激扬,马蹄踏断枯草,残叶与尘砂卷至空中,风声轰鸣,一众将士纵马驰来,马上骠勇的骑兵扬鞭策马,身后黑压压的军队在高山上扬起狼旗。
北野寒望着在山脊设卡的北庭军队,眼神冷的像是寒池里的冰。“看来他们是不想让我们踏出这片山谷了。”回过头却撞见沈晴正睁着一双美目望着自己,眸子里波光旖旎,似是被风揉碎的一汪秋水。
北野寒微怔,忙错眼躲开,低声喝道,“原来你真的没有正经的时候!”
“倒是二王子正经的样子,真是可爱的紧。”说罢趁他不备在他的唇角偷印了一吻,在他生气前指了指驻扎在山脊上的军队,然后掩着嘴看着他想要发作却不得不隐忍的表情,沈晴忽然有点希望,能像这样一直被困在这片山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