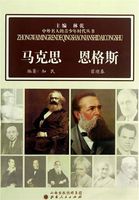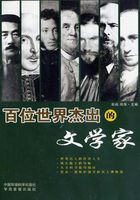李商隐离开了道观,但是他并没有回到自己家中。
他想,家中事有弟弟羲叟操持,可以放心,在外奋斗寻找出路以光耀家门才是自己肩负的责任。十六岁就“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的他,这时如初生於菟般充满自信,一腔热血,跃跃欲试,准备到人生的广阔天地搏击一番。
于是,他来到了东都洛阳。
李商隐原籍怀州河内,祖上已移居郑州荥阳,他一生中也曾几度搬迁,幼时跟父亲到浙江不算,前此曾在济源,现在是洛阳,后来还曾移家永乐(今山西芮城)和首都长安。至于他依人作幕,则跟随府主到过桂林、徐州、梓州(今四川三台),更因公事出差江陵、成都、潭州(今湖南长沙)、巴东湖湘一带,乃至江南的一些地方。漂泊无定可以说是他平生一大特色。
但洛阳是他初次入住的大城市,也是他生命史上最有纪念意义的地方——他在这里结识了影响他一生命运的令狐楚老人,也是在这里与爱慕他的柳枝姑娘产生过一段凄艳的恋情,而他岳父大人王茂元的宅邸也在洛阳,李商隐结婚以来直到岳父和妻子过世以后,住在洛阳崇让坊王宅的机会是不少的。
唐朝的洛阳,是一个仅次于首都长安的大都市。它地处中原,在西京长安之东八百五十里,位置十分重要,“北据邙山,南对伊阙,洛水贯都,有河汉之象”[1]。自东周在此建王城,东汉魏晋以下,历代皆在此建都,隋炀帝也曾在此大兴土木,修建宫殿,以之为东京(后改称东都)。唐初,在洛阳设洛州总管府,后改为陕东道大行台,又改为洛州都督府。至高宗显庆二年(657)乃于洛阳“置东都,官员准雍州”,正式确定了它的陪都地位,其行政级别与雍州(即京兆府)相当,最高长官府尹均为从三品。武则天统治期间,光宅元年(684)改东都为神都,这里实际上是她最喜欢居留的地方。从前唐高宗在时,他俩就经常离开长安,行幸东都。唐高宗死后,武则天就干脆不再返回长安,而是长住洛阳了。她最后的二十年时光,就在洛阳度过,至八十三岁高龄才驾崩于洛阳上阳宫的仙居殿。[2]安史之乱中洛阳一度被乱军占领,受到严重破坏,乱后已难恢复昔日的繁华光景。虽然如此,它仅次于长安的地位仍然未变,仍是唐朝的第二大政治、文化中心。
当初由于最高统治者经常住在东都洛阳,为了行政方便,也为显示东都政治地位的重要,唐朝在洛阳设置了一套与中央相似的行政机构,号为“分司”。这一制度在安史之乱后仍一直延续下来。分司的官员除监察御史外,其实都没有什么事可干,品级越高的,就越没事儿,他们只是因为各种原因被安置到东都来的一批闲职人员。既无需做事,又享有优厚俸禄,所以许多老官僚都愿来洛阳担任分司之职。他们往往在洛阳买下大片土地,建起豪华讲究的别墅或园林,在这里过着优游卒岁的休闲日子。像裴度和李德裕,都是做过宰相的,裴度“东都立第于集贤里,筑山穿池,竹木丛萃,有风亭水榭,梯桥架阁,岛屿回环,极都城之胜概。又于午桥创别墅,花木万株,中起凉台暑馆,名曰绿野堂,引甘水贯其中,酾引脉分,映带左右。(裴)度视事之隙,与诗人白居易、刘禹锡酣宴终日,高歌放言,以诗酒琴书自乐,当时名士,皆从之游”。[3]李德裕在长安的安邑里有府邸,同时在洛阳南郊置平泉别墅,周围十余里,开山引泉,模拟巫峡、洞庭、十二峰、九派以至于海门的景色加以疏凿布置,内有台榭百余所,遍栽奇花异草。可惜因为出将入相,忙于朝政,真正在那里享受的时间不多,后来政治上失败,被贬逐去了海南岛,平泉庄也就落入他人之手。关于洛阳的别墅园林,宋人李格非有《洛阳名园记》详载,读者若有兴趣可以参看。
正因为洛阳居住着一批高官和在政坛、文坛有影响的人物,在成名和科举路上奋斗的士子们只要有可能,就都会到那里去寻求机遇。一旦在这里找到有力的支持,或获得称赏和美誉,那么科举和仕宦就比较容易步上坦途。
李商隐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情来到洛阳。初到洛阳,他立刻被这座城市的古老悠久和壮丽雄伟震慑住了,心里不断地在赞叹:啊,洛阳洛阳,真不愧为历代帝王雄踞的伟大都城!
也许这时他还没有什么具体的努力目标——诚然,他是到这里来寻求机遇的,但他绝没想到好运会来得如此迅速而诱人,更没想到洛阳这座城市将对他的一生发生如此深刻、如此难以磨灭的影响——每天,他只是拿着自己的几篇得意文章,寻找一切机会求见和拜谒洛阳的贵人名士,既希望得到指点,也希望结交朋友,更希望得到赏识揄扬。投文献诗,以文会友,以文求知,本是唐代士子自我推介的一种风气,许多今日的名人高官,想当初也曾如此行事,所以他们往往也乐意借此与青年文士接触,既可从中识拔人才,也好博得奖掖后进的美名。
就是在这里,李商隐结识了他生命史上最重要、也是第一位身居高位的前辈——令狐楚。
时间是唐文宗大和三年(829),李商隐十九岁,正所谓年方弱冠、风华正茂之时。据《旧唐书·令狐楚传》:这年三月令狐楚以检校兵部尚书的身份出任东都留守、东畿汝都防御使,来到洛阳。
令狐楚这时已年过花甲。[4]十年前,他曾入阁为相,后因官场斗争,出京做过节度使、观察使一级的高官,在治理地方上政绩颇佳,是个饱经宦海风波、富有政治经验、很有知人之智的老人。所以,当李商隐前往晋谒(姑且假定是经人介绍,否则身为无名白衣的李商隐何缘得见?)拿出所写文章请他批评指教时,他稍一浏览,就感到眼前这位年轻文士潜质极佳,是个很有培养前途的好苗子。再经问讯,令狐楚知道了李商隐的家世和现状,见他谈吐不俗,不免对他产生几分同情几分爱怜,谈着谈着,竟于不知不觉中放下了一向威严持重的架子,谈话变得亲切起来。
令狐楚对李商隐说:“从你所写诗文看来,你的腹笥和识见都有相当根柢。可是,你现在写的这些古文和古体诗,都不是当今仕途和官场用得上的东西。”
李商隐先是一愣,然后请教:那该怎么办呢?
“要能写一点‘四六’才好啊。”令狐楚说。
当时官场通用的文体是骈文,即俗话所说的“四六”。李商隐老老实实向令狐楚说了跟处士叔读书和习文的情况,最后不好意思地说:“以前从未学过骈文,读得也很少。”
令狐楚点点头说:“是啊,这便是你的短处。”沉吟一下又说:“不过,凭你的资质和基础,学起来应该不会太难——当然要狠下几年功夫,多读书、多留心、多练习才行。”
李商隐感激令狐楚的指点,表示十分愿意朝这个方向学习。
令狐楚很喜欢他的进取精神,沉吟一下,说:“你不妨常来,和我的子侄们一起研讨切磋。”
就这样,令狐楚家的大门,含着微笑向李商隐打开了。
令狐楚有两个儿子,长子令狐绪,次子令狐绹,他们的年龄稍有参差,可能都比李商隐略大,另外还有一位令狐缄,是老人的侄儿,也在伯伯家住。三个令狐公子目前均未参与科考,也未出仕,此时都在家馆中读书习文。按照唐朝制度,以令狐楚的官爵,可以荫庇一个儿子免试为官,但令狐楚还是很重视他们的教育,希望他们科举有成,故公务之余常去查看他们的功课,随时进行评点指导。
有了令狐楚的准许,李商隐真的常常来到他家,一来二去熟悉起来,不但读书,而且留宿,慢慢地几乎成了家人一般。他和几位公子一起练习骈文写作,接触到当今官场乃至朝廷所需用到的各种文体和文本样式,很快便掌握了写作的诀窍。他的身份有点像公子们的伴读,但又不全然如此。由于父亲器重他,并经常夸奖他作文悟性高、有才气,几位令狐公子对他自然也不敢小觑。商隐开始难免拘谨,慢慢熟悉起来,也就俨然以朋友之道与他们相处,并不觉得自惭形秽或低人一等。大概因为年龄接近,李商隐和老二令狐绹关系更好、更谈得来一些。
东都留守的公务本来并不繁忙,文宗大和初年时世又还算太平,令狐楚常有时间批阅儿子们的习作,给他们传授写作今体章奏——这是一个想混迹官场并想步步升迁者的必备本领——的窍门。高兴的时候,他还会给子侄们讲讲自己年轻时候以文章被群公和德宗皇帝赏识的光荣历史。
原来,令狐楚也是自幼学文、颇负才名的人物。二十三岁进士及第后,便长期在太原府做幕僚。唐朝的太原府号称北都,地位与西京长安、东都洛阳相当。太原尹、北都留守往往兼任河东节度使,其官阶为从三品,与京兆尹、东都留守平级。令狐楚早年长期在太原府做幕僚,前后三任节度使都十分器重他,“自掌书记至节度判官,历殿中侍御史。(令狐)楚才思俊丽,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能辨楚之所为,颇称之”。就是说,连皇帝都能从众多来自太原的奏章中分辨出哪一封是令狐楚所作,而给予表扬。这自然是令狐楚引为自豪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