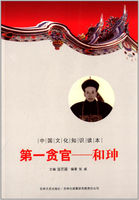还有一件事,似乎更了不起:节度使郑儋因病暴死,没来得及安排府中事务,太原驻军发生骚动,形势紧迫,将有急变。半夜,熟睡中的令狐楚被十来骑人马持刀挟持到军中,几乎所有的将领都在,大家要他连夜为已故的节度使代草《遗表》。方面大臣临终前上给皇帝的《遗表》是一封重要的奏章,其中要对当地军政和人事的安排提出建议,比如以谁为“留后”,即代理主将啦,或推荐谁继任啦,这些都事关在座诸位的地位前途和切身利益。显然,这篇文章非常不好写,在座个个都是凶巴巴的武人,得罪了谁都不行啊!令狐楚倒是胸有成竹,在一片白刃包围下,气定神闲地挥毫而书,几乎文不加点,一气呵成。写完后,召集三军,高声朗读一遍,因为辞意恳切而正大,竟感动得三军泣下,使军情顿时转危为安。[5]
一个文人,一篇文章,竟弭止了一场迫在眉睫的兵变,为地方和国家立了一大功,谁能说文章无用!从此,令狐楚声名更重,逐步受到朝廷提拔,从翰林学士一直做到宰相。每当想到这段往事,令狐楚总是兴奋不已。
“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子桓之言,非虚语也!”
令狐楚不止一次捋着胡须对子侄和商隐讲述自己的往事和感想。他的实际遭遇,似乎也在为这句话作证,在李商隐心上自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结识令狐楚,对于李商隐来说是件大事。一来他们身份那么悬殊,出身孤寒的李商隐算是攀上高枝儿了,这是一般人连想都不敢想的好事;二来令狐楚是骈文高手,在他的调教下,商隐的四六文技巧由启蒙而突飞猛进,后来甚至隐隐露出胜蓝之势;第三,是他与几位令狐公子有了同学之谊,特别是和二公子令狐绹简直成了无话不谈的知交,这对他未来的仕途当然是有帮助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令狐楚的教导和提携,令狐绹的友谊和美言,确然而不幸的是,在残酷的官场博弈和复杂的朋党之争中,情况不断变化,这些有利条件后来竟一反而成李商隐心灵和行动自由的枷锁,给他带来无穷的苦恼——当然,那些后来逐步发生的事,当下不能预知,所以此时商隐的心情很好,甚至不免有点踌躇满志。我们就让他先高兴一阵,暂不说后来的事吧。
在洛阳,除令狐楚,李商隐还认识了另一位著名人物,他就是诗人白居易。
白居易热爱洛阳,早在他杭州刺史任满后改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时,就决意从此在洛阳定居。那时他五十四岁。后来虽又出任苏州刺史,再入朝为秘书监和刑部侍郎,但到唐文宗大和三年(829),他五十八岁的时候,就坚决地“称病东归”,回洛阳定居了。史载:“初,居易罢杭州,归洛阳,于履道里得故散骑常侍杨凭宅,竹木池馆,有林泉之致。家妓樊素、蛮子者,能歌善舞。居易既以尹正罢归,每独酌赋咏于舟中。”其《池上篇》自述道:“大和三年夏,乐天(白居易号乐天)始得请为太子宾客,分秩于洛下,息躬于池上。”该文描述其池馆和家居生活:“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有堂有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中,白须飒然,识分知足,外无求焉。”[6]
老诗人饱经世事,诗文名满天下,此时年迈,已渐入“栖心释梵,浪迹老庄”之境,但还是非常乐于提携青年后进。李商隐就在这时初识白居易,受到亲切接待,二人几乎成了忘年之交。二十年后的大中三年(849),当时白居易已去世三载,按其遗愿安葬于洛阳龙门,嗣子白景受欲为其墓立碑,恳请李商隐为父亲撰写碑铭。[7]李商隐曾有信回复,信中提及当年白居易对自己的顾遇,可谓充满感激之情:
伏思大和之初,便获通刺;升堂辱顾,前席交谈。陈、蔡及门,功称文学;江、黄预会,寻列《春秋》。虽迹有合离,时多迁易,而永怀高唱,尝托馀晖。[8]
这里说的是大和初年,大约也就在李商隐结识令狐楚前后,李商隐在洛阳拜见了白居易。老诗人在客堂亲切会见这位初到东都的年轻士子,和他谈诗论文,指点剖析,话颇投机,使李商隐大有升堂入室成为白氏及门弟子之感。李商隐还曾有幸厕身白居易家的诗酒文会,在那里得见洛阳的不少达官贵人,对李商隐来说,那感觉就像春秋时代的江、黄小国得以参与大国隆重的会盟典礼一般。
这期间李商隐曾不止一次地去过白府。估计也就在此时,曾看到过白居易编撰的类书《六帖》。只是不久后李商隐即随令狐楚前往郓州,再往后由于李商隐为生活到处奔波,不能常住洛阳,他们见面的机会并不多。然而白居易对他的善待和照拂却让李商隐永难忘怀。所以当白景受约请他为老人撰写碑铭,并告诉他时任宰相的白敏中(居易堂弟)也有此意时,他便同意并很快写成交卷了。
李商隐的《刑部尚书致仕赠尚书右仆射太原白公(居易)墓碑铭》(并序)是一篇以古文写成的史传性文字,叙事简洁,文风谨严,但缕述白居易生平宦绩、个性文采以及家世戚属(从而顺理成章地附述了亲弟白行简和堂弟、现任宰相白敏中)等等,内容非常充实。文末的铭词更是凝练精当,古趣盎然,与商隐其他骈体文章的华丽风格明显不同。商隐文章今日能见到的以骈文为多,所以这篇保存在《樊南文集》中的碑铭自然弥足珍贵。
白居易早在元和(806—820)时代就诗名传扬,以他和元稹为代表的“元和体”一度风靡天下,远播海外。进入晚年,更可谓诗坛的当然盟主。而李商隐此时至多只是个年轻诗人,他的《燕台》《河阳》《河内》等诗虽然才气非凡,但毕竟还有模拟和习作的痕迹,诗风的真正成熟还有待时间的磨砺锤炼。而且他们二人诗风的美学趣尚很不相同,当李商隐形成自己独特风格之后就更为明显,说得严重些,甚至可谓大异其趣。白居易诗是平易浅淡、畅达无隐,读起来有如行云流水,直叩心扉;李商隐诗却华丽秾艳、用意深曲,像以轻纱笼面的美人,令人难窥真相。我们不知道白居易读到过李商隐的哪些诗篇,也许他们初见时李商隐曾出示过《燕台》诸诗,那已足以引起老诗人的惊异与激赏。李商隐后来的创作,白居易可能读得更多。他是在会昌六年(846)去世的。那时,李商隐的《有感二首》《重有感》《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曲江》《韩碑》等一系列重要作品,特别是那些深沉婉曲地讴歌爱情的诗篇,如《柳枝诗》和某些《无题》诗,都已写出,白居易应该有机会读到。
晚年的白居易极为欣赏李商隐诗,往往自叹不如。这位修养深邃、经验丰富的老诗人有着容纳不同风格诗派的宽广胸怀,不然怎么有资格获得“广大教化主”的美誉?
当时的诗界有这样一个传闻:有一次,李商隐去看望白居易,白居易竟对商隐说:“今生今世我是赶不上你了,但愿我死之后,能够转生投胎做你的儿子,也就心满意足了!”[9]此事真假难辨,或因白居易笃信佛教,佛教宣扬三生轮回观念,而他太喜爱李商隐诗了,所以好事者如此来编派他。不过,这个传闻能够流传开来,却使我们由此想见白居易对商隐诗歌艺术的心醉程度。
当然,李商隐在与这位老前辈的交往中,也学到了许多东西。别的不谈,就以白居易搜采成语典实而编撰的《六帖》(亦称《白氏六帖》)而言,就会给商隐很大的教益和启发。
《六帖》是一部类书,分门别类地编录采自各种书籍的成语典故,供作文赋诗时查找利用,其中有不少李商隐未曾读过的古书,使之大开眼界。同时,这种汇编语言资料的方法给写作(特别是需要大量用典的骈文)提供很大方便,也使李商隐顿开茅塞。
李商隐后来吟诗作文以辞藻丰赡典雅著称,并曾在收集民间口语乃至方言方面下过一番功夫。在他的遗著中有《杂纂》,专收当时流行口语,现在读来仍十分有趣,有的内容简直可与今天人们在网上或微博中流传的精彩语言比美。又有《蜀尔雅》和《金钥》,虽然已佚,但从书名和著录它们的《宋史·艺文志》的分类来看,显然也是属于语言词汇方面的著作或工具书。《蜀尔雅》,顾名思义很可能是仿《尔雅》(古典词书)体例解释蜀方言的。《金钥》则很可能寓写作诀窍(金钥匙)之意。在这些方面,白居易对他也许不是毫无影响。至于在诗歌创作和批评鉴赏方面,身兼诗人和理论家的白居易也必然会给李商隐以种种有益教诲,所以才使李商隐心悦诚服,发自内心地承认自己几乎无异于白居易的“及门弟子”。
令狐楚此次担任东都留守的时间不长。他是三月上任,同年十一月就进位检校右仆射,调迁为天平军节度使、郓曹濮观察使,要离开洛阳了。
天平军治所在郓州(今山东东平),距洛阳九百七十多里。令狐楚问李商隐是否愿意随他到郓州去,并说:“如果你愿去,那么,我给你一个节度巡官的位置,是可以的。”
巡官是节度使幕府的一个小官,虽然职级不高,但这时李商隐还是一个没有取得功名的白丁,令狐楚的这个建议无疑是对他的破格优待,是李商隐根本没想到的。
试想,他本来至多只是令狐楚子侄们的读书伙伴,跟着令狐楚到郓州去,就是幕府的正式官员了。在郓州,他不但可以继续学习文章,而且获得锻炼办事能力的机会,更有了一份官俸,对家庭颇有帮助。李商隐明白,令狐楚显然是想进一步栽培自己,这是老人家的好意,也是自己走上仕宦之路的重要一步。所以,他不假思索,满含感激地接受了。
[1]见《旧唐书·地理志》河南道。
[2]以上所述据《旧唐书》之《地理志》与《则天皇后本纪》。
[3]见《旧唐书·裴度传》。
[4]若依刘禹锡《令狐楚集叙》“开成二年十一月十二日薨于汉中官舍,享年七十”推算,本年应为六十二岁。据《旧唐书·令狐楚传》则应为六十四岁。
[5]以上所述据《旧唐书·令狐楚传》。实给李商隐带来许多好处。
[6]史文及《池上篇》均引自《旧唐书·白居易传》。
[7]据李商隐《太原白公墓碑铭》,知白景受请李商隐为白居易撰写碑铭是在大中三年(849),距商隐初见白居易的大和三年(829)恰为二十年。
[8]李商隐《与白秀才状》,作于大中三年(849),见《李商隐文编年校注》,1801页。
[9]见《蔡宽夫诗话》,郭绍虞《宋诗话辑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