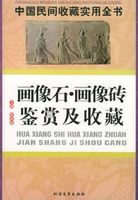2.惠施“善譬”
惠施在名辩思想方面另一突出贡献是第一次从理论的高度概括了譬喻推理。惠施无论是在高居相位,为国君出谋划策,还是与天下辩者“相与乐之”、“终身无穷”的滔滔雄辩中,都堪称是一面旗帜,不但善辩,而且在辩论中以“善譬”而闻名。据《战国策》记载,魏惠王曾宠信一位名叫田需的大臣。能受到国君的信用,当然是春风得意。
旁观者清,惠施及时予以忠告:你必须与大王周围的人搞好关系。你瞧那些杨树,横插能活,倒着栽也能活,折断再种还能活。然而,有十个人种杨树,假使只一个人去拔,那就不会有杨树能幸存。以十人之众去种这么容易成活的杨树,也敌不过一人去拔,为什么呢?原因是种树难而拔之易。您虽然取得大王信任,但想消除大王对您信任的人太多,如此,您必定处在危险之中。惠施用了一个譬喻推理,以容易存活的杨树栽难拔易,来比喻伴君为臣的安危,向正得魏惠王宠信的田需提出居安思危的忠告。
《战国策》上另一处记载:魏惠王死后,定下了安葬日期。安葬那天恰值雨雪交加,群臣请求太子改日安葬。太子不听。群臣束手,恭请曾佩五国相印的公孙衍设法,号“犀首”的公孙先生也无良策,说:“吾未有以言之也,是其唯惠公乎!请告惠公。”这件事唯有惠施先生能解决吧。
惠施慨然允诺,去见太子。惠施对太子说:从前的帝王季历葬于楚山脚下,积水漏流浸塌了墓地,使得棺材的前板露了出来。文王说:哈!先君一定是想见见群臣百姓了吧,所以使积水浸塌的棺材前板露了出来。于是将棺材挖出,搭好帐幕,百姓朝拜三日后再安葬。这就是文王处理此事的标准。现在魏王安葬的日子虽已定,雪下得却这么大,高及牛的眼睛。道路难行。这是由于先王想再停几天,扶助社稷、安抚百姓才使雪下得这样大。因此而更改日期,这也是文王当年的处理方法,假若您不这样做,难道是羞于效法文王吗?太子听了惠施援引古例的类比分析,心里折服说:很好,暂缓几天,另定安葬日期吧。矛盾如此尖锐,群臣的意见:雪这么大举行丧礼,必定是“民必甚病之,官费又恐不给”,即劳民伤财。请改日安葬,而太子却以为人子,“不行先王之丧,不义也”加以拒绝,而且说:不要再说了。面对僵局,惠施从容不迫,用一个类比推理,就说服了太子,不能不令人惊叹于惠施对譬喻推论方法的娴熟。惠施应用这种譬喻推论如此得心应手,除了他对自然、社会现象的深刻观察与研究外,还得益于他对思辩本身所作的精湛研究。从理论的高度概括出所谓譬喻推论就是:
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
惠施之后的后期墨家对譬也有个定义:
譬也者,举他物而以明之也。
东汉王符也说:
夫譬喻也者,生于直告之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
物之有然否也,非以其文也,必以其真也。
与惠施关于譬的定义相对照,可以看出惠施在名辩思潮中第一个提出譬的定义的深远影响及意义。
二、尹文子名的理论
尹文(约前360~前280),齐国人。战国时名家代表人物之一。生当齐宣王、齐滑王时代。与名家另一代表人物宋钎(jian读音肩)齐名,并称宋尹学派。宋铆、尹文、田骈(pin读音蹁)、彭蒙、慎到等辩者同在齐国稷下学宫游学。在稷下学宫游学的除名家学派的人物外,尚有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学派的人物。在不断的辩论过程中,各自形成自己的特色,具有较多共同点的学者或学说遂成为一派。尹文学说的形成正是稷下学风的体现,它兼儒墨,合道法,广收并纳,而自成一家。
在政治上,他反对诸侯间的兼并战争。他的主张是“禁暴息兵”,救世之战,即禁止攻伐,止息兵事。他以“宽”、“恕”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主张“见侮不辱”,救民之斗,即如能从思想上认识到被他人欺侮而不感到耻辱,就可以使天下安宁、太平。《汉书·艺文志》列尹文为名家第二人,著录有《尹文子》一篇。记有“说齐宣王,先公孙龙”。另一位汉朝人高诱说:
尹文,齐人。作《名书》一篇,在公孙龙前,公孙龙称之。
可陪《名书》早巳失传。流传至今的《尹文子》一书包括《大道上》、《大道下》两篇。或以为是伪书。虽不一定是尹文所写,但梁启超认为,其为“先秦古籍毫无可疑”。我们着眼于考察其名辩思想方面的贡献。而《尹文子》一书在名辩方面的贡献集中表现在关于名的阐述。
1.尹文论名
《尹文子》认为名的本质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表达与称谓。客观对象产生时并不具有各自的名称。纷繁复杂的万千对象各自所具有的性质:方、圆、黑、白等是本来就存在的,而正因为大干世界的万事万物各有各的性质,名才有其反映、称谓的对象。这就是《尹文子》所说的“形生于不称,则群形自得其方圆,则众名得其所称也”。此处所谓“形”即指有形之物,又与“实”同义。这说明形、实是第一性,是根本的。有了形、实,才有对它们的反映、称谓,才能表达这些形、实,进行交流,这显然是唯物主义的。
由名是对实的反映、称谓这一名的本质,我们可以看出名的作用之一即是名以指实。除此之外,《尹文子》还认为对不同的实,给以不同的名,因而名不仅指实,而且通过名可以区别形、实,即区别不同的客观对象。这就是“名者,名形者也”,“有名,故名以正形。今万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则乱”。世上万物千姿百态,纷繁复杂,不用名称、概念去反映、称谓,就会产生混乱。这是从物(形、实)出发,一旦由于对物(形、实)加以反映而形成一个正确的名,那么这个名就有对形、实的规范和检验的作用。
这就是所谓“名以检形”、“名以定事”、“名称者别彼此而检虚实者也”。当然,从形、实的角度看,不仅要依形而定名,而且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名罗列在那儿,必须有其形、实与其相应。否则同样会陷于混乱。这就是“万名俱列,不以形应之则乖”。不论是“以名正形”,还是“以形正名”,虽然前提不同,但其归宿、其目的或原则是同一的,即要求名、形相符。这就是《尹文子》的“正名”要求。
“以形正名”,即依据形来给以相应的名。这体现出形(实)第一性的唯物主义观点。“以名正形”,则说明,一旦在人的认识中对某个或某类对象形成了一个正确的名,经过约定俗成为社会所公认,那么名就对形(实)有认知、区别、规定的作用。名不指形,形不应名,即名不正,危害极大,使人们的正常交流成为不可能。因此对名不正的形名关系不可不加以纠正。正如《尹文子》上指出的“名不可不辩也”,“名称者不可不察也”。名正,则万事不乱。
相反,如果名不符实,实不符名,名实丧乱就会产生种种恶果。《尹文子》中除理论上的论述外,还举了一些实例,恰到好处地论证了名实不符引起的种种情况:齐宣王好射,“悦其名而丧其实”;黄公好谦,使得卫国鳏夫“违名而得实”;欲献凤凰给楚王的楚人及卖山雉的骗子却“违实而得名”等。不仅如此,《尹文子》中还谈到了同一语词表达不同概念的问题。“周人怀璞”、庄里丈人为儿子起名“盗”、“殴”,康衢长者为家童取名“善搏”,家犬取名“善噬”,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例子。幽默、诙谐、生动,给入以启迪、思考。
关于名的种类,《尹文子》作出了这样的划分,“命物之名”、“毁誉之名”及“况谓之名”。命物之名是对具体的有形之物属性命名得到的名称、概念,如方、圆、黑、白;“毁誉之名”是反映毁谤与称赞所用名称、概念,如善、恶、贵、贱;“况谓之名”是描述说明表达主观感情的名称、概念,如贤、愚、爱、憎。这种分类显然没有什么逻辑意味,显得粗糙、肤浅。值得注意的是《尹文子》中对“名”与“分”的区分。分为两种情况,一种如“好牛”、“好马”、“好人”,等等。其中“好”是属性概念,“牛”、“马”、“人”则是实体概念。在《尹文子》中,“牛”、“马”、“人”称为名,而“好”则称为“分”。在人们思维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区分“名”与“分”。牛不是好,好不是牛。合在一起表达一个概念“好牛”,好与牛分开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可混淆“名”与“分”。另一种隋况如喜欢白色、憎恶黑色,爱好甜味、讨厌苦味等,其中“喜欢”、“憎恶”、“爱好”、“讨厌”是主观性的概念,而“白色”、“黑色”、“甜味”、“苦味”则是客观性的概念。在《尹文子》中,前者“喜欢”、“憎恶”等称为“分”,后者“白色”、“黑色”等称为“名”,同样要求“名”与“分”不可混同。
《尹文子》中关于“名”与“分”的区分对于名辩思想的发展与名辩学的建立有重要意义。公孙龙的《白马论》中有“色非形,形非色”的区分,很难说不是受了《尹文子》中“好非牛、牛非好”的影响与启发。特别是公孙龙《指物论》中对“指”与“物指”两个范畴的分析,可以说是对《尹文子》区分“名”与“分”,即好(分)、牛(名)这一思想的发展与提高。《指物论》中的“指”是不与任何具体对象相结合的事物属性,如抽象的“白”、“坚”。而一旦与具体对象相结合,这些事物属性如白马之白、坚石之坚,这些具体的白、坚就称为“物指”。虽然没有确凿的材料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但从这二者的内在联系上看,不能否认公孙龙受到了《尹文子》对“好牛”
这个概念中两个构成成分“好”与“牛”明确加以区分的影响。
2.与齐王论士
尹文,作为稷下学宫的一位著名辩士,先秦的文献中保存了一些他的言行事迹。他与齐王讨论什么是“士”这件事,不仅使我们领略了其善辩的风采,而且也使我们看到其中所涉及的名辩学的定义问题。
《公孙龙子·迹府》及《吕氏春秋·正名》都记载了这件事。齐王对尹文说,我很喜欢士,而齐国却没有士,这是为什么呢?尹文说,我很想知道大王所说的士是什么样的人。齐王不能回答。尹文说,现有一种人侍奉国君很忠诚,服侍父母很孝顺,与朋友交往讲诚信,与乡邻相处很和顺,有这样四种道德品行的人,可以称他为士吗?齐王说,好!
这正是我所说的士啊!尹文说,大王若得到这样的人,肯以他做自己的臣子吗?齐王说,那是我所希望而得不到的。这时,齐王正提倡勇敢。于是尹文说,假使这人在大庭广众中间,受到侵害、欺侮而最终不敢起来搏斗,大王仍以这样的人做臣子吗?齐王说,这样的人怎么能算士呢!被侵害、欺侮而不敢搏斗,这是耻辱!忍受耻辱的人,我是不能用他为臣的。尹文说,他虽然被侵侮而不敢搏斗,但并未失掉他的四种道德品行,此人没有失去他的四种道德品行,也就是没有失去他作为士的条件。然而大王一会儿以他为臣,一会儿不以此人为臣,难道大王刚才所说的士,不算士了吗?齐王没法回答。尹文说,杀人的要判死刑,伤人的要受惩罚。人们惧怕大王的法律规定,受到侵害、欺侮而终不敢起来搏斗,这是维护大王的法令啊。然而大王却不用他做您的臣子,这是对他的处罚。而且大王认为人不敢争斗是耻辱,必然认为敢于争斗是光荣,而用敢于争斗的人做臣子,这是奖赏他。您所奖赏的正是官吏所要惩罚的。大王认为对的,正是法令所要惩罚的。这样,赏、罚,对、错岂不相互错乱,矛盾了吗?齐王无话可说。
尹文的滔滔宏论令齐王语塞。究其原因,作为著名的辩者,尹文的名辩艺术使他在与齐王论士过程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左右了整个论辩过程。具体说来,尹文替齐王给“士”下了一个定义:所谓士就是具备忠、孝、信、顺四种道德品行的人。虽然这个定义齐王认可了,但当尹文提出虽有此四行的人被欺侮时却不敢于起来争斗能否成为士的时候,齐王予以否认。因为齐王认为人受欺侮应敢于争斗。显然,齐王所认可的关于士的定义范围太宽了。
“士”的内涵中缺少了受欺侮敢争斗这一条,这样就使齐王陷入了“有忠、孝、信、顺四行可以为士”与“有此四行不可以为士”的矛盾之中。其次,尹文又从国家法令“杀人者死、伤人者刑”与“士”敢与不敢争斗的关系人手,分析出敢于争斗则违法,不敢于争斗则合法,其结果是“上之所是”(齐王所肯定的)恰是“法之所非”(法令所要惩处)的。使齐王又陷于自相矛盾之中,而“无以应”。
尹文运用名辩方法揭示论敌言论中所蕴涵的矛盾,从而战胜对方。我们不能不由衷地佩服尹文高超的名辩艺术手法。
三、公孙龙的思想体系及其名辩贡献
与惠施并称“辩者之囿(尤)”的公孙龙是中国古代名辩思想发展阶段的一个中坚分子。他在名辩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他的思想理论自成体系。
他与其他辩者提出的诸多辩题,特别是他对“白马非马”
这一命题的论证极大地刺激了名辩思想的发展。毫不夸张地说,从先秦至今仍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足见其中所蕴涵的名辩艺术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