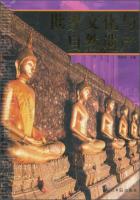从上面罗列的各点可以看出,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对先秦诸子的学说大体进行了全盘考察,从先秦学术发展的整体走势到每家学术的主旨均有所研究,而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对各家学说的进步性的评价。他的评判标准是“以人民为本位”:“批评古人,我想一定要同法官断狱一样,须得十分周详,然后才不致有所冤屈。法官是依据法律来判决是非曲直的,我呢是依据道理。道理是什么呢?便是以人民为本位的这种思想。合乎这种道理的便是善,反之便是恶。我之所以比较推崇孔子与孟轲,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在各家中是比较富于人民本位的色彩。荀子已经渐从这种中心思想脱离,但是没有达到后代儒者那样下流无耻的地步。”
但是郭沫若有关先秦学术的观察和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相比,差异极大。结合前面的研讨,我们可知,这就是他对先秦学说的“总清算”和对其批评的“总答覆”。《十批判书》和《中国通史简编》有关先秦诸子评价的问题,内容十分丰富和复杂,全面评价其观点不是这篇小文所能承担的。但是从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肯定《十批判书》和《中国通史简编》等书的观点存在直接的呼应关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十批判书》对先秦思想的全面而系统的研究的动因,主要来自于作者对同道的批评的回应。虽然我们不能绝对地说《中国通史简编》是《十批判书》唯一的理论对象,但是就其观点的全面性和权威性而言,类似《中国通史简编》的观点正是引发郭沫若撰写《十批判书》的重要因素。这是我们今天阅读和研究《十批判书》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十批判书》的撰写发端于延安和大后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环境和学术风气。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当局对进步思想的政治压迫反而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盛,党领导下的历史学研究在中国通史编撰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这是《十批判书》得以产生的整体学术环境。但是《十批判书》的写作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墨子的思想》是直接的动因。郭沫若看到了延安方面的《中国通史简编》等著作,对其中有关先秦诸子的评价不很赞成。此后《群众》周刊编辑乔冠华来约稿,他就写了《墨子的思想》,以批评以墨子为“工农革命的代表”的观点,这一观点与党内《中国通史简编》等书对墨子的主流评价大相径庭。郭文发表之后,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以及延安方面的不满,《群众》周刊还刊发了对郭沫若的商榷和批评文章。这样的批评让郭沫若很不安,也很不服气,所以他就对先秦诸子的思想进行了全盘的清算,写成了一系列的文章,以作为他对这些批评意见的总答覆。在某些小的方面,郭沫若做了一些让步(比如《孔墨思想的批判》中取消认为墨子反动的说法),但是在大的方面他基本坚持了自己的立场。最后在编辑成书时,他把不成系统的《墨子的思想》等编为《青铜时代》,而把他自己认为成系统的见解编为《十批判书》。
明确了《十批判书》的理论对象和写作意图,我们就能更好地评估其学术价值和思想意义。
第一,郭沫若对先秦学术的考察本身就有极大的价值。尽管他的某些论断随着考古新发现和时代的发展而显得不准确了,但是他的宏观视野和理论基础对于我们今天继续推进研究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十批判书》重要贡献之一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标准,对先秦诸子进行了一番总清算。他对先秦学术思想主线的考察,充分肯定了老子学说的巨大影响,以道儒两家为先秦学说的主轴,很有见地。他力主老子先于孔子,尤具卓识,这也已经为今天的考古发现所证实。而他对各家学术的评价,也有不同的成绩,这方面已经有学者进行了研究,本文不再赘述。郭老这些研究直接推动了先秦诸子研究的发展,他有关先秦诸子研究的学术史价值,还应该得到更充分的研究和揭示。
第二,《十批判书》展现了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马克思主义史学就是在不断的战斗中发展起来的。范文澜编写《中国通史简编》对墨子的称颂,郭沫若的《墨子的思想》对墨子的批评,学术界对郭沫若的批评和《十批判书》的总答覆,这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学术论争的完全回合。而郭沫若作为这场马克思主义学术论争的中心人物,不仅留下了《十批判书》这样一部力作,也推动了学术研究的进步。这是中国现代史学史,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一个重要事件。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研究先秦诸子的动因之一就是批评学术界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他以实际行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是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的一个极佳例证。这场学术争论上承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下启共和国的学术论争,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对于研究中国现代学术史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术史都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以往对此论战没有足够的重视,今后对于这场论争以及抗战期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研究应该加强。
第三,《十批判书》的写作过程表明,我们不能脱离此书的创作的具体背景来就事论事。以往有人认为《十批判书》是直接针对国民党的文化统治政策是简单化的说法,不符合抗战时期学术史的实际。而某些学者认为《十批判书》抄袭《先秦诸子系年》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说《十批判书》抄袭《先秦诸子系年》的一个默认的前提是郭沫若是在无人所知的情况下闭门造车。但是我们考察《十批判书》的写作过程中可知,这部书本身是在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氛围中写出的,其写作过程充满了和当时人物和观点的互动、碰撞和交锋。因为时局的关系(大后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战斗性,这场讨论的焦点是先秦学术的发展大势和先秦诸子思想的属性(是革命和进步的还是反动和保守的),因此《十批判书》的主脑也集中于此,其主要贡献和不足也在于此。这和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有完全不同的问题意识,因此这两者呈现完全不同的面貌。举例说来,在《十批判书》中,老子及道家思想和孔子及儒家思想一起成为左右先秦思想发展大势的主要思想流派,这是《十批判书》主要观点之一,但是钱穆认为老子思想为晚出,甚至晚于庄子,对老子的研究并不占主要地位。这就是一个重大的差别。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主要是史实考证,其中有关老子的《老子杂考》基本是考证老子有无其人,《道德经》作于何时,略无一言及其评价(也不可能作出评价)。而《十批判书》中的《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的主要工作是清算道家学派,以回答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对老子的反动的评价。并且郭老对于道家思想早有研究,他在《十批判书》中有关观点,延续了他本人在1934年发表的有关论文的见解。余文所指各节,在郭书中均属于小节,非其研究重心所在。因此认为郭沫若抄袭钱穆的著作,是脱离了《十批判书》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具体语境的错误说法,实不能成立。我们今天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开展对《十批判书》的学术价值的研究,必须密切联系作者所处的总体背景和具体情境,这方面还有大量工作可做。
[作者简介:戚学民,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