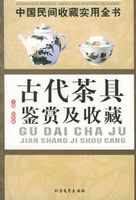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为分析美学的反本质主义倾向提供了最重要的动力。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概念,以及他对“美的”一词的用法的澄清,在美学领域中引起了对艺术的审美本质的普遍怀疑。在这一背景下,维茨等美学家认为对艺术进行本质规定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而传统的艺术定义,包括借助审美经验来进行的定义,都是错误地使用语言的结果。迪基(G.Dickie)在与比尔兹利(M.Beardsley)的著名争论中,通过对比尔兹利使用的“审美经验”一词的分析,不仅把“审美态度”理论斥为“神话”,进而认为根本不存在“审美经验”这种东西,而迪基本人对艺术的“制度性定义”已经完全避免了对审美经验的依赖。艺术的定义问题在当代分析美学中引发了大规模的争论,在此不再叙述。但是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不管是坚持审美经验在艺术中的价值的美学家,还是要求取消审美经验这一概念的美学家,都认为用审美经验、审美特性等等来规定艺术的本质是不充分的。
由此,“艺术的审美理论”被拓展开来,不再囿于旧的自律美学的疆界。这种拓展至少是在两个向度上推进的。首先是对审美态度理论的拓展。即反对把无利害的“审美态度”,或者对艺术品本身的兴趣作为产生艺术经验的唯一条件,而认为理解、接受艺术的过程涉及多种因素,特别是认知的因素。例如,对一个艺术作品的欣赏往往要涉及对它产生的历史背景的知识的了解,或者需要对作者的意图进行假设。这些知识或者假设是传统的审美态度理论所忽略的,但它们往往有助于我们以恰当的方式对艺术品进行反应,甚至构成了产生正当的审美经验的必要条件。第二,是对艺术的审美价值理论的拓展,即认为艺术品的价值并不唯一地在于引起那种无利害的愉悦。艺术品的道德价值、认知价值等,可以是其艺术价值的构成要素。
这样的拓展对于理解电影等大众艺术尤为重要,因为这些通俗艺术很难被纳入先前的审美理论的范畴。“审美态度”的“三D特征”很难说是对我们欣赏电影的方式的正确表述,很难说对一部标准的好莱坞电影的“静观”是什么意思。并且“无利害的愉悦”也不能够刻画我们对大多数电影和大多数当代艺术的感受,如对黑人电影、女权主义艺术等等的正确欣赏必须包括对其政治、社会内容的理解。而拓展后的理论,特别是把认识要素纳入对艺术欣赏的解释,有助于说明电影欣赏中的许多现象。例如,一部恐怖片往往旨在引起观众的恐惧,但恐惧的情感并不单纯是由影片的形式要素(例如恐怖的怪物的造型、惊悚的画面或音乐)所决定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我们对影片中受到威胁的角色的“感同身受”,是替这些角色而恐惧,或者因为他们而感到恐惧。而我们和角色之间之所以能够形成这样的情感纽带,往往需要以某种方式涉及对角色的道德评价——我们为善良无辜的正面角色而担忧、害怕,但当被恐惧所威胁的角色是反面人物时,我们往往不会如此,至少不会为他们感到强烈的担心。也就是说,观赏这种电影时,道德评价促使产生了情感体验,我们对角色的道德态度是我们对他们的情感反应的必要成分。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在论及悲剧时早已说明了这一点,因为悲剧产生的怜悯之情在很大程度上被他视为我们对悲剧主角的感受,而这种感受内在地包含了我们对悲剧主角的道德评价——他们是比我们高尚而又犯了过失的人物。
也许会有人反对说,这只是表明了对艺术的欣赏需要涉及认知或者道德评价,但并不意味着艺术的审美价值需要涉及道德价值和认知价值;或者说,道德和认知只是实现审美价值的手段而并不构成审美价值本身。确实,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强弱”两种认知主义主张。“弱的认知主义立场”只坚持对艺术的理解会涉及认知过程,而“强的认知主义立场”则不仅坚持对艺术的理解需要涉及认知过程,并且坚持艺术品的认知价值可以是其审美价值的正当成分,没有独立于认识价值的审美价值。稍后我们将看到,这两种主张都在电影的认知理论中有所体现。
2.审美经验的现象学解释到认识论解释的转向
反本质主义者的概念澄清,打破了“审美经验自成一类”之类的“神话”,但是多数人并不赞成因此而彻底否定审美经验,而是寻求更有效的解释审美经验的方式。但此时的“审美经验”已经不再是一个浑然一体、抗拒分析的特殊概念,它也不再只能依靠自身(“以自身为目的的”,“自身有价值的”)来说明自身的优越地位。艺术引起的审美经验与别的经验或反应一样,在各种语境中、各种条件下会产生正当和不正当之别,会有效果上的好和不好之分。这要求人们联系社会、历史、文化的各种因素,来对审美经验产生的条件、所涉及的内容及其恰当性标准进行说明。这种要求在分析美学中引起了审美经验的解释的认识论转向。
认识论转向之前的审美经验概念,被称之为“现象学的审美经验概念”。需要说明,这里的“现象学”并不是指以胡塞尔、海德格尔为代表的作为哲学学派的现象学(尽管与之相关),而主要指“现象主义”。早期分析哲学中的逻辑实证主义提出了命题的证实原则,即证实分析命题的方法是演绎推理,而证实综合命题的方法是经验证实。凡是对事实有所断定的命题都属于综合命题,因此“X是美的”也属于综合命题,其有效性也需要经验证实。但是,经验证实是一个需要不断验证的过程,它必须最终被归为一个自身无须接受验证的终极尺度。这一尺度何在?维也纳学派的代表人物石里克认为,检验尺度必须是一切知识的确定性基础,这就是终极的经验,即个人的直接感觉状态。他把个人的直接感觉称为“给予”,并指出“每个命题的意义只有通过给予才能确定下来”。
这种把个人的“给予”视为无须检验的终极经验的观点就是“现象主义”。后期维特根斯坦在其“私有语言论题”中不遗余力地反对心理主义,实际上也包括对现象主义的反对,因为所谓的“私人语言”所指称的恰恰就是个人直接的、私有的感受。同样,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直接影响到了分析美学对审美经验的理解。后来赖尔关于“机器中的幽灵”的论证,更进一步要求取消笛卡儿意义上的心理性实体。
“现象学的审美经验概念”要求把握的是“具有这种经验像什么样”,即把审美经验视为一种内省性的、只能被个人直接感受到的心理现象。体验者对这种感受的报告成为不可再分析的终极陈述。在分析美学中,现象学的审美经验概念的主要坚持者是比尔兹利。他把审美对象称之为“现象”,而审美经验是通达这一“现象”的唯一途径。对这一概念最早、最著名的批评来自迪基,他指出比尔兹利在谈论审美经验的统一性、完满性和强烈性等特性时,实际上是在把作为艺术作品特性的统一性、完满性和强烈性与审美经验本身的特性混为一谈。并且,迪基进一步质疑根本不存在具有统一性、完满性的经验。这种批评促使比尔兹利不断修正自己的理论。并且,这一批评不仅在比尔兹利那里,也在整个分析传统的美学中导致了朝向“认识论的审美经验概念”的转向。简单地说,“认识论的审美经验概念”要把握的不再是那种私人的、直接的感受性质,而是要把握一种以适当方式对审美对象进行的认识。也就是说,审美经验的认识论概念要把握具有这种经验的主体以适当方式对经验对象的认识,而这种认识需要根据对象的客观属性来加以解释。
前面已经提到,康德美学带来的“认识论转向”,是从关注审美对象转移到关注我们主观方面对对象的审美判断,而这里的“认识论转向”意味着什么?要理清这个转向中涉及的众多理论问题和它发展的历史脉络,需要比这大得多的篇幅。并且,并非所有的问题都与我们的主题有关。所以,在此我只提出一个笼统的看法。简单说来,我们可以把这次转向理解为一种在主观当中寻找客观性的努力。联系到分析哲学一直以来对心理主义的反对,我们可以简单地说,“现象学”概念想要把握的那种审美经验的内容是绝对主观的——它“是个体、统一体,属于某人在某时的属性(也许是大脑的属性)”。它具有绝对主观的、绝对为我所有的、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的感受性质。分析美学反对依据这种心理内容来解释审美经验,因为它不仅不可观察,并且也不出现在我们对自己的心理状态的描述当中,即它不是我们关于审美经验的描述的指称对象。在当代心灵哲学中,一般把现象学的经验概念试图把握的那种经验性质称之为“感受性质quilia”,或者“现象性质”,或者经验的“质的维度”。
多数分析哲学家认为,当我们描述自己的心理状态时,例如说“我高兴”“我害怕”时,我们所描述的并不是这类性质。可参考维特根斯坦与此有关的比喻:“假如每个人都有一个装着某种东西的盒子:我们把盒子里的东西称为‘甲虫’。每个人都不能看别人的盒子,所以每个人都说只有看自己的盒子才知道甲虫是什么样子。——也许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每个人的盒子里的东西各不相同,而且这种东西还在不断变化。”“假如‘甲虫’这个词在这些人的语言中有着一种用法呢?——如果有一种用法,那它不会充当一事物的名称。盒子里的东西在语言游戏中没有任何地位,甚至把它当做某种东西的地位都没有,因为盒子甚至也可能是空的。——是的,人们可能把盒子里的东西‘除尽’。它消去了,不管它是什么。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根据‘对象与名称’的模式来解释感觉表达式的语法,那么对象将作为完全无关的东西而被排除在外。”(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93节)可以认为,审美经验解释中的认识论转向是在分析哲学反对私人语言的更大背景之下产生的。需要指出,持审美经验的认识论立场,并不需要反对这种感受的存在;但认识论立场必须强调的是,这种感受并不是使审美经验成为审美经验的原因,也不是美学研究的正当对象。相反,认识论立场试图从引起审美经验的原因和条件来对之进行说明,也就是说,用主体通过正当方式对艺术作品的特性的认识来加以说明。并且,这种认识需要用作品的物理属性加以解释。因此,分析美学对“客观性”的这种追求,可以视为采取了一条共同的途径来试图对柏拉图提出的一个古老问题做出回答。在《会饮篇》中,柏拉图追问:“我们究竟是因为X是可爱的才爱X,还是因为我们爱X才宣称X是可爱的?”如果选择前一种思路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站在客观主义的立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