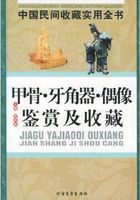电影研究中的认知主义(cognitivism)立场,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就已经出现,但其兴起的标志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两部在电影研究界引起轩然大波的著作。一部是电影理论家大卫·波德维尔对当代电影批评的批评——《制造意义:电影解释中的推理和修辞》,另一部则是哲学美学家诺埃尔·卡罗尔对当代电影理论的批评——《神话电影》。此外,认知主义电影研究在电影心理学(例如约瑟夫·安德森、巴巴拉·安德森)、电影美学(例如诺埃尔·卡罗尔、贝里斯·高特、格利高里·居里)、历史研究(例如大卫·波德维尔、斯蒂芬·普林斯)以及关于电影公司和全球市场化的工业研究等领域展开。它们被统称为“认知主义电影理论”(cognitive film theory)。这些研究在风格与兴趣方面体现出了一些重要的共同特征,但是要具体说明共同的研究原则或者理论信仰是什么,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如果可能的话)。
狭义的认知主义电影理论,指运用当代“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方法研究电影的理论。大卫·波德维尔的工作,可以视为这方面较为普遍的代表。认知心理学强调研究人的认知过程,并且主要持信息加工观点(大脑—计算机的类比),把认知过程作为选择、转换、储存和处理感觉信息的过程来研究。
广义的认知主义电影研究并不一定信奉认知心理学的理论预设,尤其是人机类比的假定。这些研究者仅仅坚持,对电影的接受和理解需要涉及理性认识——推断、评价、判断、假设等等。心理学意义上的“认知”和哲学意义上的“认识”在英文中是同一个单词——cognition,尽管各自强调的研究方式不同,但都研究获得知识和使用知识的途径。因此,广义的认知主义电影研究又被称为“电影的认识论”。认知科学运动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系统地从认知途径来研究电影无疑受到这一运动的推动。但广义的认知主义途径却并不是认知科学所独有的,它可以追溯到古代。例如,对于许多哲学家来说,亚里士多德就堪称最早的认知主义者,他将情感等身心状态定义为某种由认识所导致的感受。比如,恐惧是某种“痛苦或痛感,是由关于未来的失败,或者由对令人痛苦的邪恶的相信所引起的”。而在电影研究中,明斯特伯格和阿恩海姆的古典电影理论,也被认为具有认知主义要素。本文所指的认知主义是广义的认知主义。
需要指出,不管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认知电影理论,都不是一种专门的理论。首先,认知主义者研究的领域各不相同,没有人试图用一种整体性的理论来指导不同研究领域的研究,也没有人认为这些在不同领域中开展的认知电影研究能够形成一种统一的理论。其次,并不存在公认的“认知主义”纲领或者原则。事实上,多数认知理论家具有一种反对形成统一理论的强烈倾向,并将这一点视为认知理论区别于其他电影理论的一个特征。
我们看到,在这样理解之下的认知理论,具有方法和前提上的多样性,并且内在地抗拒对它进行整体性的特征概括。即使在心理—物理的关系方面,在认知电影理论中,既有否定心理取消论的大脑—计算机的类比,也有主张心理内容不可还原的心理主义,既有吉布森影响下的根据“直接知觉理论”来研究电影视知觉的“生态学”方法(例如安德森夫妇),也有格利高里·居里影响下的建构主义观点(例如大卫·波德维尔)。因此,认知理论家普遍认为,最好把认知主义视为一种“角度”(perspective)而不是一种“理论”,在这种角度之下,包含了各种各样的甚至彼此冲突的理论。例如卡罗尔曾多次告诫说,认知主义研究必须警惕“大理论”的倾向,而应该针对具体语境中的问题来选择适合的理论和模式。但是,对电影理论中针对各种具体问题而进行的认知主义研究进行全面考察,显然超出了我们的能力。我们只关注电影引起的情感反应问题的认知主义研究。
电影被称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艺术样式。我们不妨把这种拟人化的说法表述得更直接些,把电影的“影响力”视为电影引起观众的各种反应的能力。而情感反应无疑是观众反应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需要做出一个限定:本文讨论的情感反应,主要指主流商业电影或“剧情片”(movie)引起的情感反应,而不是对所有“电影”(cinema)而言。对于人们习见的那些商业电影,与其他艺术门类相比,以下看法至少在直觉上是正确的:第一,它们往往能够有效地引起许多观众的情感反应;第二,它们往往能够有效地引起观众的强烈的情感反应。并且,许多商业类型电影往往旨在引起特定类型的情感,例如喜剧片、恐怖片、惊悚片等等,都是根据其致力于引起的那种情感类型来定义的,对它们的成功和失败的评价也要根据它们是否有效地引起了那种情感。这两个假定并不是说商业电影比其他艺术的影响更广泛或者更强烈,而只是就我们熟知的关于商业电影的种种事实而言——这也正是它们被称为“大众艺术”或者通俗艺术的原因。显然,电影引起的反应(包括情感反应)的广度和强度,可以从道德、文化、历史等多种角度来解释,而认知角度只是其中一个角度。我们将讨论认知电影理论在这一问题上提出的各种解释。
尽管难以对认知主义抽象地加以限定,但对电影观众的情感反应问题的研究,我认为有两个重要的知识背景,它们从截然相反的方向促进了认知电影理论的工作。一个背景是英美分析美学中审美经验研究的认识论转向,而另一个背景则是当代电影理论以及文化研究中普遍的反认识论倾向。在我看来,这两种倾向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视为对同一种美学传统进行突破的结果。但它们各自选取了不同的路径,并最终在电影理论中形成了激烈的交锋。这个传统就是艺术的审美理论。
一、审美经验研究的认识论转向
在传统美学中,艺术作品引起的情感属于审美经验的研究范畴。可以说康德开启了美学的“认识论转向”,即从对审美对象的特征的罗列转移到关注我们主观方面对对象的审美判断。但是,当代分析美学在已经属于主观领域的审美经验层面再一次进行“认识论转向”,又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它包含两个既有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向度:第一,是对艺术的审美理论的拓展;第二,是从审美经验的现象学解释到认识论解释的转向。前者主要是反本质主义的结果,即反对依据“审美经验”、“审美特性”等等来规定艺术的本质;而后者则是反对心理主义的结果,在美学中主要体现为反对用现象语言来解释审美经验,或者把审美经验当做自身无须验证的、个人的终极经验。
1.对艺术的审美理论的拓展
先谈对“艺术的审美理论”(aesthetic theory of art)的拓展。康德美学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这一美学框架之下的艺术理论,即根据康德的审美经验概念来定义艺术。在康德那里,审美经验是根据审美对象产生的愉悦来规定的:一个对象引起的审美经验就是从对该对象本身的观照中获得愉悦的经验,它是为着自身的目的而必然有价值的经验,换句话说,这种愉悦是不涉及利害的,而康德用“不关心对象的实存”来说明这种无利害性质。康德把“无利害”作为审美判断的质的规定,并进而构成了美的分析的基础。由此,审美对象引起的经验被理解为一种无利害的愉悦,这种经验因其自身而有价值;同时,对象引起这种经验的功能决定了这个对象是审美对象。
康德并没有提出艺术的定义。然而,他的美学却成为后来的理论家为艺术定义的基础,以至于此后的艺术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无利害”的自律美学的分支,即“艺术的审美理论”。在这种艺术理论中,审美经验或审美特性(作品引起审美经验的那些性质)成为对艺术的本质性规定。至少从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开始,就明确地通过审美经验来定义艺术。贝尔在这一问题上使用的循环定义是众所周知的:艺术的本质即“有意味的形式”。何谓“有意味的形式”?若一个对象引起我们特定的审美经验——贝尔称之为“审美情感”——则该对象是“有意味的形式”。何谓审美情感?“有意味的形式”或者艺术引起的那种经验就是审美情感。也就是说,一方面,艺术的功能(或者价值)就是引起审美经验——无利害的愉悦;另一方面,判断一个对象是不是艺术品,唯一的标准就是它能否引起这种审美经验。“无利害”既是引起那种经验的一个条件(不关心对象实存的、对形式的观照),又描述了那种经验的性质(因自身而有价值的超脱、自由之感)。前者逐渐形成了欣赏艺术的审美态度理论,而后者则关系到艺术的审美价值理论。这样的思想受到19世纪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等艺术运动的推动——“为艺术而艺术就意味着艺术为其所产生的经验而存在”。
我们无意于在此用过多篇幅讨论自律美学的贡献或其局限,我们关注的是,通过这种“无利害的审美经验”来定义艺术是否充分。当代美学和艺术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从各条路径对“无利害”的审美理论进行突破。例如,在欧陆传统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框架下的艺术理论和文化研究致力于发掘艺术经验之下的社会性根源,而后现代立场的解构主义等思潮则更进一步将自律美学的认识论基础加以消解(这在当代电影理论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将在后面详细讨论)。而在英美的分析传统之下,艺术哲学和艺术理论同样试图突破艺术的审美理论,但其突破的路径颇为独特,即借助语言分析而进行的反本质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