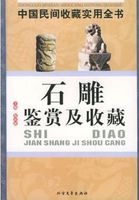此次回无锡,冯云山又来到了周家,说是送还那本印谱,同时问了问《金丝雀》的演出情况。周贻白对他十分警惕,有时候到无锡的公共花园去散步喝茶,总觉得背后有特务跟着。于是他不再多出门,只在家里看书、写剧本,或者整理中国戏剧的历史资料。
1943年,他写了两个话剧剧本:《阳关三叠》和《连环计》。到上海送这两个剧本时,每次都来去匆匆。《阳关三叠》只看了一次排演,《连环计》只和唐槐秋共同排了一次——演员陈玉麟扮演剧中的吕布,一些身段是周贻白排的。由于此次需要排练,因此向冯云山说明要多耽搁四五天,但是正式上演时,他仍然没有看到。
1944年至1945年,日伪当局朝不保夕。然而,中国旅行剧团也举步维艰。唐槐秋把中旅的演员分到绿宝、美华、丽华三个戏馆演出,不再需要新剧本。周贻白则继续在无锡写了《云淡风轻》、《姊妹心》、《花蝴蝶》、《三星拱照》等现实题材的话剧,又为中实剧团写了话剧《天外天》。此外,还写了若干话剧或电影的“本事”,如《花蕊夫人》、《侠骨柔肠》、《水性杨花》、《海阔天空》、《火之洗礼》等。至于已上演的《绿窗红泪》、《金丝雀》、《阳关三叠》、《连环计》等话剧剧本,则已由世界书局出版。
三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日本投降。在此前后,中旅和其他职业性的话剧团体大都走上了商业化戏剧的道路。战后,唐槐秋赖以生存的三个戏馆全都垮了,上海滩上到处纸醉金迷,严肃的话剧更加低迷。周贻白在1945年第6期的《朝雾》杂志上写了一篇论文,名《三十六种剧情的检讨》,其中涉及到这种情形:
中国的话剧,除开以前的文明新戏不算,从理论鼓吹,到舞台实践,总计不到二十年工夫。近年来居然发展到一地有十数团体,同时作职业表演。这情形不但是我们在民国十五六年初干话剧时不曾想到,就是在事变后一二年间,也没有做过这种期望。尤其是上海,那时大家都把这一隅之地比作一所孤岛。劫后烬余,关于一切事情都不免有筚路蓝缕之慨。复兴的急务当然谈不到话剧上去。
然而,不久的时间,上海的商业忽然呈现一种畸形的发展。于是,娱乐事业亦因之而获得苏生的机会。这期间话剧也好像出笼的商品一样,从纯艺术的立场,一步步向职业途径上迈进。赢利竞争的结果,因而造成今日剧团的繁兴与观众的攘夺。
话剧在上海固然是兴盛了,其光焰之烛照殊不亚于民国初年的文明新戏,不过,这种兴盛的现状却不一定是话剧本身的进步。而是,话剧在商业上有了相当价值,可以培育着使之源源生产,然后有人输以资本,才使其蔓延滋生地蓬勃起来。换一句话说,现在的话剧是企业家一种赚钱的工具,不管是剧本、导演、演员,乃至剧场的杂役,都只有一个目的,这目的就是利润的获得。至于戏剧的使命、剧本的意识、导演的修养、演员的技术,都用不着吹求。因为在企业家的眼中,只要卖座好,演期能够长久,便是好戏。反之,纵然你把上述种种说得入微尽妙,如果售座不佳,一切都是废话。因此,上海的话剧,与其说是为了戏剧,不如说是为了商业。同年,周贻白在《中国戏剧小史》中亦称:这一时期虽然剧团增多,但是因利益驱动。翻译的外国剧本“不惜点金成铁而去迎合一般观众”;大多数人的趋向“专向闹剧方面取材”;“一般聪明的剧作家虽有创作,亦必移其观点于卖座之盛衰”;“于是大鼓书、小调、皮黄剧、流行歌曲、色情舞蹈、刺激动作都一一表演于剧中”;“批评者亦复以卖座盛衰而作艺术之估价。”
这一点他是深有体会的。受新文化运动以来戏剧观念的影响,特别是受易卜生现实主义的“社会戏剧观”的影响,他比较重视戏剧的社会功能。如前所述,他创作历史题材的戏剧往往注重“去芜存精地注入新的生命”;现实题材则注重“处处吻合时势趣向,幕幕含有警世意味”,甚至认为这能够体现时代戏剧的演进。
1939年阿英的话剧《碧血花》上演后,他在11月11日的《大美晚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明末遗恨”——话剧与皮黄的比较观》。文中说:“中国之为异族宰割,固然不止一次,……而整个版图的变色,则为宋明两代,……悲怆之史实,在民族意义上说来,这不能不算是一种无可补偿的损失。”在旧剧中,“南宋之亡,不亡于朱仙镇班师,而亡于崖山殉主”,“当战不战,不和而和,直到把整个江山送于他人,方才瞑目”;明代亡国,亡于崇祯皇帝的“煤山殉国”,名人官员则“当死不死,不降而降,情愿缩着龟头,留下狗尾,把姓名挤入贰臣传,才算甘心”。
又说:在旧剧中,“朝代的兴废都只描写了一个帝王的下场”,“所谓‘《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真正的亡国惨状,在民间何止千百倍于此?”在这个意义上,清代末年“皮黄剧《明末遗恨》的意识并不正确”,而魏如晦(阿英)的话剧《碧血花》“以另一种姿态出现”,题材与名称虽亦作《明末遗恨》,“实际上他是另起炉灶,别出钳锤。同时,他又加上一段郑成功焚弃青衫决心复明的动人故事”,“郑成功那把宝剑的光芒,在观众的眼中是颇为辉耀的”。
周贻白本人创作的《朱仙镇》、《北地王》、《李香君》、《花木兰》等历史题材作品,一方面以查考历史故实为根据,另一方面便出自同样那种“另起炉灶,别出钳锤”的创作理念。
1941年10月,在话剧《绿窗红泪》的“自序”中,周贻白从中国戏剧演进的角度更加明确地谈到了他的戏剧观念:中国戏剧,素不侪于著述之林。以其托体近卑,仅能谐俗也。然而,元人杂剧以口语入曲,曾光烛一时。明清传奇承其余风,亦能继之争耀。宜其各有千秋矣!而《续文献通考》以《西厢记》、《琵琶记》列入经籍考,乃被目为怪诞不经,此则卫道者眼光衡文,非戏剧本身之过也。
中国戏剧之起源,或以为始于优孟假孙叔敖衣冠以讽庄王。虽不必即其正轨,而后世“弄参军”者,每借以行其谲谏,则其借题发挥,谈言微中,质亦有所自来。惜中国戏剧自草创至于成形,渐趋入歌舞之歧途而未觉,徒知作故事之传达,不复为意识之安排,其被屏于著述之林,良有以也。
中国话剧之兴起,历史尚浅,征诸往昔,虽宋元院本有不用一曲而纯以口语出之者,然今日之话剧决非由此发展而成。盖贩自舶来,依样模仿,参以己见,另具作风。以其无弦管之嗷嘈,具语言之真实,乃赐以嘉名,命为话剧。此民国十七年事也。当时新铡初试,观众尚觉寥寥,已而逐渐伸张,乃臻今日之全盛。方之民国初年之所谓“文明戏”固不可同日而语,即以之与历史悠长之“皮黄剧”相比较,亦有上下床之别。盖意境既殊,观众之感受各异,运命所趋,断难以口舌争也。
话剧既非专为形态之表达,则其所演之故事不过为剧作者借作发挥之题目而已。其间或讽劝、或箴规、或纠斥、或指示,必当有其中心所欲言者。若徒为观众娱目赏心而作,又何必费如许笔墨,而记此无足惊奇之故事乎?
因此,他撰写的现实题材的《绿窗红泪》、《金丝雀》等作品均带有“或讽劝、或箴规、或纠斥、或指示”的意识形态倾向和道德观念痕迹。
《绿窗红泪》写的是上海滩上的社会世象:一位富孀被情人掌握家产。女儿玉英成人后虽然精明,却陷入了新的爱情与财产的纠葛,再次被骗,终于自杀。周贻白在自序中称:“或谓本人编剧,故事每有所影射。射人乎?射事乎?固亦无人能道其实。……《绿窗红泪》一剧,有无其事不足深究,但姐弟争产,玉英被骗,皆常见之事;而彭福山、常振华亦常见之人(按:彭福山、常振华是剧中以爱情谋取女方家产的两代男人)。至若情夫冒为舅氏、家奴欺骗主人,则更属寻常矣。故曰:事有类于此者,中心有所欲言耳。”
1943年3月创作的《金丝雀》异曲同工,写一位歌舞明星在上海滩的不幸遭遇。其自序称:金丝雀,一自由翱翔之生物也。徒以羽毛茂美,鸣声宛转,遂为人视为玩物。罗而致之,笼而豢之,金碧其所居,丰华其所食,以为遇之至厚,当不复思及野食山岩、栖身林木之日矣。然而,昔人诗曰:“笼鸡有食汤锅近,野鸟无粮天地宽。”金丝雀虽闭置一笼,难遂飞腾之志;豢之者但知赏其羽毛之茂美、鸣声之宛转,吾知其心必有其戚戚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