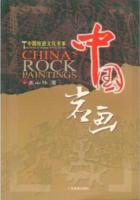在浩瀚的欧洲现代美学中,雅克·马利坦往往为中国人所忽略,作为新托马斯主义的领袖式美学家,他在欧洲却享有盛誉:“20世纪哲学和文化生活中的一支强有力的力量”。马利坦继承了托马斯·阿奎那的宗教思想,在哲学和美学上与之一脉相承。马利坦对阿奎那的思想进行系统、详细的阐述,并且能够融合现代的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等西方哲学进行新的阐释,使宗教哲学焕发新的光彩。马利坦一生著述甚丰,主要著作有《艺术与经院哲学》、《诗的境界及其他》、《诗的现状》、《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艺术家的责任》,其中《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是马利坦的艺术哲学代表作,系统地阐述其美学思想。1952年华盛顿国家艺术馆举办“梅隆美的艺术讲座”,邀请了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教授马利坦作第一个讲座,马利坦为此写了讲稿,这就是《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1953年在美国出版。在该书中,灵魂、艺术、精神、想象、创造性直觉、诗歌、生命、美、诗性体验、顿悟等是关键词,马利坦论述了其内在的关系,全书充盈哲思与诗意融合一致的气息,宗教的神秘色彩和对美的向往、对诗的浪漫气息的品味在鞭辟入里的哲思中端呈于读者面前。马利坦的美学思想阐明了艺术生产中的精神超越的精神动力机制,在审美时空建构过程中艺术家创造性直觉在生命波流中绵延的历程。
第一节审美中的自我与事物
马利坦认为艺术是作为一种精神现象的人类艺术品的生产过程,所以,马利坦意义上的艺术还是从现象学视界进行定义的。而诗是艺术创造活动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内在交流。诗是“事物内部存在与人类自身内部存在之间的相互联系”,“诗是所有艺术的神秘生命”。诗依附艺术,诗赋予艺术以生命。艺术是“一种精神现象的人类艺术品的制作过程”是一种“人类精神创造性的或创作的、产生作品的活动”。按照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观点,艺术还是一种存在,一种活动的存在而不是静止的状态,静止的其实是艺术文本。在艺术和诗中包含着精神的创作性,或者反过来说艺术和诗是人类精神创作性的释放。在诗中精神创作自由达到美的目的,美是诗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而在艺术中精神的创作性要依赖于类型的作品的制作,束缚于作品的物质之中。在创作的自由度上诗超越艺术。
马利坦认为在审美中首先要处理的关系是自然和人之间的关系,自然在人类历史中被赋予意义从而显得美。
大地上的这些地方浸透着人的智慧和辛劳。正是历史,使自然与人的结合得以实现。结果是自然散发出征象和意义,使她的美如花盛开,绚丽多彩。
在审美关系之中,自然和人类保持了自身本质的独立,但在审美之中“被神秘地混合在一起”。在视觉和直觉之中,人类获得审美的愉悦。“自然在某种程度上是走进了人的血液之中并同他一道吐露自己的情怀”。在情感、情怀、血液的波流之中人类和自然达到融合的境界,人获得美感,自然获得审美意义。马利坦认为,自然饱含着情感时更美,这种情感是内蕴认识的情感。
它像那种从所有征象以及意义中产生的情感一样饱含着人对自然的侵入;而且我说过,它构成或形成了视觉中的愉悦。
在征象和意义之中能够产生情感,马利坦这部书一直在强调这一点。智性和理性能够展现生命,智性和想象都是诗的精髓。智性既包括逻辑上的理性,也包括生命深层次的智慧和领悟。同时,马利坦认为无意识对精神产生不明说的意义,在审美之中也有重要的价值。马利坦意义上的智性是包含生命深层次冲动的领悟,与中国禅宗相通。在蕴涵情感的征象中会产生视觉的愉悦体验,愉悦是主体和客体的情感与形象的交融体验。
马利坦阐明了审美之中对立的双方:事物和自我。事物是世上的事物,包含自然的原始的情感。这不无泛神论的观点。更重要的是,事物还包含种种存在、外形、活动等物质和精神上的方面,其实就是作为艺术家的人的“他者”。自我就是有血有肉的精神生存者,包含艺术家的身体和精神的方方面面。
马利坦旁征博引地引用东方艺术案例分析自我和事物之间的种种关系。东方艺术忽略自我,在艺术中观察事物,对事物的生命力隐含的某种宗教意味进行苦思冥想。艺术属于宗教,甚至是巫术活动的一部分。而艺术品在很大程度上没有作为艺术的独立性,而具有作为精神教育的工具价值。“气韵生动”谢赫《古画品录》序中提出的绘画六法:“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是“让生命力表现艺术家在事物中所捕获到的独特的精神共鸣”。活泼的山水画表达了在事物中领悟到的生命的运动和结构的和谐。中国艺术家忘却自我,从而“空故纳万境”(苏轼语),在心灵中领悟体验事物。印度艺术“把自己的灵魂让给了寓于事物之中并成为感觉惊人的精美的传神的狂热性”。事物成为神的“倒映”才有意义,洁净的荷花具有意义是因为神圣的神灵。艺术提供灵魂升华的幻境。艺术为事物所俘虏,沉迷于事物“内在生命的狂热和外在生命的丰饶”。东方艺术朝向事物,朝向群体,表现超自然的事物,同时也隐约地展现自我,这是与西方艺术对立的他者。在西方现代艺术阶段,艺术家强调创造的主观性,对自我的揭示取代了对外在美的描绘,从西方的古典/宗教审美观中解脱出来。西方现代艺术在揭示自我的同时隐约地展现客观事物。“当艺术努力去揭示和表现艺术家的自我时,给艺术以生命的诗性感知,同时,捕获并表现了它们赖以生存的事物最重要的内容、超表面的实在和奥秘的含义。”在创造性直觉/诗性直觉之中,智性、情感和无意识等人类深层次精神与事物融和,艺术展现自我也展现事物。
第二节创造性直觉
创造性直觉(诗性直觉)是诗和艺术的精神动力,它是“存在于人的灵魂的最高级地带的一种纯精神性的活动”存在于人类的精神之中。诗人和艺术家因为更关心创作性自我同客观实在之间的内在交流从而发掘了创造性直觉。
在它们(艺术)中起主要作用的和极大作用的智性或理性不是概念的、推论的、逻辑的理性,甚至也不是工作的理性。而是处在靠近灵魂中心的隐蔽而高级地带的创造性理性。在这种创造性理性中,位于灵魂的各种力量的唯一本源的智性展开它的活动,并与各种力量结合在一起。这就是美的艺术对于实用的艺术的超越。
这里的创造性理性是艺术的力量之源,艺术与智性的关系类似“玫瑰香味与玫瑰”。它与中国禅宗中的禅悟的思维方式极为相似。禅宗动用的是全身心的精神力量,从而实现对世界和人生的把握。创造性直觉具有认识性和创作性,创造性直觉具有感知,在通过意志力和欲望力把握对象,在具体化的生命领悟之中把握事物。这种知性和中国禅宗的悟的思维极其相似。创造性直觉还有一种创作性,这是一种来自生命本原的智性冲动,沉睡在潜意识深渊之中,在生活际遇之中苏醒,从而赋予作品以完形。创造性直觉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先天,是灵魂的自由的想象力,创造性直觉的拥有者倾心于其中,从而更好地发挥创造性直觉。
柏拉图认为疯狂分为人的疯狂和神的疯狂,神的疯狂包括灵感的疯狂、神秘的疯狂、诗的疯狂和情爱的疯狂,神的疯狂实际上可以引申为人的精神带有神性的疯狂,在艺术中人的精神的内在动机很大程度上是神的疯狂。马利坦认为人的精神存在两大类无意识:精神的无意识和与身体本能密切相关的前意识。“存在两大类无意识……处于生命线上的精神的无意识和由肉体、本能、倾向、情结、被压抑的想象和愿望、创伤性回忆所构成的一个紧密的或独立存在的物力论整体的前意识。”精神的无意识与柏拉图的神的疯狂相似,而本能前意识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就基本重合。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在中国影响盛隆,但是艺术与本能无意识的关系相对于精神无意识而言,笔者以为是不可比的,艺术毕竟是一种精神的超越,是一种“神的疯狂”。而智性作为人的一种基本的精神能力,与人的生命紧密相连,精神前意识潜在控制了智性和欲望,在艺术创作中发挥巨大的作用。逻辑、概念、理性这些都成为智性的外在形式,同时也能够对本能的前意识发挥调控作用。精神无意识是一种从属于人的灵魂的精神力量,是认识和创造力的源泉,也是爱欲的源泉。用尼采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具有超越性的精神冲动,也是人生的一种基本的建构性力量。“我们知道我们在想什么,但我们不知道我们怎样在想”,启发性智性渗入意象之中,从而激发潜在的可理解性,启发性智性推动心灵的运行而本身并不被认识。
马利坦划分了人的精神世界,灵魂是人的精神世界的原点,是人的精神力量的源泉,是一切精神现象的最后本原。灵魂的力量贯穿精神的理性和感性活动。人的精神世界可以划分为三个套叠的圆锥。最外面的圆锥是智性的圆锥,智性从灵魂之中产生,智性的外在表现形成圆锥的下边沿,也就是概念和观念的世界。中间的圆锥是想象圆锥,在智性圆锥的基础上产生,想象形成意象世界。智性是想象的推动力量,想象也可以被外在的感觉激活。想象圆锥的下边沿是清晰的意象,也就是想象的外在形式。最里面的圆锥是外部感觉的圆锥,通过想象而产生,这是不同于现实中的感觉的外部感觉,是一种从想象中产生的具有虚幻性的感觉,这种感觉在艺术中是常见的。外部感觉圆锥的下边沿是直觉性材料,它可以通过记忆与想象唤起,也就是外部感觉的外在表现。
三个圆锥体构成精神的层面,其中充盈着象征的生命的活力,智性仿佛领持着神的旨意,从灵魂深处推动着想象和直觉的世界建构。精神的前意识存在于智性圆锥之中,而本能无意识贯穿三个圆锥,包含了理性和感性的力量。灵魂通过智性的力量构建精神世界,同时,反过来,人具有一种本质性的生命力量——诗的力量,艺术的诗歌精神能够让人摆脱概念、规则、逻辑和规律,在想象的世界中展现自由丰饶的生命力量,所以,诗源于人的整体:感觉、想象、智性、爱欲、欲望、本能、活力和精神的融合。诗让人获得一种力量从物象、感觉和意象超越,飞向自由的灵魂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