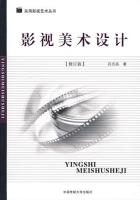安燕
一、创作与美学归纳
所谓“大后方”,时间概念专指1937-1945年的抗日战争时期,空间概念专指隶属于国统区与租界区、沦陷区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根据地相对应的区域,而集中于这一区域的大后方电影现象又主要发生在以重庆为中心、包括武汉、成都在内的地区。抗战时期大后方故事片创作从武汉至重庆时期,总计19部半(西北影业公司《老百姓万岁》未完成),其中武汉时期3部,重庆时期“中制”12部,“中电”3部,成都“西北”1部半。虽然在数量上不及纪录片,但无论在创作班子、经费投人、宣传向度、政策倾斜等方面,还是在创作实绩、艺术影响上故事片都处于大后方电影的主流地位,代表了抗战时期大后方电影乃至整个抗战电影的主流叙述与最高成就。从1938年1月到10月武汉沦陷前大约半年多的时间里,“中制”完成了《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忠魂》、《八百壮士》三部故事片;迁到重庆后,从1938年10月到1939年底的建厂过程中,拍了《保家乡》和《好丈夫》;1940年建厂完毕走上正轨后,先后完成了《东亚之光》、《胜利进行曲》、《火的洗礼》、《青年中国》、《塞上风云》、《日本间谍》的摄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从1941年到1942年未拍新片,抗战后期恢复拍片后,1944年又摄制了《气壮山河》、《血溅樱花》两部故事片;1945年摄制《还我故乡》、《警魂歌》两片。抗战八年,处于大后方的“中制”共计生产故事片15部。另外,“中制”设在香港的分公司“大地影业公司”也于战时完成《孤岛天堂》、《白云故乡》两部故事片的拍摄。“中电”武汉时期未有故事片创作,迁到重庆后,1939年4月,完成了第一部故事片《孤城喋血》,同年9月完成《中华儿女》,最后一部故事片《长空万里》1941年完成上映。“西北影业公司”在拍摄纪录片《华北是我们的》的同时,进行惟一一部故事片《风雪太行山》的摄制,另一部故事片《老百姓万岁》因公司停办没能最后完成。战时大后方故事片摄制因总体上受资金、器材、人力限制及炮火的干扰,创作数量不多,拍摄也十分艰难,多部影片摄制时间持续了几年。尽管如此,他们仍创造出了形态独特自成一体的故事片格局,使其在中国电影的历史中棱角分明。当然,在其独立自主中,我们依然不难窥见大后方故事片创作上承传统下启创新的内在生命律动,我们有理由对这些为转折开路的作品格外厚爱。正是从他们开始,中国电影历史整体地或者部分地改变了自己的进程。
大后方故事片创作在横向的宏观向度上,并未体现出整一性的类型,题材与内容的选取“已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写前线的英勇杀敌,固然是抗战电影;写后方的突击生产,何尝不是有力的抗战宣传?看起来似是平凡庸碌的市民生活,里巷琐闻,也未尝不可成为抗战的巨制”。在抗战主题统摄下的非整一性类别,在风格化的美学前提上,却呈现出一种整一性的可归纳性:纪实性故事片。以纪录手段和纪录风格大幅度进人故事片领域,纪实元与纪实化带来了纪实性故事片的形态分野。无论是纪实元还是纪实化的进人,大后方纪实性故事片在整体美学层面突破了单一文本内部不同影像风格的界线,在剧情推动与纪实风格之间实现了良性互动。尤其是纪实化风格的确立,改变了此前国民党官营电影与30年代民营“新兴电影”和“国防电影”局限于纪实元插人带来语段完整表意的段性自足形态,而进人到最小的语言单位镜头的纪实性叙事的元突破。在国民党官营电影的少量故事片以及“新兴电影”、“国防电影”一定数量的故事片创作中,出现了贴附于传统剧情叙事的插人式纪实语段,这种纪实语段作为一种带着明显提示性、功用性目的以调用形式存在的单位元,是外在于影像文体的,没有进人叙事结构,也未影响叙事方法和叙事风格。是作为一种硬性的表意投射而被填塞到文本的某一空间,更多表现出对下层社会的应答。由于电影在内驱力作用下的向前发展,由于战时大后方大部分故事片导演皆是战前民营电影业的中坚,也由于战时电影知识分子在革命的野性反抗中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皈依,整一性的纪实性表达成为大后方特定的历史与时代、物质与精神的必然。大后方故事片创作在纪实性策略上呈现出两种明显的倾向:一是纪实语段以贴附和插人的形式进人故事片,基本沿袭了30年代故事片创作纪实元调用的方法;二是经特定历史重捶之后,纪实元演变或深化为纪实化,纪实性的获得不再仅仅依赖于纪实语段的填充,而是在整体影像形态和镜语体系上呈现出非功用的进人叙事结构的纪实风格。作为美学风格的纪实化的实现,是纪实元在大后方故事片文本之间大面积扩散和在单个文本内部高度集中的结果,也是大后方纪录片创作横向参照、渗透与移人的结果。因此,纪实元是纪实化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美学前提和美学参照,而纪录片也成为故事片风格取向上的有力资源。正是在此意义上,显示了历史流程的延续与互动。
二、归因分析
大后方纪实性故事片的集中出现,单从形式内部变革而论,皆迥异于其前与其后的电影阶段。它应当是一个毫无疑义的转折期,更应当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发展期,其自成一体的电影格局具备了历史分期的可行性和必然性。惟其如此,我们更有必要深刻追究大后方纪实性故事片形态生成的根源,只有这样,才能对其内部进行合理解说。首先还是要回到中国的叙事本体论传统,中国传统美学善于从整体形态把握本体,讲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内在因果关联,叙事性成为中国文艺创作的基本生命。战争纪录片虽然有着某种潜在的叙事性,但其外显形态依然是对现实的如实再现,其感性意识流式的零散讲述和材料拼接与中国人的这种全息性叙事思维毕竟大有不同。加之叙事电影的主流正宗传统也在提醒着中国电影人的记忆,使他们难以轻易舍弃,于是叙事的潜在欲望成为中国电影人的内在追求,也使得纪实性故事片的出场具备了可行的心理动因。其次,抗战爆发后,战时大后方电影获得了从边缘甚至空白向中心移动的契机。在移动过程中,既无传统也无现实的大后方电影之惟一的出路是吸纳整个中国电影历史的和现实的养分,并因而发生变化,形成自己独立的品格。故事片向来是中国电影存身的命脉,而纪录片又活生生的近在眼前,历史的丰富积淀与现实的热烈需求转换成故事性与纪录性,这种状况几乎是本能地落人大后方电影人的视野,水到渠成地加之于大后方电影身上。然而,既然是“移位”,把大后方的这场电影革新看作是一个动态的结构,那就不能不充分考虑到移位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耗损”与“对话”。“耗损”与“对话”既意味着原初完整性的丧失,又意味着兼容并蓄的可能性。再次,当纪录片狂轰滥炸的生产倾向于一种惰性的饱和,处于那种饱和状态中的关系系统会努力寻求自我再生,便突然产生出使该系统脱离惰性的饱和状态的创新浪潮。纪实性故事片正是产生于饱和状态的纪录片中的创新浪潮。当然,创新不是割断与母体的联系,而是在对母体的依附中寻求新的生长的可能性。纪实性故事片的复杂性和悖反性在于:既是一种特殊的纪录形态,又是对纪录性的一种本质超越。在这种特殊的形态里,戏剧性与纪录性构成一种内在紧张。戏剧性在纪录性的强大挤压中似乎大大削弱了,然而同时又因其顽强生长的向度在纪录性的普泛参照中显示出了被突出和强化的奇异色彩。更开放地分析这一成因,除了传统叙事力量的惯性作用,与当时盛极一时的话剧创作也是分不开的。大量电影人向戏剧界的移人,电影与话剧创作的“两栖”身份,使得电影对话剧的借鉴具有了充分的条件。纪实性故事片中强大的戏剧性功能,能够在更为强大的纪实观念、纪实思维、纪实风格的潮流中作出某种抵制并最终得以有力存活,除了传统叙事观念的支撑,近在眼前耳濡目染具有强大戏剧性能量的话剧创作,使其伸手可及的可能性变得如此直接而现实。最后,抗战对现实主义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在对以往的现实主义作品肯定的同时,大后方电影人又提出发展全新的现实主义的主张。“我们看到了《春蚕》、《盐潮》、《渔光曲》这许多作品,崭新的内容完成了崭新的形式”,“真正为观众所喜爱的作品,却是循此路线发展下来的。伟大的抗战起来!新现实主义的要求更迫切,这原是中国电影更向前进、担负历史任务建立中国电影艺术的武器”,“在实现抗战建国辉煌的新文化这一伟大的理想的总的努力中间,电影工作者必须努力克服一切困难,造成又一个划时期的跃进,使内容形式和技术都要有新的研究,新的发明,新的改革。”“新现实主义”的自觉要求使得大后方电影创作迅速而迫切地走上发展和变革旧现实主义的道路,纪实性故事片是这种愿望和行动的强烈结果。在这里,现实主义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统领性的模糊范畴,而是具有了切实具体的物质内容和形式实体。
三、“缺失美学”:“共名”时代的派生物
抗日战争缔造了一个万众一心的“共名”时代,大后方电影创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无可逃避地成为这个“共名”时代的派生物。按照陈思和对文学“共名”现象的理解,所谓“共名”,即是“当时代含有重大而统一的主题时,知识分子思考问题和探索问题的材料都来自时代的主题,个人的独立性被掩盖在时代主题之下。我们不妨把这样的状态称作共名,在这样的状态下的文化工作和文学创作都成了共名的派生。”大后方纪实性故事片创作虽然具体内容不一,对战争生活的选取各有侧重,艺术处理方式也各有不同,但所有创作都统摄在战争现实这一宏观题材背景和战争文化这一“共名”状态之下,却是不争的事实。大后方电影的“共名”特征在于将电影当成某种可以为抗日战争这一特定的现实政治起作用的有力的东西,因而可以将之直接组织起来,使其成为抗战的一部分。在大后方地区,激进的知识分子为了抗战达成了与政府的和解,大量电影人拥人国民党官营电影业,这样的现实决定了“共名”状态下的电影生产既依赖于对现实权力的依附,又诚恳地出自大后方电影人的一种主动和自觉的选择。任何“共名”状态下的文艺生产都只能是时代文化的产物,大后方电影生产的官营性质,使得它比别的个体创作显现了更加鲜明的“共名”特性。应合时代的“共名”与艺术创造的深致求工之间的裂隙似乎永难弥合,“我们如今站在一个漩涡里。时代和政治不容我们具有艺术家的公平(不是人的公平)。我们处在一个神人共怒的时代,情感比理智旺,热比冷要容易。我们正义的感觉加强我们的情感,却没有增进一个艺术家所需要的平静的心境”。“在我们这样一个狂风暴雨的时代,艺术的完美和心理的深致就难以存身。传统和生活不会一下子合好无间。”“共名”状态下的大后方电影无论纪录片还是纪实性故事片无疑都是这样一种“缺失美学”的代表。按照亨利·塞尔对“缺失美学”与“在场美学”的区分,在场美学力图超越历史,逃避时间性;缺失美学则使艺术面对历史的诡计,接受时间,也接受历史制造的来不及过滤的粗糙和平凡对艺术的伤害。在这些电影作品里,有的是壮烈的场景、丰沛的激情、鲜活的生命、伟大的爱与忠诚,缺乏的却是艺术修辞的内在清醒。然而,对于它们在电影历史长河中的单纯和孤立,我们却无从责难,他们贴近时代而生的真诚和朴拙使他们获得了另一种美:力的美。在这里,我愿意转引刘纳在《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一书中对辛亥诗歌的评价来对大后方纪实性故事片创作的美学风格略作概述。我认为这一描述对于大后方故事片创作整体面貌的把握同样异常准确:“适应着新的社会审美需求,为传达亢奋的时代狂热,辛亥革命时期激进诗歌表现出了那时代特有的力度和亮色,那时代崇尚粗犷恣肆、咄咄逼人的风格,许多优秀作品的气魄、气概、气势都以‘粗’、‘直’为特色。大气磅礴的粗豪之中既包涵着不可摹拟的风采,又暴露着艺术情感的粗糙、艺术形态的粗砺和艺术构思的粗率。外在的气势压倒了内在的气韵,外在的强度超过了内在的深度,以传统的艺术眼光去打量,自然是难人眼的,……然而,辛亥革命时期激进诗人们做出的审美选择是狭窄的、有很大欠缺的,却又是不同凡响的,它体现了一种单色的美:力的美。”
相对于大后方电影所欲表现的“共名”于战争的内容和所欲展示的这样一种单色的力的美,周围地区的既有的电影词汇和修辞不是已经硬化就是因为陈旧而失去了活力。当传统电影语言形成的叙事和抒情与战争中人们的某一部分真实遭遇发生抵触和分裂的时候,一种应合于时代“共名”的新的电影语言和电影形式必将应运而生。抗日战争的残酷现实和大后方特殊的政治环境,决定了战时大后方故事片创作由一个尚可倾诉自我的抒情时代走向一个评点世界的叙事时代。结构主义代表人物托多罗夫提出,一个社会总是选择符合意识形态的行为并且使之系统化,“史诗在一个时代成为可能,小说则出现于另一个时代,小说的个体主人公又与史诗的集体主人公形成对照,这一切决非偶然,因为这些选择的每一种都取决于选择时所处的意识形态环境。”卢卡奇也认为艺术作品的形式本身是我们观察和思考社会条件和社会形势的一个场合。战时大后方生产的这些“金刚怒目”式的故事片作品以美学风格的纪实化形态呈现出来,印证了历史事件缔造的意识形态对艺术创作在技术上的必然性。詹明信所谓“形式的意识形态”正是这种技术必然性的成果,它一再表明,电影与身边历史的深刻对话恰恰要而且不能不诉诸深刻的电影形式,大后方故事片创作的纪实形态是这场对话的重大结果。战争同时带来了对集体性、对集体行动的张扬,也带来了固有的激进的民间性的苏醒。大后方声势浩大的大众化、通俗化、民族形式大讨论及其巡回放映形式的普及,无不表达了试图回到民间、发动大众的努力。来自民间的集体行为的重要表征是狂欢化,狂欢化显示了从种种压抑中获得解放和自由。狂欢化是抗战时代“共名”状态的精神派生物,也是其返回民族记忆的心灵依傍。“狂欢化具有构筑体裁的作用,亦不仅决定着作品的内容,还决定着作品的体裁基础。”战时大后方故事片创作纪实形态的生成几乎是民间狂欢化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精神投影,也是调动民间力量完成集体性狂欢的物质武器。
大后方早期的故事片甚至带有较为明显的政论色彩,以战争事件或战争新闻为支点,在整体纪实背景下用戏剧化手段进行表现,如《保卫我们的土地》、《八百壮士》、《胜利进行曲》等。纪实性故事片充分发挥了电影媒介融合的优势,将许多不相干甚至互相抵触的内容和表现手法揉在一起,新闻评论、新闻报道、纪录片、表演、作者阐述、纪实性手法、戏剧化情节结构等等一切与观念革命有关的信息,向观众喷射,形成一股强大的意识流,用以冲击观众。不安于传统,而要人侵到别的领域,这种侵人式的进取性格,是战争文化的产物。纪实性故事片是真实与虚构的混合,既是纪实,又是戏剧。它与纪录片有着本质的不同:纪录片是直接展现正在发生的真实事件,环境和事件不允许搬演;纪实性故事片则通常是通过演员表演,展现真实发生过的事件,环境和事件可以依照导演意图摆布和重演,其创作与拍摄都是一种再创造过程。在表现形式上,强调对生活流程的自然再现,镜语表达、画面构图平易朴素,符合现实生活的一般逻辑,强调实景拍摄、跟踪拍摄,采用自然光效,以突出真实感。纪实性故事片允许对人物和事件进行虚构,但将其放在一个纪实性的背景上,使其染上强烈的纪实色彩,为整个剧情创造一种现场性极强的实况展播效果。大后方纪实性故事片通常没有常规戏剧式电影那样贯穿一体的动作和强烈的冲突悬念,没有通常意义上的高潮,而是多用细节和片段经营的开放性结构。因其情节的零散性和片段性,纪实色彩也就越加分明。大后方纪实性故事片通过风格冗余或拔高的形式,从内部破坏了传统叙事的权威,纪实风格上的超负荷反而使得另一种相悖的具有明显戏剧性特征的因素心理写实获得了生长的可能性空间。心理写实使得真实被超真实化了,超真实对真实的废除不是通过猛烈的破坏,而是通过假定、敛聚和吸收,通过上升到模式的力量来实现,模式起到了一种吸收真实的空间的作用。通过宏观的高度真实,通过纪录式资料的加速循环,通过纪实风格的饱和,通过取消真实与其表征之间的距离,通过真实能量流动的内向爆炸,通过这些形成了模式的力量:超真实终止了真实肆意蔓延的流程,它通过将其提升为模式的方式终止了作为叙述过程的现象的真实,而同时获得了内在的人的真实。超真实将想像从历史那里解放出来,使艺术的意志内转,使电影语言面对其自身。在大后方纪实性故事片里,真实与超真实的对应转换成纪实性与戏剧性的对应,构成了大后方纪实形态的故事片的内在紧张,也成为其剧情推动和意识形态宣喻的重要力量。《火的洗礼》、《好丈夫》、《日本间谍》、《血溅樱花》尤其《东亚之光》等都是在纪实与故事的异常紧张之中再三徘徊的作品。战时以宣传意图为主旨的大后方纪实性故事片,已经开始背离我国传统叙事电影的美学原则。它不再依赖强大而自足的故事能量,不再依赖流畅而完整的讲述,而是在叙述视角和叙述结构上以纪实风格的过剩漫布,通过故意放慢情节,通过叙事的片段化和零散化,通过对线性情节发展的松散化处理,通过扩大叙述的伸缩性,通过插人语段带来的叙事阻隔,呈现出一种脱离旧有电影叙述原则的松动。有别于传统环环相扣陈陈相因的线性叙事逻辑,大后方纪实性故事片这种较为散碎的讲述方式,与抗日战争时代大后方电影人“知觉革命”的情感态度有关。作为愤怒电影人的一次集体行动,他们不愿将自己的情感隐蔽于故事和人物身后,而是以感性意识流的方式迫切地赋予作品直接的宣泄功能。感性革命必然带来对逻辑和稳定性的破坏,一切与此时此刻的感性遭遇背离或抵触的传统电影语言,只能在被改造中获得继续生存的权利。
抗战时期的大后方电影作为艺术现象,早已被轻易地超越了。但是,它们的精神感召力、情感吸引力却是无可替代的。当我在一遍一遍的阅读过程中,在惊奇那些单薄、粗陋、素朴的作品竟能保有如此长久的生命的同时,又分明真切地体验到它们焕发着的强烈的精神力量。它们是那样值得珍惜和敬慕,值得珍惜和敬慕的不是那些粗朴的影像本身,而是影像后面激情四溢的性灵、真纯热切的情绪。在此之前,不会有这样似乎是随便的、即兴的、容易拍出的真而纯的影像;在此之后,效仿这种纯洁和真挚,只能沦人一种矫情。粗朴、纯粹、真挚动人的气质是时代留给它们的缺憾,也是时代赐予它们的恩惠。那些参差的黑白影像留下的真纯热切的画卷,永远是中国电影史弥足珍贵的财富,并因此而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