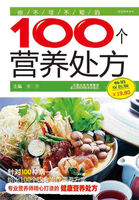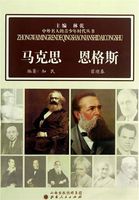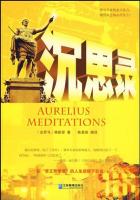现在不用他说我也知道一些事情的谜底了。无端地遭到别人的嫌弃、厌恶,冤不冤呀。我真想战斗,可这战斗怎么打呀。
我决定采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即用脑子去这样地想:在见义勇为者为和歹徒搏斗而倒在血泊之中时,尚有人袖手旁观,无动于衷,见死不救,你现在是这样的一个危险人物,人家能不逃避吗。如果真的是人人动手在向他人向弱者向不幸者捐献热情、爱护、帮助和支持,女歌手韦唯还唱“只要人人都献出一份爱”的歌吗?!她即便唱了还竟会有那么多的人听并被打动吗?!发生了的,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发生。许多的事情只有在亲身经历了之后,才能感受得真,体会得深,理解得实。把自己的那份苦痛、忧愁咽到肚子里去,沤掉它,烂掉它,直到完全消解为止,别指望所有的人都像你自己一样,把你自己的事当做一回事。不然的话,我们还有多少事可干呢。
为了给新老癌民“减负”,弄清癌症究竟是不是一种传染性的疾病,我在动手写这本书前,并不满足我以往的认知,找了许多医者和他们写的书,得到的回答是一致的:“癌症不会传染”。有一位医学专家指出:癌症不是传染病,它不能把致癌基因通过任何途径进入他人体内。事实上,将癌症病人的癌细胞或癌组织移植到一个健康人体内,经过多次试验,均未发现这些健康人长出类似的癌来,而是机体的防御系统以惯用的“排外”天性将癌细胞吞噬掉,此即排异反应。有人做动物实验,把健康动物与患癌症的动物关在一起长期观察,健康动物并未传染上癌症;把动物癌细胞的滤液接种到健康动物身上,也未使健康动物长成肿瘤。医院或疗养院不同病种的癌症病人和其他病人混住在一个病房,也从未见到相互传染的情况。从事癌症治疗的医护人员,长年与癌症病人接触,甚至有的医生对癌症病人做手术时手指不慎刺伤,被癌性液体污染,也未曾传染上癌症。
医书上说,夫妻双双患癌、一个家庭中有一人以上者患癌,都不能得出癌症会传染的结论,这是因为:第一,一个家庭的成员有着相同的致癌因素,从而使家庭成员中有一人以上者患癌。第二,家庭中有一人先患癌后,另一成员或更多的成员情绪受到重大打击,不能镇静、乐观对待,生活规律、饮食等受到重大影响,免疫功能大大减弱,加之相同的致癌因素,使自己也跟着生起了恶性肿瘤。第三,与遗传有关。癌症确有家族遗传倾向,但必须指出的是,癌症不存在确定的遗传性。
不是遗传性疾病,一个家族中癌肿瘤发生的相对聚积性并非遗传所致,遗传只是与癌症有一定的联系,还得加上其他的致癌因素才能导致癌症的发生。这也说明,癌症与传染是不沾边的。
医书上又写道,因病毒能引起癌症就推演出癌症是传染的,也是乱点鸳鸯谱。其理由是:有些癌症如胃癌、肝癌、子宫癌等均与病毒或细菌有关。问题的关键是,这些病毒可以传染,但因此导致的癌症并不能传染。如乙肝病毒可引起乙型肝炎,如久治不愈可成为慢性肝炎,再久治不愈就会发展成肝硬化,在各种致癌因素的作用下诱发肝癌。乙型肝炎急性期如积极治疗而痊愈就不会诱发肝癌。由此可见,某些病毒或细菌并不是引起癌症的直接原因。
医药界的行家指出:无论是在医院里,还是在家中,对癌症病人都不必采取隔离措施。病人的亲戚朋友前来探视或陪伴也不必考虑传染的问题。对癌症病人采取的疏远和歧视的做法,会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压力,使他们感到孤独、失落、活得毫无意义等。这对他们无疑是雪上加霜。
视癌症病人为瘟神,惟恐躲避不及的人,还会继续存在下去的。这就是中国的国情。我们不妨看看艾滋病人的遭遇就更觉得我说的话是站得住脚的。有位专治艾滋病的医生说,有人向她咨询,自己可不可以同艾滋病人拥抱、握手、接吻,她回答他说可以。可当另有人向另外一位专治艾滋病的医生提出自己可不可以和艾滋病病人拥抱、握手、接吻时,这位医生回答是不可以。有位艾滋病人看护者居然对采访一位艾滋病人的电视台的女记者说,你怎么还不尽快离开他呀,要知道,你是在和1米多高(病人1米多高)的厚厚一层的艾滋病病菌接触呀,有多危险呀。我曾在电视屏幕上看到这样的画面,一个患艾滋病的青年男子拿烟给人家抽,人家不敢抽,到小卖店去买东西,店主不愿卖,用冷漠驱赶他赶快离开。我真敬佩那男子,他居然有勇气活下去。艾滋病只是通过血液、性、母婴三种途径传染,并非只要与艾滋病人一接触就会被传染。可是,有些人就是觉得自己的命特别值钱,生怕沾艾滋病人的边,力求离他们远些远些再远些,连拉屎都要与他们隔三个蹲坑才好。
是笑何忌强颜
我的中晚期胃癌不仅使我过早地结束了我的办公生涯,还使我失去了已经享受了的并应继续享受下去的一份人生欢乐和趣味。这是我所始料不及的。
我们一帮子在北京工作的中学同学经常聚会。每次聚会时,同学们都愿意我能参加,因为我爱说笑,能给聚会增添情趣和欢愉。我是聚会的高级“味精”。我呢,只要有可能,绝不缺席。办公室的生活是紧张、严肃、辛苦的,同学们聚会,是个纵情、放松、调节生活的好场所,何乐而不到呢。我也不负重望,每次都能逗得他们前仰后合几回。
我出院后不久,在北京工作的中学同学们又举行了几次聚会,并要我也参加。我虽然精力和体力很困难,还是一回也不落地参加了。不仅如此,我一如既往,竭力扮演活跃分子的角色。但是,我发觉,我新的笑话质量并不以前的次,一个个却像过期失效了的产品一样,引不起“顾客”的兴趣,反应极端冷淡。我惶然了,茫然了。
原先的聚会,热烈、愉快、尽情,而后来的却总是有些儿阴沉、灰暗,似乎有个什么无形的东西在起着作用。莫非与我有关,我得探个虚实,别把这傻瓜的角儿一直演下去。又一次聚会上,我讲了两个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故事是很精采的,若被马季、姜昆、冯巩等人拿了去,稍微加加工就可成为令观众捧腹的段子。我在讲的时候不时做动作,使眼神,卖尽力气,以达哗众取宠的目的。可是听众们个个像是木头人,没有反响,不作配合,不捧场。也有笑了的,却笑得稀罕:不动眉宇,不露牙齿,只挤弄两个嘴巴子上的肉,因而找不到笑容,真不如哭好看。这下我明白了,我已不是生活的高级“味精”了,我已改当“笑容抑制剂”了。只要有我在场,不管哪一次聚会,就不会有开怀的笑,就不会出呛人的欢乐的氛围。我的欢乐权讨不回来了。
我这人还挺小气,决定讨回欢乐权。干嘛不呢,那些属于我的呀!欢乐权,大小是个权益呀,理应不受侵犯呀!在一次在北京工作的中学同学的春节聚会上,人家举杯祝贺“节日快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我举杯严正声明:“自即日起,凡我所说所作,有笑或有乐价值的,诸位要笑得正常些,乐得正常些,不要不伦不类损坏人体细胞组织。小常宝要讨回她的女儿装,我要讨回我的欢乐权。提请在座的同学要注意到,现在已不像‘文化大革命’年代,秃子打伞——无法无天,而是强调建设民主的法制国家,一切依法从事,你们拿我的话当耳旁风,我就告上法庭,要求赔偿因你们的行为而造成我的精神损失。索赔金额恕不现在奉告,反正我的脾性你们是了如指掌的,我这人一生和钱最相好,所以索赔金额不会小,难免是个天文数字。要是不心疼钞票的话,你们就继续为非作歹下去好了。还请诸位打掉傲气,别老以为我已风雨飘摇,朝不保夕,我们中究竟谁是八宝山中那种‘小单元房’的第一位搬迁户,还得骑着毛驴看唱本——走着瞧。得癌症我已带一回头了,这回我反正不打算再带这个头,看谁敢强制执行。哈哈,春节献词,当否,请多多批评指正。谢谢!”
时隔不久,我的参加春节聚会的一位中学男同学也患了胃癌,并很快故去,成了八宝山中那种‘小单元房’的第一位搬迁户。他的妻子对别人说,她丈夫的死,完全是由我在春节聚会上讲的不吉利话造成的。她对我很是气愤。我未讨得欢乐权,反而惹下了祸,落得人家的怪罪。真是人一旦倒霉,喝凉水都能涩牙。
我住在北京的中学同学搞聚会,我回老家后,我住在和县城里的中学同学也搞聚会,他们用小汽车把我拉进县城里,今天在这位同学家聚,明天在那位同学家聚,一天不断地往下轮,打算将几十个同学都轮一遍。聚会的内容大同小异,先是大家对我说些安慰、同情、关爱的话,接着是鱼虾肉鳖的大餐和餐后的合影。我已认定这里同学们的心迹和在北京的中学同学们的心迹毫无二致,所作的一切均是为了和我作最后的告别。我的心理还未坚强到能够长时间地看人家在对我进行“准”遗体告别仪式,不得不中途逃出县城外,回了我乡村的家。
渐渐地我对聚会的兴趣越来越淡漠,有时甚至编织谎言,制造借口,一推了之。即便硬着头皮去了,也任他们关切我,怜悯我,向我献爱心,获取我现在这种情况下理应获取的。我不服也得服地充当被欢乐遗忘了的人。
我并非癌民中的怪人。我读过一位癌症病人写的书,书中提到,他也不喜欢亲友们以及周围的人们在向他表示安慰、关切时透着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情。他认为,他们的行为向他表明,他们对他的生存没有信心。书中便有了这样的文字:“如果一个癌症患者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周围的人们对他是这样一种恐惧心态,那他会是怎样一种心情和感受呢?只能是不愉快。其结果,只能更加重他的悲观情绪,使他丧失生活的勇气和信心。”许多的医书也提醒着癌症患者的家属、单位的领导、朋友、同学、老乡及熟人们,在和癌症患者接触时不能表露出惋惜、可怜的言行,要多谈一些愉快的事情,多谈病愈后美好的将来。要多从正面鼓励病人战胜疾病,表露出自己真诚地热切地希望对方早日康复,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共同为社会做贡献的情绪。要努力以情以理转变对方对癌症的消极信念。
时至今日,也还有人从言语和神情中流露出对我的生命前景的关注和担忧。每当此时我就怦怦地心跳,血压似乎在升高。但这样的现象我是越来越少碰到了,毕竟病后我已活了够办4次奥运会的时间了。
身“下岗”心“在岗”“坐家”到底不是“出家”,“出家”往深山古庙里一呆。“出家”不认家,就自己一个人,想的少,遇到的也少,定是十分的美好。我仔细地一琢磨,未必是这样。“出家”当尼姑,就要和大小老少的尼姑们处关系。“出家”当和尚就需要和大小老少的和尚们处关系。无论当尼姑也好,还是当和尚也好,都要面对吃饭、饮水、穿衣、看病等基本的生计问题,这其间就会生出矛盾、麻烦和苦恼来,也可以说活得就并不那么轻松。我就在南京中央门长途汽车站亲眼见到尼姑活得不遂心的一幕。两个年轻的尼姑手持写明座位号码的长途公共汽车票,好不容易地挤上了车,两个抢占了她俩座位的大男人就是耍赖不让座。她俩一点辙也没有,只能被迫地接受了享受站票待遇的现实。我想,此时此刻,她俩肯定是一肚子火的。但是,出家人毕竟是出家人,社会关系相对比不出家的人要简单些,牵的挂的少些,缠的绕的少些,罗嗦自然也少,心比不出家的人要清静得许多。要不然,古往今来,怎么会有那么多失意、受挫折的人争着往尼姑庵、和尚庙里跑,削发为尼为僧呢。
我现在当的是“坐家”,情况和“出家”的就发生了差异。
我觉得我有强过“出家”人的一面:尼姑与和尚们看病尤其是看大病一定有问题,我与解放军总医院相隔咫尺,有什么疼痒,几步路就能到,且吃药打针免费;尼姑与和尚们吃水通常要爬高跨低地到山下去挑,我家有自来水管子,要用水,只需用手轻轻拧一下水龙头,即可敞开地去取;尼姑与和尚们形只影单,六亲不认,我有一双儿女,妻子在我病后第14年才跟我离婚,我总的讲不乏天伦之乐。我爱我的家,爱我的后勤学院那个4层楼上拥有2间住房的家,也爱现在干休所5层楼上4室1厅的家。除了早晨或晚上要锻炼身体,进行娱乐活动,去食堂打饭,去院内商店或小摊上买穿的用的以外,我很少离开家,有时几天都不下楼。我不愿到大街上去,不愿到亲友家去,更不愿爬山涉水地到京外去。我成年累月地偎在我的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