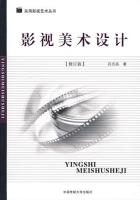中国古代早期长篇小说在明代嘉靖至万历间(1522-1620)陆续成书问世。多种小说的最早版本排列如下:
《三国志通俗演义》,嘉靖元年(1522)
《水浒传》,天都外臣即汪道昆序本,万历十七年(1589)
《西游记》世德堂百回本,万历二十六年(1598)
《金瓶梅词话》,万历四十五年(1617)
《隋唐两朝史传》(《隋唐志传》)龚绍山绣梓本,万历四十七年(1619)
外加刊于万历年间的《三遂平妖传》和《封神演义》共八部。后两者具体年代不详。
《三国志通俗演义》作于弘治七年甲寅(1494)的庸愚子即金华蒋大器序云:“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这当是指罗贯中草创之后的最近一次改编,下距嘉靖本刊行只相差二十八年,其他七种书找不出最后成书前较近的一种版本的记载。从它们最后成书到以前较近的一种版本相隔都很久,自数十年以至数百年不等。如《列国志传》今存万历三十四年(1606)三台馆重刊本,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残本有元至正十七年(1357)伯颜序;现存《西游记》世德堂百回本刊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而嘉靖二十年王寅(1542)杨悌为他哥哥杨慎《洞天玄记》杂剧所写的《前序》已经提到《西游记》书名以及同今本一致的一些具体情节,可见世德堂本之前《西游记》成书至少已有半个世纪之久;又如今存《金瓶梅词话》以万历四十五年(1617)为最早,而汤显祖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完成的《南柯记》传奇最后一出袭用了《金瓶梅》最后一回的相似情节,可见汤氏此时已读完这部小说。麻城刘家藏有此书。汤氏曾在万历八年(1580)前往做客,为他家甄选金元杂剧两三百种。如果汤氏阅读《金瓶梅》也在此行,则《金瓶梅》从成书到出版至少相隔三十七年以上。
上述几部小说都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它们从各自最早的传说开始,经过长期的不同的改编写定者之手,在此期内陆续成书。现在所见可信的中国长篇小说的个人创作以吕天成(1580-1618)的《绣榻野史》为最早。它成书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前后。本文以它作为中国早期长篇小说的下限,后期即个人创作的长篇小说的上限。此后依然有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长篇小说继续成书间世,但个人创作已经出现,并正在逐渐加强它的势头。本文卷首所列几部长篇小说今存最早版本半数也在此下限之后,但成书则显然较早,所以仍在论述之列。
据龙膺《重刊沦錣文集》卷二四《答吕麟趾(允(胤)昌)太仆》,署名吕天成的杂剧《神女》、《戒珠》、《金合》是他父亲吕允昌的作品。《绣榻野史》的情况可能与此相似。否则,很难想象一个“少年”会写出刻意模拟《金瓶梅》的淫秽色情篇章的“游戏之笔”(引号内词句见王骥德《曲律》卷四《杂论》第三十九下)。在此之前,个人创作的长篇小说在中国并不存在。
本文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早期长篇小说发展史的基本事实之一,它是小说史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
《三国演义》、《水浒传》作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经胡适、鲁迅、郑振铎的研究已成定论,尽管对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还没有一致的认识。
吴承恩(约1506-1582)创作《西游记》说创自胡适的《西游记考证》,但它的论据却经不起认真的查证。详见章培恒教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见长春《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不仅如此,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记杂剧》、《永乐大典》所载的《梦斩泾河龙》片段以及世德堂百回本清晰地显示了《西游记》成书的各个阶段。
《金瓶梅》作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潘开沛《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1954年8月29日北京《光明日报》)创之于前,随即受到徐梦湘的批评,见同一报纸次年4月17日。由于没有答辩,个人创作说似乎已占优势。
本文作者以长篇论文《金瓶梅成书新探》(上海《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3期)重申《金瓶梅》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详尽的论证难以在这里重复。后来鉴于《金瓶梅》除惨淡经营的成功描写外,同时并存着行文上到处可见的疏失。如卧云亭下玩花楼边,潘金莲撇下月娘等人独自在假山旁扑蝶为戏,她和陈经济调情以及陈经济上前亲嘴被潘金莲推倒的情节,第十九回和第五十二回居然有大段相同;又如最后一回西门庆已经转世为自己的遗腹子孝哥儿,而同一回却又说西门庆托生为东京富户沈通的儿子:鉴于这些以及不胜列举的许多破绽,因此将原来结论李开先(1501一1568)是《金瓶梅》的写定者改为他或他的崇信者。并作如下解释:如果改编写定者是李开先的崇信者,他的文化修养不会很高,算不上《野获编》所说的“大名士”;如果是李开先本人,那他并未自始至终进行认真的校订。写定者无论对此书的成就和缺陷都不起什么作用。这样我算是纠正了自己过去对写定者的作用估计过高的失误。
《金瓶梅》的色情描写如第七十九回西门庆死于淫欲:“初时还是精液,往后尽是血水出来,再无个收救……尽继之以血,血尽出其冷气而已。”1949年以后,国内(大陆)批评界习惯于将《金瓶梅》的色情描写视为自然主义加以贬斥,我以前的一些论文也不例外。其实它同19世纪法国自然主义强调遗传和环境对人决定性作用的主张背道而驰。这些描写来自辗转相传、以讹传讹或层层加码、愈演愈烈的口头传说。它追求的不是细节描写的真实性,而是耸人听闻的轰动效应。它不可能出于文人笔下。
以上所举几部长篇小说都曾经历或长或短以数百年计的竞相流传的时期,它们难免彼此影响,互相渗透。彼此渗透、互相影响的事实反过来又证明它们不是个人创作。在个人创作中只有施加影响或接受影响的单向作用,不可能是双向作用。本文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早期长篇小说发展史的又一基本事实,不宜对此视而不见。
小说名着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彼此影响、互相渗透,可以确定为双向作用的事实举证如下:
一、《水浒》和《金瓶梅》
《水浒》第五十七回引首诗:
人生切莫恃(将)英雄,术业精粗自不同。
猛虎尚然逢恶兽,毒蛇犹自怕蜈蚣。
七擒孟获奇(恃)诸葛,两困云长羡吕蒙。
珍重宋江真智士,呼延顷刻入囊中。
本回内容是徐宁的钩镰枪大破呼延灼的连环马,迫使他归顺梁山。
引首诗配合得十分贴切。《金瓶梅》第一百回引用此诗前六句只有两个字有出入(见括弧内,下文同),而尾联改为:“珍重李安真智士,高飞逃出是非门。”第三至第六句的比喻完全落空,成为无的放矢。显然,这是《金瓶梅》因袭《水浒》而露出马脚。
《金瓶梅》第九十八回引首:
心安茅屋稳,性定菜根香。
世味怜(薄)方好,人情淡最长。
因人成事业,避难遇豪强。
今日峥嵘贵,他年身必殃。
因人成事指陈经济遇见春梅,得以在守备府用事,豪强指下一回的刘二。第二年刘二的姐夫杀死陈经济。本回陈经济才从收容他的道士那里离开不久,前四句暗合他的这一番遭遇。《水浒》第三十八回引用此诗,末联作“他日梁山泊,高名四海扬”。豪强指宋江在江州牢城营结识的戴宗和李逵。但前四句在这里无所指。“因人成事业”用来指宋江,未免降低他的身份。可见《金瓶梅》此诗是原作,而《水浒》则是生搬硬套。
二、《西游记》和《封神演义》
《西游记》第一回赞词“千峰排戟”,结尾说:“必有高人隐姓名”,写的是灵台方寸山,须菩提祖师的住处;《封神演义》第三十八回却用这首赞词形容“狰狞凶恶”的妖怪龙须虎的洞府,显然不合。
与此相反,《封神演义》第五十五回的赞词:“山顶嵯峨摩斗柄”的结尾:“不是凡尘行乐地,赛过蓬莱第一峰”,写的是天帝亲女的洞府夹龙山,《西游记》第二十六回同一赞词的结句则是:“应非佛祖修行处,尽是飞禽走兽场”,而后文明明是勅赐宝林寺,前后不相照应,当是蹈袭而发生的失误。
三、《水浒》和《平妖传》
《水浒》第五十六回赞词:凤落荒坡,尽脱浑身羽翼;龙居浅水,失却颔下明珠。蜀王春恨啼红,宋玉悲秋怨绿。吕虔亡所佩之刀,雷焕失丰城之剑。好似蛟龙缺云雨,犹如舟楫少波涛。
描写徐宁雁翎甲被盗,以羽翼、明珠、红(花)、绿(叶)、刀、剑、云雨、波涛比喻失物,十分贴切。《平妖传》二十回本第十九回用来描写主将文彦博败阵可说牛头不对马嘴,显然由于《平妖传》盲目蹈袭《水浒》而致误。
与此相反,《平妖传》二十回本第二十回有一首七绝:神器从来不可干,僭王称帝讵能安?潞公当日擒王则,留与妖邪作样看。
《水浒》第九十三回引用此诗,将后二句改为:武松立马诛方貌,留与奸臣做样看。
方貌是农民起义者方腊的三弟,无论如何不在朝臣之列,不管是忠或奸。这个不伦不类的比拟说明《水浒》袭用《平妖传》的原作而出现差错。
四、《水浒》和《西游记》
《水浒》第五十回的引首:乾坤宏大,日月照鉴分明;宇宙宽洪,天地不容奸党。使心用幸,果报只在今生;积善存仁,获福休言后世。千般巧计,不如本分为人;万种强为,争奈随缘俭用。心慈行孝,何须努力看经;意恶损人,空读如来一藏。
它和《西游记》第十一回的相应诗句只有个别文字出入,正好用以互校。《水浒》的引首把它作为格言,和后文没有任何联系。《西游记》则将它列入唐太宗御制榜文之内,是不可分割的组成之一。有可能《西游记》是原作,《水浒》则是套用。
《水浒》第三十一回的赞词“高山峻岭”和第三十二回的赞词“八面嵯峨”被合成一处,见于《西游记》第三十六回。《水浒》成书可能比《西游记》早,但它第三十一回的赞词不太符合正文所说的月下景象。“幽鸟闲啼”,樵夫在山,很难说是晚上,显然不是原作。
《水浒》第二十七回东平府尹陈文昭的赞词,《平妖传》第二十九回开封府包待制的赞词,《金瓶梅》第十回东平府尹陈文昭的赞词,《西游记》第九十七回铜台府刺史姜坤三的赞词,四者大同小异是流传过程中交相作用的明证。有人将它作为考证《金瓶梅》作者的依据,可能没有想到它被四部小说所同时引用吧。
上述四部小说赞词雷同无独有偶,同时见于《平妖传》四十回本第十六回的赞词“十字街渐收人影”,《西游记》第八十四回的赞词“十字街灯光灿烂”,《水浒》第三十一回的赞词“十字街荧煌灯火”,《金瓶梅》第一百回的赞词“十字街荧煌灯火”。四者都嵌入十、九、八、七……颠倒的序数。如果不是彼此影响,互相渗透,那就难以理解。
上面所说的古代早期各长篇小说名着在流传即形成过程中双向的蹈袭只以赞诗或引首词为例,因为它们文字简短,一望而知。实际上它们之间的彼此影响远不止此。它们可以在题材相近的作品如《西游记》和《封神演义》之间,或《水浒》和《平妖传》之间发生,但也可以在题材迥异的作品之间发生。试举例如下。
《水浒》第五回鲁智深躲入民女帐中,把满心想做新郎的山大王打得狼狈而逃,正同《西游记》第十八回《高老庄大圣降魔》手法雷同。
《金瓶梅》第一百回西门家的丫环小玉在永福寺门缝中窥见普静禅师作法超荐亡灵,有的亡灵提头带血在“阴风凄凄,冷气飕飕”中出现。《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一六《玉泉山关公显圣》普净禅师收服关公的阴魂。联辉堂刻本卷一三有云:关公阴魂“大呼还我头来”,可见关公阴魂原本无头。小说所引《传灯录》明明说玉泉山六祖神秀“拆毁其祠,忽然阴云四合,见关公提刀跃马于云雾之中,往来驰骤。”小说却接受《金瓶梅》的影响将神秀换上普净。
《平妖传》、《水浒》、《封神演义》都写到天罡地煞。《封神演义》黄飞虎过五关显然受到《三国志通俗演义》关羽故事的影响。《封神演义》结尾的封神榜和《水浒》第七十一回的《忠义堂石碣受天文》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