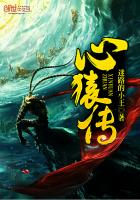中国古典文学主要在封建制度下形成,世界上很少有别的民族的封建制度延续得像中国那样持久,封建文化像中国那样辉煌,正如欧洲文学着称于世的却主要是它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共产党宣言》曾这样指出两个社会的不同:“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找不出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同时还指出封建社会中存在的是“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家庭关系上笼罩着的是“温情脉脉的面纱”,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纯粹的金钱关系”。中国同欧洲的文学传统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上述社会制度的不同而产生的。但是一经形成之后,就有相对的独立性,会对后代的文学发生深远的影响。
封建时期的文学从好的方面来看,的确如歌德所指,比较注意思想内容,但是它容易流于封建说教或单纯的抗议,往往对艺术性重视不足。在不少的中国古典小说戏曲中可以看到这个缺点。
中国的先秦诸子曾在思想领域放出了异彩,但却没有产生完整的文艺理论。孔子在《论语》中对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作了评论,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又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些话对后世的文学批评和创作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它们着重文学的思想意义及社会作用,但很少涉及艺术性。大约同孟子同时,古希腊出现了亚里士多德的美学着作《诗学》,下面是它的第六章为悲剧所下的定义:“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模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感情得到陶冶。”尽管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纯艺术”论的反对者,但在这一个定义以及《诗学》全书中偏重的却仍然是艺术性。以上说的不是对孔子或者亚里士多德的评价,我只是如实地指出他们各自的特点。这些特点对中国与欧洲的文学传统的形成是发生过一定的作用的,它们直接间接对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特点的形成也不是没有关系的。
如果探索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创作同他们当时社会思潮的关系,我们将发现莎士比亚的条件显然比汤显祖有利。莎士比亚的戏剧是文艺复兴的产物,它是作为中世纪的宗教剧、讽喻剧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封建关系在英国受到比别的国家更为彻底的摧毁。在他的时代,个性已经成为先进思想家注意的中心。他们信仰人的个性力量,保卫所谓天赋的个人权利。英国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在《乌托邦》中说:“自然命令我们生活得愉快,就是说,把享乐当作我们全部行为的目标,他们(指乌托邦人)把德行解释成依从自然的命令的生活。自然还号召人们互相帮助达到更愉快的生活,这个号召是正当的。决没有任何一个人得天独厚,其命运比别人高超。自然对有生血气之伦,无不一视同仁地善意看待。”这里除了“互助”这一点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所独有的东西,其他都是当时先进思想家的共通的语言。莎士比亚的创作是在文艺复兴和唯物主义盛行的情况下涌现出来的。汤显祖的《牡丹亭》的主题,同当时左派王学的某些近似个性解放的说法有渊源关系,但他们对爱情即所谓人欲的态度,只要不断然加以否定就很不容易了。以理学家而兼文学批评家的李贽也许是难得的例外。他曾在《藏书》卷二九的《司马相如传》提出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思想。但《牡丹亭》完成于《藏书》出版的前一年,很难说直接受到后者的启发。另一方面,汤显祖时代的左派王学又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它对封建礼教的批判不可能是坚强有力的。汤显祖和同时代的小说戏曲作家不时在作品中乞求鬼神的助力,同这种唯心主义的有神论思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以戏剧传统而论,汤显祖的条件却比莎士比亚好。在莎士比亚时代,英国戏剧不久前才摆脱了中世纪的落后状态而成长,历史很短。在汤显祖以前三个世纪,中国已经出现过一个戏曲的黄金时代,这就是以关汉卿、王实甫为代表的金元杂剧。在高则诚的《琵琶记》之后,民间的南戏也已经发展成为传奇,汤显祖生活在传奇的全盛时期。富有民主性的元代杂剧并未受到明代文人的普遍重视,汤显祖所收藏的金元杂剧却据说达一千种之多。这个数字为现在所知的金元剧目的两倍。近千种戏曲的精彩处,他都能一一背诵。这是姚士粦和他交谈后所得的印象。《牡丹亭》对金元杂剧的成句、熟语那么灵活自如地广泛运用,可以证明姚士粦的记载大体是可信的。臧懋循也曾承认他所编集的《元曲选》一百种,其所根据的部分材料——抄本杂剧两三百种就出于汤显祖的鉴定和选择②。元代杂剧中,《西厢记》(包括金代的诸宫调在内)、《倩女离魂》、《两世姻缘》、《碧桃花》、《墙头马上》、《张生煮海》以及其他多种杂剧都同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主题有关。从文学语言来看,董《西厢》比任何一种元代杂剧对《牡丹亭》的影响都要大。当然最值得注意的是《倩女离魂》和《两世姻缘》两个杂剧。前者是中国戏曲里《惊梦》这一个关目的最早的来源。深闺小姐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出之于口的被抑制的愿望,巧妙地通过梦魂的形象传达出来了。它十分有力地描写了封建压迫下青年女性对自由幸福的向往。这个主题在《牡丹亭》里得到更光辉的成就。后者玉箫女和韦皋的再世姻缘、她的自画肖像等情节对《牡丹亭》的相应部分肯定有借鉴作用。
杂剧的第四折也是《牡丹亭》最后一出《圆驾》的蓝本。
汤显祖同莎士比亚的种种不同有如上述,但他们的作品在外形上却有很多类似之处。
他们都不曾多花脑筋为自己的剧本编造故事。莎士比亚的三十六个剧本绝大部分取材于中世纪的口头传说、史诗和传奇故事,只有个别例外。汤显祖的五个戏曲则以唐人传奇、《大宋宣和遗事》及明人笔记小说为依据。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以1303年发生在意大利维罗那城的真人真事为基础。1562年英国诗人阿瑟·勃罗克(Arthur Brooke)根据法文翻译的这个意大利故事写成长诗,1567年威廉·潘特(William Paynter)又把故事从法文译成英文。这两者是莎士比亚创作的主要依据。《牡丹亭》取材于明代笔记小说《燕居笔记》卷九中的《杜丽娘慕色还魂》。据说这是发生在南宋的故事。笔记同传奇的同异约略相当于《会真记》同《西厢记》的关系。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都穿着古代的服装,而在他们的胸中跳动着的却是一颗同时代的心。当朱丽叶说:“你即使不姓蒙太玖,仍然是这样的一个你。姓不姓蒙太玖又有什么关系呢?它又不是手,又不是脚,又不是手臂,又不是脸,又不是身体上任何其他的部分。”对封建门第的无所谓的态度,显然带有同时代的人文主义色彩。这种封建族姓观念在英国资本主义发轫以后两百年的狄更斯时代,以至更后的哈代的时代也不曾绝迹。读了第一幕第一场罗密欧的对话:“她已经立下了这样的誓言,为了珍惜她自己,造成了莫大的浪费;因为她让美貌在无情的岁月中日渐枯萎,不知道替后世传留下她的绝世容华。”我们会辨认出这同时又是莎士比亚第一首十四行诗的主题,是一个当代人的思想。《牡丹亭》讽刺杜宝“则平的个李半”而超迁相位,明明白白同当时边将以收买蒙古族女酋长三娘子而官升尚书、侍郎有关。
汤显祖同莎士比亚之所以借古喻今,不自己编造故事,除了当时剧作家习惯于这样做之外,一个原因是当时作家不便无所顾忌地揭露现实。
汤显祖的《紫箫记》传奇就因为“是非蜂起,讹言四方”③,而被迫搁笔,始终没有完成。比莎士比亚时代略早的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第一次提出了他对社会主义的空想,但是他不得不谨慎地来一个假撇清。他在着作的结尾说,这个乌托邦“有不少荒谬的地方”,他“不能同意他(指书中人物)所说的一切”。到莎士比亚时代,言论不自由的情况并没有改变。马克思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雅典人台满》第四幕第三场中的一段对话,指出作家“绝妙地描绘了货币的本质”②。马克思这句话当然是正确的,但同样正确的是莎士比亚并不懂得政治经济学。作家有了本于经验的感性认识,有时是可以作出鲜明生动的描写的,虽然他的理性认识还停留在朦胧的模糊不清的状态中。我认为这样的情况正是莎士比亚和汤显祖之所以只能不自觉地借用古代传说的更为重要的原因。
这一篇无意于作结论的论文,不妨在此结束。与其说本文已经就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作了比较,不如说只是对他们之所以成为汤显祖、莎士比亚的各种条件作了极其肤浅的解释。我深信只有对自己民族文化具有不可动摇的自豪感的人才能充分评价别民族的伟大成就而不妄自菲薄。一个最有信心的民族也一定最善于向别的民族学习,而不骄傲自满。如果这篇文章能有助于人们心中这种情操的滋长,那就是我的意外收获了。
1963年春
(原刊《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