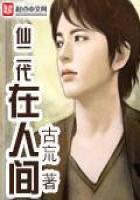100多年前的呼兰,是松花江北岸一座并不繁华的小城。城中只有两条大街,一条自南向北,一条从东到西。松花江的支流呼兰河绕城而过, 小城由是得名。
1911年的端午,萧红出生在呼兰河畔的一个乡绅之家。那一年,南方革命军的枪声震天动地,却似乎并未惊醒这个远在中国东北角的小城。呼兰河依旧悠悠流淌,小城的日子依旧宁静、保守而荒芜。
萧红本名张乃莹。张家的祖上从山东经过闯关东来到东北,经过一番艰辛,创下了殷实的家业。第四代张维祯继承了呼兰的部分土地和房产,于是带领全家迁到呼兰。由于年过半百而膝下无子,张维祯遂在族中选定堂侄张廷举作为继子。12岁的张廷举过继到呼兰后继续求学,从黑龙江省立优级师范学堂毕业,日后成为黑龙江省教育厅秘书。
1909年,张廷举与同是出自乡绅之家的姜玉兰成婚。两年过后,他们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取名乃莹。这个女孩就是日后的女作家萧红。
萧红的童年在呼兰度过,虽然生活在父母身边,但得自父母的眷爱却很有限。5岁那年,胞弟张秀珂出生,从此母亲便很少顾得上她。至于父亲张廷举,是个形容严峻,不苟言笑的男人,对她始终疏远。在幼小的萧红眼里,他总是斜视着自己,威严而高傲,每当从他身边经过,萧红就觉得自己的身上像生了针刺一样。
在一篇自传性的散文《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中,萧红直言不讳地写道: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同样地吝啬而又疏远,甚至于无情。
8岁那年,萧红的生母姜玉兰去世,自此父亲的脾气愈发暴躁,甚至偶然打碎了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地步。
3个月后,父亲娶回了继母梁亚兰,那时,萧红和弟弟为母亲志哀而缝在鞋面上的白布还未撕去。
在这样的环境里,萧红能得到的唯一温暖来自祖父张维祯。祖父身材高大,喜欢拿着手杖,嘴里含着旱烟管,眼里总是溢满盈盈笑意,亲切而和蔼。萧红回忆道:等我生下来了,第一个给了祖父无限的欢喜,等我长大了,祖父非常地爱我,使我觉得在这世界上,有了祖父就够了,还怕什么呢?虽然父亲的冷淡,母亲的恶言恶色,和祖母的用针刺我的手指的这些事,都觉得算不了什么。
性情温厚,待人宽容而善良的祖父,一举一动都给萧红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让她懂得,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祖父亦给了萧红文学的启蒙,在她心中播下了美的种子。在《呼兰河传》中,萧红记下了自己幼年跟随祖父学诗的片段:早晨念诗,晚上念诗,半夜醒了也是念诗。念了一阵,念困了再睡去。
祖父教我的有《千家诗》,并没有课本,全凭口头传诵,祖父念一句,我就念一句。
祖父说:
“少小离家老大回……”
我也说:
“少小离家老大回……”
都是些什么字,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只觉得念起来那声音很好听。所以很高兴地跟着喊。我喊的声音,比祖父的声音更大。
我一念起诗来,我家的五间房都可以听见,祖父怕我喊坏了喉咙,常常警告着我说:“房盖被你抬走了。”
听了这笑话,我略微笑了一会工夫,过不了多久,就又喊起来了。
夜里也是照样地喊,母亲吓唬我,说再喊她要打我。
祖父也说:
“没有你这样念诗的,你这不叫念诗,你这叫乱叫。”
但我觉得这乱叫的习惯不能改,若不让我叫,我念它干什么。每当祖父教我一个新诗,一开头我若听了不好听,我就说:“不学这个。”
祖父于是就换一个,换一个不好,我还是不要。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这一首诗,我很喜欢,我一念到第二句,“处处闻啼鸟”那处处两字,我就高兴起来了。觉得这首诗,实在是好,真好听“处处”该多好听。
还有一首我更喜欢的:
“重重叠叠上楼台,几度呼童扫不开。
刚被太阳收拾去,又为明月送将来。”
就这“几度呼童扫不开”,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就念成西沥忽通扫不开。
越念越觉得好听,越念越有趣味。
……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这首诗本来我也很喜欢的,黄梨是很好吃的。经祖父这一讲,说是两个鸟,于是不喜欢了。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这首诗祖父讲了我也不明白,但是我喜欢这首。因为其中有桃花。桃树一开了花不就结桃吗?桃子不是好吃吗?
所以每念完这首诗,我就接着问祖父:
“今年咱们的樱桃树开不开花?”
在萧红的笔下,父亲是一个暴君,母亲也仅仅只是一个不爱她的母亲,但是只要提到祖父,她的笔调就立刻变得温情、柔软。祖父不仅给了她唯一的宠溺和疼爱,亦给了她一所后园。每当被祖母责骂,萧红就会拉着祖父的手往屋外走,边走边说:“我们后园里去吧。”
祖父的后园里,有樱桃、李子和大榆树,有如火般热烈绽放的玫瑰,还有各种不知名的草种吐出一串一串的花穗。幼小的萧红在这里捉蝴蝶、追蜻蜓,观看蜜蜂采花粉,跟着祖父铲地、拔草、栽花,学着分辨各种植物。困了,就找个阴凉的地方,把草帽盖在脸上,闭上眼睛就睡着了,醒了就再跑,再玩。玩腻了,就去和祖父乱闹一阵,或是在祖父的大草帽上偷偷插上一圈玫瑰花,或是抢过祖父浇菜的水瓢,把水往天上扬,喊着:“下雨了!下雨了!”……
后园向萧红敞开了另一个世界,这里没有威压和欺凌,没有势利和冷漠,只有高远的天,洁白的云,明亮的太阳和自由自在的花草树木。淳美的自然将萧红孕育成一个敏感多思的少女,她率真、任性、无拘无束,她将用一生的时间去追寻爱与自由,这两件源自祖父与后园的最宝贵的东西。
一年又一年,伴随着祖父和后园的春夏秋冬让荒芜的岁月变得明媚起来。
曾经祖父给萧红讲诗,讲到“少小离家老大回”时,萧红问祖父:“我也要离家的吗?等我胡子白了回来,爷爷你也不认识我了吗?”祖父一听就笑了: “等你老了还有爷爷吗?”看到萧红不开心了,祖父便赶忙搂着她说:“你不离家的,你哪里能够离家呢……”
萧红害怕离开祖父。
她深深记得,每当父亲打了她的时候,她就来到祖父的房里——从黄昏到深夜,看窗外的白雪,如棉絮一样飘着,而暖炉上的水壶盖,则像伴奏的乐器一样振动。
她亦深深记得,祖父常常把布满皱纹的手放在她肩上,而后又抚摸着她的头,温和地说:“快快长吧!长大就好了!”……
直到有一天,萧红真的长大了。
后园里的玫瑰依旧花开满树,但祖父不在后园里,他被装进了一个黑黢黢大箱子,一声不响地走了。
那是1929年6月7日,萧红躺在后园的玫瑰树下,园中依旧飞着蜜蜂和蝴蝶,绿草依旧散发着清馨的气息,一切都还是十年前的样子。十年前,母亲去世了,她仍在园中扑蝴蝶;十年后,祖父去世了,她却一直哭着,用祖父的酒杯饮了酒。——人间的温暖和爱仿佛都被带走了,她的心像被丝线扎住了一样痛。
躺在玫瑰树下的萧红在心中暗暗发下誓愿:
以后我必须不要家,到广大的人群中去……
可是,她颤怵了,人群中,还会有人像祖父一样疼她吗?
祖父去世了,后园的花儿也谢了,萧红最终离开了家。然而只有“少小离家”,却没有“老大回”。
童年里,那些虽然缺少父母的爱却不失为无忧无虑的日子,再也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