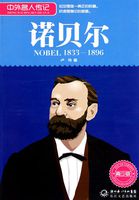1920年秋季,呼兰的两所小学开设了女生部,首次招收女学生。这一年萧红9岁,进入了龙王庙小学女生部就读一年级,从此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求知生涯。
小学时代的萧红已然表现出了记忆力好、聪明灵活等优点。她学习勤奋,成绩优异,作文尤其写得好,在文学方面的天赋与才华已然小荷初露。
高小毕业后,萧红希望继续念中学,却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整天都对萧红沉着脸的张廷举,这次也冷冷地说:“上什么中学?上中学在家里上吧!”
张廷举不让萧红上中学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新文化、新思想在青年学生中的影响更加广泛,身在教育界的张廷举不会不知道中学学堂里的风气,那些学生以追求个性解放为名,自由恋爱,不服管束,动辄还要从“旧家庭”出走,这些都是张廷举所无法容忍的。他当然不希望萧红被这些不良习气“教坏”,干出荒唐事来,败坏张家的声誉。
年少的萧红畏惧父亲,但她想要上学的心是坚定的,她开始了对父亲和继母持久战式的反抗。半年多的时间里,继母反复同她吵嘴,父亲也一再责骂她,而她却始终不放弃求学的信念。
一天,父亲又一次无端冲她吼道:“你懒死啦!不要脸的。”萧红难以压抑内心的屈辱,她再也忍受不了这个家庭如机器一般对她的压榨,大声反驳父亲道:“什么叫不要脸呢?谁不要脸!”话一出口,愤怒如火山一样爆裂喷发的张廷举,立即扬起手,将萧红重重地推倒在地。
萧红慢慢从地上爬起来,没有低头,亦没有掉下一滴眼泪。多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萧红依旧不忘在文中讽刺她的父亲:父亲从那时起他感到父亲的尊严是受了一大挫折,也从那时起每天想要恢复他的父权。他想做父亲的更该尊严些,或者加倍的尊严着才能压住子女吧?
就这样一天天与父母僵持着,萧红渐渐病了。她的那些顺利升学的同学写信给她,向她讲述中学里热闹的事,也说些她不明白的功课。读着这些满含欢悦的信,病中的萧红心情愈加焦急。
老祖父心疼孙女,帮她向儿子求情。张廷举无动于衷,坚决不肯让步。亲戚朋友们也来劝说,然而每每提到萧红上学的事,张廷举都不答话,只是板起脸走到院子里。于是渐渐地,没有人再敢提起这件事了。
夏天过去了,秋天过去了,寒冷的冬天也就要过去了。正值青春年华的萧红在这个阴冷压抑的家里被困了整整三个季节,几乎是在用生命与父母抗争。
1927年春天,16岁的萧红终于如愿升入了中学。至于她的父母最后为何会妥协,萧红曾在文章里解释道:“那不是什么人帮助我,是我自己向家庭施行的骗术。”而在她留下的所有文字里,却找不到任何关于这一“骗术”的具体说明。据说,萧红曾以出家相威胁,张廷举为了维护张家的颜面,才被迫应允。
萧红就读的中学,是哈尔滨的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张廷举之所以把萧红送到这里读书,是因为这是一所为富家女子开设的十分保守的学校,校长孔焕书的思想也极为封建,这正合张廷举的心意。
不过,这所学校里依然有一些思想开放的教员,在他们的教导下,萧红全身心地投入了知识的海洋,如饥似渴地汲取精神的养料。她仿佛一棵曾被家庭的土壤抑制的盆栽,一经回到广袤的大地,就开始欢快地抽枝长叶,焕发出勃勃生机。
美术老师高仰山毕业于上海,他从那里带来了充满活力的现代艺术气息,亦带来了与时俱进的新思潮。萧红在他的感染下,萌发了对绘画的爱。她最爱画的是自然的风景,因为小时候常在祖父的后园里嬉戏,萧红对自然的美有着敏锐的感悟力,而用画笔勾勒描摹纯美的自然,仿佛也让萧红的心变得更加纯净安宁。在艺术的世界里,她可以暂时忘掉烦忧,忘掉她曾目睹过的一切不平、一切丑恶和一切伤痛。
在高仰山的带动下,萧红和班上的同学一起成立了“野外写生会”。每到星期天,他们便背起画板和颜料,跟着高老师四处写生。他们画树林、画江岸、画风雪、画阳光,最爱去的地方是马家花园,这里有着中西合璧的建筑,亦有着种类繁多的花草树木。萧红仿佛拥有了一个更大的“后园”,这个后园带给她快乐,也启发着她无穷的创造力。
画笔让萧红体味到了一种自由。此刻,她的生命正如一张白纸,将在这张纸上描绘怎样的风景,将使用怎样的线条组合和色彩搭配,这一切,都应该由她自己选择,都可以由她自己决定。萧红懵懂地感到,自己生命的图样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她要在这张纸上建构出一番属于自己的轰轰烈烈。
萧红的最后一幅美术作业,画的是《劳动者的恩物》,这是高仰山为这幅画取的名字。当时,高老师在教室里放了许多静物,同学们都按照老师的要求摹绘,而萧红却去找老更夫借了一支黑杆的短烟袋锅子和一个黑布的烟袋,开始自己的创作。萧红从小就常与呼兰的农民、长工交往,她了解他们的生存处境,也喜欢他们的朴实和善良。这烟锅和烟袋,真实地反映了劳动者辛劳、卑贱的状态,亦寄托了萧红心中深切的同情。她已经开始在艺术创作中有意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了。
另一位对萧红有着深远影响的老师是教授历史的姜寿山。姜老师毕业于北京大学,在课堂上,他不仅讲授历史知识,还为同学们讲解世界见闻,因为讲说生动,深受学生的欢迎。姜寿山是萧红的新文学启蒙老师,是他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新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学译本介绍给萧红,让萧红对文学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热情。那时,萧红也经常阅读哈尔滨的《国际协报》文艺版。在这些中外名家名篇的熏染下,她的文学素养不断提升,文学天赋和写作欲望也渐渐被激发出来。
萧红开始写作诗歌和散文,她的作品以“悄吟”的笔名常常在校刊和壁报上发表。虽然此时这些作品大都抒写的是稚嫩的少女情思,但语言十分优美,受到老师和同学的喜爱,已然显现出了萧红的创作潜力。
1928年冬天,日本为控制中国东北,迫使奉系军阀张学良签订《满蒙新五路协约》,协约规定,日本享有东北五条铁路的修建权。11月9日,为保护东北路权,哈尔滨学生罢课,上街示威游行。在其他学校男生的热情鼓舞下,女中的学生不顾校长的严厉反对,也加入到了游行的队伍中。
骆宾基曾在《萧红小传》中说,萧红是个很少说笑、内心孤独的女孩。而此刻,这个安静而柔弱的萧红站在此起彼伏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喊声中,激昂的学生运动仿佛有着巨大的感召力,让她激奋,让她被一种强烈的民族情绪笼罩——
我只感到我的心在受着挤压,好像我的脚跟并没有离开地面而它自然就会移动似的,我的耳旁闹着许多种声音,那声音并不大,也不远、不响亮,可觉得沉重。它带来了压力,好像皮球被穿了一个小洞咝咝的在透着气似的,我对我自己毫无把握。
萧红意识到,她不仅是她自己,她也属于她身处的这个群体,她身体里流动的青春的热血同样也在沸腾。她对这片土地的爱,连同这片土地上的苦难所带给她的激愤,统统都被激荡出来,她想要宣泄,想要呐喊。她自告奋勇承担起了散发传单的任务,在市民群众中大声朗读着传单。
然而,铁路最终还是在东北由日本人建成了。
这次失败的示威游行在萧红的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萧红说:“每当我读了一节关于学生运动的记载文章之后,我就会想起那年在哈尔滨的学生运动。”
那些斗争、伤口和鲜血带给一个17岁少女的惊惧是可想而知的。更让萧红难以忘怀的,是示威者的盲目和混乱,“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初目的似乎被示威者遗忘了,人群愤怒地冲向市政府大楼,而在遭到了警察的干涉后,竟然连政府也忘了,又高呼起“打倒警察”的口号。这场没有组织和纪律的运动,伤害的终究只是无辜的普通人。17岁的萧红似乎从这条铁路的建成中明白了什么,她的心逐渐成熟起来。
在参加社会活动的过程中,萧红结识了一些外校的男生。她的远亲表兄陆哲舜(一说陆振舜)在哈尔滨政法大学读书,因为住地较近,两人之间有了频繁的往来。陆哲舜欣赏萧红的气质与才华,亦时常给萧红指引和鼓励。渐渐地,萧红的心中对表哥产生了一种别样的感情。和表哥在一起,她觉得快乐,却又说不清原因,似乎是爱,又似乎只是志同道合的友谊。
不等萧红思索清楚这份懵懂的情感,一纸婚书突然降临在了她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