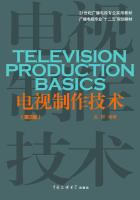秦王坐章台以见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传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万岁。相如视秦王无意偿赵城,乃前曰:“璧有瑕 ,请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 ,倚柱,怒发上冲冠,谓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发书至赵王,赵王悉召群臣议,皆曰:‘秦贪,负其强,以空言求璧,偿城恐不可得。’议不欲予秦璧。臣以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国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强秦之欢,不可。于是赵王乃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书于庭。何者?严大国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见臣列观,礼节甚倨。得璧,传之美人,以戏弄臣。臣观大王无意偿赵王城邑,故臣复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
这里的“怒发上冲冠”五字,诚足表出蔺相如当时的愿以“头与璧俱碎”的精神。但后人借用这句成语,改为“怒发冲冠,冠为之裂”则不通了。又如某君译欧文(Washington Irving)小说,有老人之袖“飘飘可三大英里”,乃译为“飘飘三大英里,遮断行人”,则简直不通了。夸饰就是说谎,但说谎说得不当,不如不说。
(三)叠字
用字巧妙的方法很多。中国文中,有一种用叠字以增加文句的意义的,如《诗经》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最著名的如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连用许多叠字,活现出一种凄凉神气!又如《白雪遗音》中的“人儿人儿今何在?花儿花儿为的是谁开?雁儿雁儿因何不把书来带?心儿心儿从今又把相思害!”这种叠用名词的法子很可增加语句的活泼与有力。
“大匠诲人,能与人以规矩,不能与人以巧。”岳飞论用兵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巧妙是不可教的,只要自己努力去研究,能够多读、多作、多研究,自然能出语惊人,用字有神。俗语说“熟能生巧”,这句话是很有意义的。
(选自《作文讲话》,北新书局,1930年)
用词(张志公)
一用词的几个基本问题
用词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用哪种类型的词的问题,也就是用词的基本原则问题;一个是用哪个词的问题,也就是基本原则的实际运用问题。
用哪种类型的词的问题,答案很简单:要按照大家共同一致的习惯使用大家都懂得的词。
每个词表示一定的意义,有一定的用法。这意义和用法都是基于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多少年来的共同一致的习惯形成的。按照这种习惯来用词,大家都懂;不按照这种习惯,大家就不懂,或是不易懂。高尔基说,读者“有权利要求作家用最丰富的、灵活的语言的普通字眼对他们说话”。这可以说是用词的基本原则。
怎么知道某个词是不是大家都懂得的词呢?最有效的检查方法是看一看口语里和按照口语写的好的作品里是否常用这个词。常用的一定是大家都懂得的词,不常用的一定是大家不易懂的词。这也就是说,要尽可能地多用口语里和好的作品里常用的词,避免不常用的词。赵树理谈他的写作经验时说:“‘然而’听不惯,咱就写成‘可是’;‘所以’生一点,咱就写成‘因此’,不给他们(按:指农民)换成顺当的字眼儿,他们就不愿意看。”这句话值得体味。
常用不常用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从前常用的,现在可能不常用了,从前不常用的,现在可能常用了;这个地方常用的,那个地方可能不常用;这些人中间常用的,那些人中间可能不常用。这样就引出了下面这一连串的问题。
(一)方言土语和普通话
方言土语里的一些词,是某个地方常用的,别的地方不用或者不常用的。这种词在写作中可以不可以用呢?
总的原则是:写作应该用普通话,不宜于使用方言土语。方言土语是流行于一个小区域的,写作中用了方言土语,无异乎替作品划了一个圈子,使它只能在这个圈子里产生作用,一跑出圈子去,人家就不懂了。这显然是削弱作品的力量,不应当的。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我们应当积极大力地推广普通话。提倡说普通话,提倡用普通话写作。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方言土语绝对用不得。首先要看作品的性质,其次还要区别方言土语的性质。
文学作品里,为了特定的目的需要用语言来表现地方色彩、或是用语言来表现人物的特点时,偶然采用些必要的方言土语是许可的。非文学作品,不大有这种需要。
方言土语是服从于民族共同语的,然而民族共同语并不排斥方言土语里的若干优秀的成分。事实上,民族共同语总是以最有力量的、使用范围最广的某一种方言为基础,吸收了别的一些方言来加强了它自己而形成的。因而,正如鲁迅所说,“方言土语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各就各处的方言,将语法和词汇更加提炼,使他们发达上去的,就是专化。这于文学,是很有益处的,它可以做得比仅用泛泛的话头的文章更加有意思。”
其次,方言土语里的有些词固然是只能用于这个方言区域的,出了这个区域,人家就不懂。但是另外也有些词,尽管别的地方本来不用或是不常用,可是用起来大家也能懂。像这种词,如果它们有一定的用处,那就不仅能在写作中使用,而且很有可能被吸收进民族共同语里去,成为民族共同语的词汇的一个构成成分。
(二)文言和白话
“文言”和“白话”是对待着说的,它们指的是写作中所用的语言。用现代口语或是跟现代口语很接近的语言所写的文章叫作“白话文”。至于文言,就可以有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解释。广义地说,凡是跟现代口语不同的,都可以叫作文言。可是,所谓跟现代口语不同,又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古代的口语,比如《水浒传》的语言,就是跟当时的口语很接近的,虽然跟现代的口语很有些不同的地方;另一种是在写作的当时,跟口语有很大的距离,比如清朝桐城派、阳湖派那些作者所写的古文就是跟当时的口语很不相同的。狭义地说,只有这第二种才算是文言,第一种仍算是白话。我们这里所说的文言是广义的,也就是说,凡是现代口语里不用或不常用的字眼,我们都管它叫作文言词语。
从原则上讲,应该尽可能地按照现代口语来写作,文言词语应该尽可能地避免。这道理很简单,不必多讲。
然而,文言词语也并不是绝对用不得。古典作品里所表现的古人的语言,有许多优美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
鲁迅是反对文言、倡导白话的。可是在他的作品里时常可以发现些文言词语。下边这些句子是从他的一篇杂文《怎么写》里摘抄下来的,下边点了黑点儿的都可以算作文言词语。
(1)有时有一点杂感,仔细一看,觉得没有什么大意思,不要去填黑了那么洁白的纸张,便废然而333止了。
(2)记得还是去年躲在厦门岛上的时候,因为太讨人厌了,终于得到“敬3鬼神而远之33333”式的待遇,被供在图书馆楼上的一间屋子里。
(3)寂静浓到如酒,令人33微醺33。
(4)望后窗外骨立33的乱山中许多白点,是丛冢33;一粒深黄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灯。
(5)我靠了石栏远眺33……
(6)几乎就要发见仅只我独自倚着石栏,此外一无33所有33。
(7)腿上钢针似的一刺,我便不假思索3333地用手掌向痛处直拍下去,同时只知道蚊子在咬我。
(8)恰如冢中3333的白骨33……
(9)开首的两句话有些含混,说我都与闻其事3333的也可以,说因我“南来”了而别人创办的也通。
(10)第六期没有,或者说被禁止,或者说未刊,莫衷一是3333,我便买了一本七八合册和第五期。
(11)假使说的是张龙赵虎,或是我素昧平生3333的伟人,老实说吧,我绝不会如此留心。
(12)倘作者如此牺牲了自由,即使极小部分,也无异于削足适333履3的。
(13)纪晓岚攻击蒲留仙的《聊斋志异》,就在这一点。两人密语,绝不肯33333333泄,又不为第三人所闻,作者何从333333333333333知之?333
(14)万一变戏法的定要做得真实,买了小棺材,装进孩子去,哭着抬走,倒反索然无333味3了。
不仅在这类带有议论性的文章里用得着文言词语,文艺作品里有时也用得着。
(15)他真是一个巧言令色3333的小人。
(郭沫若:《屈原》)
(16)就连我现在都还听得毛骨悚333然3呢。
(同上)
(17)那似乎有些高兴的眼光,正眺望33着四周,跟着爸爸回娘家,是一年中难逢到33的好运气。
(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这里举这些例子,只是要说明一点:写作中在必要的地方适当地运用一些文言词语是可以的,有时并且是有好处的。就拿前面举的例子来看,有的是口语里没有相当的说法的,有的是比口语的说法简洁有力的。毛泽东同志说:“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由于我们没有努力学习语言,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
毛泽东同志这段话肯定了学习古人的语言的必要,同时也指出了学习的原则:第一,要吸收的是那些“有生气的东西”,“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第二,“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是要“坚决反对”的。
就是那些有生气的文言词语,也还要运用得当。在不必要或不适当的地方生硬地搬弄上一些文言词语,不但于文章无益,反而会损害了它的风格。至于自己乱造些文言腔调的字眼,那当然更是不好的。下边是几个在期刊上发现的运用不得当的文言词:
(18)夜班工人在深夜或清早下班后,最好在室外或空气新鲜的室内做几节体操,散步片刻后再入睡,这样可以使因劳动而疲劳的大脑得到调节,使我们更快入睡和睡得更甜。但应注意运动量不要过大,以免引起大脑神经细胞的强烈兴奋而影响入睡。
“入睡”是个文言词,口语说“睡着”。这一句用了三个“入睡”,只有第二个还过得去,虽然也不如说“睡着得快些”自然。第一个根本用错了,那里说的是“散步片刻再去睡”,不是说“散步片刻再睡着”。第三个前头来了个“影响”,两个词这样一配搭,使意思晦涩,不如照口语的习惯说成“……兴奋,以致睡不着”;否则也得把“影响”改成“不能”。
(19)这个寓言,对于我们很有教益。
“教益”原来就是文言尺牍里用得很滥的一个字眼,这里实在不如说成“很有启发的作用”“很有教育的意义”等,比较自然、明白。
(20)这诚然是科学上的奇迹。然而现在这样的“奇迹”却已经司空见惯了。
“司空见惯”是个文言的典故,用在这儿虽然不能算错,但从修辞的效果上看,就不大好。首先,“司空见惯”往往是指常常看见不大好的现象,至少也是指常常看见一般的、无所谓好坏的现象,某种好现象时常发现,我们不大用这个字眼。其次,“司空见惯”的下文是“不以为意”,就是说,因为很常见,所以不在乎了。科学上的重大成就,现在确是很常见的,可是我们绝不因为常见而不在意。正相反,对于那些伟大成就——那些“奇迹”——我们经常是极端重视的。从这两方面看,在这里用了“司空见惯”这么个文言字眼,不但不能加强语言的表现力量,反而是减弱了力量。
(21)有计划地发展儿童的举动行为及运动技术以使从多方面发展脑髓的反射机能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以使”是生造的文言虚词。文言里有“以便”“使”“使之”“使能”等,没有“以使”。这里可以用“以便”。
运用文言词不妥当的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的。这里把用错的,不当用的,用的不是地方的,生造的,每样举了一个,无非提醒读者一声,指出应当注意的问题而已。
(三)模糊和明确
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词,有些含义是相当模糊的。使用的范围最广,频率最高的词,含义往往也最模糊。像“打”“搞”之类的词,离开了上下文真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词义模糊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它本来就是只表示一个模糊概念的。比如“这个疑问长时间没有弄清楚”。“长时间”是多少时候?几十年?几年?几个月?“长”是和“短”比较而言的,它并不表示确切的数量。另一种情况是,能够表示很多意义的词,往往成为含义模糊的词,如上边举的“打”“搞”之类。说话写文章,有时候可以甚至需要使用模糊一些的词,有时候就要求尽可能地明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应当由于滥用把一个含义本来明确的词弄得模糊起来。下边举几个例子:
1.基本上
“基本上”是用得很广泛的一个词。这个词很好,很有用,可是用得有点滥,一滥就会掩蔽了它的特点,反而使它不能充分地发挥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