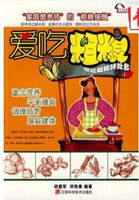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关于“我们为什么会发胖”的批判性思维方式绝不是我原创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908年,德国内科医生古斯塔夫·冯·伯格曼(Gustav von Bergmann)首次应用了术语“亲脂性”——也就是“喜爱脂肪”——来说明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对于储存脂肪的喜好程度。其实,我在本书中所讲的内容,基本上都来自冯·伯格曼的理念,是其理论根基的现代发展版本。而如今,德国内科医学会的最高奖项之一就是以冯·伯格曼命名的。
冯·伯格曼对肥胖学的看法直截了当,他认为肥胖是多余脂肪代谢路径的失调,然后他依着这条思路着手研究脂肪组织的调节作用。我先前已经引用了许多他的观察结论,他发现,我们身体中的有些组织有明显的“亲脂性”,非常热衷于积累脂肪;其他组织则没有这种嗜好。他明智地指出,这种属性差异不仅在组织之间存在,而且还因人而异。正如身体的有些部位容易长毛发,其他部位不长;有些人毛发比其他人多,有些人毛发比其他人少;有些部位宜积累脂肪,其他部位不积累;而有些人就比其他人胖,这些人的身体显然更具“亲脂性”。这些人通常很早就开始发胖,他们自己则对此无计可施。那些身体不是亲脂性的人则比较清瘦,即使他们作出种种努力,也很难增肥。
20世纪20年代后期,冯·伯格曼的亲脂性理念被维也纳大学的尤利乌斯·鲍尔(Julius Bauer)发扬光大。鲍尔是将遗传学和内分泌学应用于临床医学的先驱者,那时这些学科还都处于启蒙阶段。那个年代很少有医生能想象出利用基因特点去判断人体特征和诊断疾病。鲍尔比任何人更清楚基因与疾病之间的关系,他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企图让美国医生看清路易斯·纽伯格“变态食欲论”假设中的种种错误。
纽伯格坚持认为,基因如果对肥胖有作用的话(对此他持怀疑态度),可能仅仅让肥胖者产生无法抑制的想多吃的冲动。鲍尔则反驳称,基因引发肥胖的唯一途径不是控制大脑冲动,而是直接影响了脂肪组织本身的调节性能。鲍尔在文章中说:“基因调节亲脂性,然后这种调节就决定如何支配我们的能量摄入以及能量消耗。”
鲍尔认为肥胖一族的脂肪组织类似于恶性肿瘤。他解释道,这两者都有各自的侵略扩张议程。肿瘤受到驱使,生长扩散,这与肿瘤患者的饮食量和活动量没有多大关系。在易发胖的人群中,脂肪驱使脂肪组织成长和扩张,与肿瘤一样。这类脂肪在完成扩张地盘这个目标之前,很少关注身体其他部位在做什么、需要什么配合。鲍尔在1929年写道:“异常的亲脂性组织,即使在营养不足的情况下,也会掠夺食物。它要保持它的脂肪库存,也许还会无视其他组织发来的‘补货’需求。这是一种混乱的状态,脂肪组织只为自己而活,根本不为整个生命体的发展考虑。”
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冯·伯格曼和鲍尔的亲脂性假说在欧洲几乎被全盘接受。随后则风靡美国。1979年鲍尔以92岁高龄辞世时,医学期刊《柳叶刀》为他写道:“他的英语版讲义在当时受到了英美医学界的极大欢迎。”
然而在随后的十多年内,这种概念就消失了。那些没有死于二战或逃离欧洲(鲍尔于1938年离开欧洲大陆)的医生们和研究者不得不处理比减肥更迫切的事情。战后,美国的新生代医生和营养学家开始填补这一研究空缺,他们倾心于纽伯格的“变态食欲”逻辑论,这也许与他们对贪食和懒惰之惩罚报应论的偏见有关。
战后医学界的反德情绪或许可以理解,但却对医学进展毫无帮助。战后,美国的减肥专家和权威对来自德国的医学文献视而不见,虽然正是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在营养学、新陈代谢、内分泌学和遗传学所有这些和减肥相关的领域奠定了基础,并完成了大量极有意义的研究。等到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接手这一领域后,肥胖就正式成为了某种饮食失调——这是仁慈的说法,其实就是想说肥胖是性格上的缺陷。从此以后,期待权威们能够注意到脂肪组织本身有调节作用的一切愿望都付诸东流。
战后,仍有一些研究型医生偶尔会得出相同的结论。作为20世纪60年代儿童肥胖学权威领头人的布鲁赫依然认为,脂肪组织调节方面的缺陷可能就是肥胖的原因,并公开表明她对同行如此无视这一理念感到迷惑不解。
直到1968年,吉恩·梅尔才发现,不同体型的脂肪容量与血液中不同的激素浓度有关,并认为相对激素浓度的细微差别可能就是让有些人发胖,而另一些人就是苗条的原因。换句话说,如冯·伯格曼和鲍尔说过的那样,激素浓度也许就决定了脂肪组织是否具有亲脂性。
战后对“我们为什么会发胖”这个问题最具洞察力的专家,恰好是一位在激素失调方面的权威人士——塔夫斯大学的埃德温·阿斯特伍德(Edwin Astwood)。1962年,他担任了美国内分泌学学会的会长,并在当年的年会上做了个题为“肥胖遗产”的演讲。阿斯特伍德抨击了多吃引发肥胖的理念。他把这种理论描述为“我们暴饮暴食的罪魁祸首”。就我所知,他的演讲与任何一个针对“我们为什么会发胖”的话题一样出彩。他的演讲注重事实证据(始终是个好主意),并且毫无偏见(同样也是个好主意)。
阿斯特伍德首先指出的是,很显然容易发胖和容易保持苗条的倾向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的基因决定的,就像是一种代代相传的遗产。如果基因决定了我们的身高、发色和脚码,那么为什么不相信“基因遗产”能决定我们的体型呢?
但是,如果基因真的控制了我们的体型,它们是怎样做到的呢?1962年,生化学家和生理学家向着确认体脂肪是如何精确调节人体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我们之后就会讨论这一问题。阿斯特伍德认为生物调节就是明确的答案,正如他的前辈冯·伯格曼、鲍尔和布鲁赫一样。如今,有数十种酶和多种激素已经被确认为影响脂肪累积的因素,它们中有些负责把脂肪从脂肪组织解放出来,另一些则把脂肪放入脂肪组织内。总体来看,储存在任何个人或任何人体部位的脂肪数量,将由这些调节力的平衡来决定。
现在,假设这些调节过程发生了差错。
假设,脂肪的释放或它的氧化(即人体把脂肪作为燃料)受到了某些阻碍,或者脂肪的储存或合成变得极为普遍,会发生什么现象呢?缺少食物是饥饿的起因,对身体的大部分部位来讲,脂肪是食物。很容易想象,轻微的营养紊乱就会导致贪婪的食欲。
可是在我看来,肥胖者感觉到的是怎样的饥肠辘辘、垂涎欲滴,绝非瘦骨伶仃的医生们所能理解的……
这一理论足以说明节食减肥为什么如此失败,以及为什么大多数肥胖者在限制饮食时会感到无比痛苦。这个理论对我们的朋友——精神病学家也极有意义,他们总能找到各式各样对食物的偏见,认为正是食物的诱惑给肥胖者带来了黄粱一梦。如果我们食不果腹,有谁能够不被大脑中对各种食物的渴望紧紧缠住呢?饥饿相当可怕,以至于它和瘟疫、战争并称为人类三大最糟糕的噩梦。除了生理上的不适外,肥胖带来的心理压力,以及瘦子们和社会上其他人的奚落和嘲笑,听不完的批评,对暴饮暴食及缺乏“意志力”的指责,还有无休止的负罪感,都让肥胖者更不好受。我们有理由相信,正是肥胖者承受的这些情绪困扰使精神病学家产生了偏见。
为了搞清楚肥胖和我们为什么会发胖,我们必须搞明白阿斯特伍德所理解的概念是什么,以及肥胖学专家们在二战前全盘接受,而战后却停滞不前的理念是什么。贪食(多吃)和懒惰(少动)只是任何调节紊乱的副作用;尽管紊乱很细微,也会将大量的卡路里转移到脂肪组织储存起来。不久后,备受折磨的我们可能真的有冲动或需要去找精神病学家帮助了。并不是情绪困扰让我们发胖,而是无法改变的发胖,以及伴随而来的饥饿感、失落感、被指责贪食的羞辱和所谓缺乏“意志力”的指控使我们感到情绪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