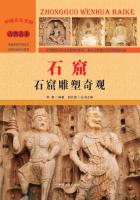一、行藏大节
阎步克曾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并不是游离于社会政治系统之外的智者哲人群体。他们与官僚政治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作为知识分子与官僚的结合体,中国古代的士人阶层自其产生之日起,便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出仕为官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人的第一人生选择。但是,能否成就一番事业不仅取决于文人士子的自身素养,还要取决于多种复杂的社会政治条件,诸如所处时代是否清明、所侍君主是否仁德等等。因此,中国古代文人士子虽然先天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却经常会受到统治阶级的遗弃甚至迫害,于是,出处行藏便成为文人士子的人生抉择之一。
中国古代儒家正统思想中对于文人士子如何选择出处行藏有着明确的进退原则:“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者,耻也;邦无道,富且贵者,耻也。”(《论语·泰伯》)是否参与政治取决于邦国是否有道,如果身在“有道”的治世,就应该积极参与社会政治,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自觉担任伦理道德的维护者和推广者;如果生逢“无道”的乱世,则应该选择退隐,洁身自好,不与污浊的世道同流合污,正所谓“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这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子如何选择出处行藏的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是孔子所提倡的“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也就是说,文人士子的人生目标不应仅停留在个人的食禄与贫富上,而应以道统为最高指向,以整个社会的进步与富足为己任,所以,不一定身居乱世就一定不出仕。韩愈对此有过明确的解释,“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闵其时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故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圣一贤者,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岂使自有余而已?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韩愈《争臣论》)忧国忧民,为君王和百姓担负责任,积极救世也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子的最高精神指向,正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将两个层面综合起来看,出处行藏的选择便成为一个颇具矛盾的问题:汲汲奔命于仕途,既可能是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也可能是贪图富贵名利;退避隐居,既可能是洁身自好、修身自持,也可能是贪图安逸,不关世事。这样“仕”与“不仕”便分别具有双重价值,处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该如何选择亦非易事,中国古代绝大多数文人士子面对出处行藏的人生困境都流露出内心的矛盾与抉择的痛苦。
元代文人也是一样,面对故国的衰亡与世道的纷乱,出处行藏也是折磨他们的人生困境之一。一方面,蒙古贵族入主中原,身处易代之际的许多元初文人怀着对故国的眷恋纷纷退出政治舞台,以不肯仕元的人生选择彰显着内心的志节,关汉卿、龚开是这方面的代表;同时,游牧民族尚武轻文的思想观念使得整个社会纲纪松弛、礼法荡然,许多文人看破世道的纷乱也相继退隐,在隐逸生活中自我娱适,吴镇、王冕是这方面的代表。
这部分文人虽然放弃了“兼济天下”的出仕之路,但秉承着中国正统文人济世苍生的精神积淀,他们却无法泯灭对世事的关怀,所以投身市井的关汉卿在其杂剧中呼号:“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堪贤愚枉做天!”痛斥着世道的黑暗;穷困潦倒的龚开用笔下那些腰束兽皮、头戴蒙盔的群鬼形象寄寓着“扫荡凶邪”的复宋意图;孤舟独钓的吴镇在其画作中张扬着儒家知识分子“斫头不屈,强项风雪”的孤傲与尊严;山阴自耕的王冕通过诗歌创作抒发着内心深处的济世情怀,“山河频如梦,风雨独关心。每念苍生苦,能怜游子吟”。
他们“怀道而避世”,在远离政治与功利的生活中,通过艺术活动张扬个性情感,以笔墨为游戏自娱自适。这样纵然可以获得人生的慰藉,却也不免带有几分无奈的苦楚。元代文人秉承着儒家传统的文化积淀,自然也有着修齐治平、兼善天下的雄心壮志,但是特殊的历史境遇却往往令他们怀才不遇、沉抑下僚,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面前,元代文人不得不放弃出仕之心,在退避与隐逸的生活中通过张扬内心的情志以获得自尊与自我确认。其中虽然沉积着不屑仕进的豪迈与坦荡,却也流露出深埋于心中的无可奈何,正如关汉卿的小令所唱:“世态人情经历多。闲将往事思量过,贤的是他,愚的是我,争什么”;吴镇也曾作诗感叹:“人生遽如许,万事徒碌碌。有尽壮士金,余缪匹夫玉。轩车韫斧钺,粱肉隐耻辱。”世道纷乱,身无所系,既然不能“兼善天下”,那就索性“独善其身”,“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的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在元代文人身上尽显无遗。
另一方面,面对异族的入主与世道的乱离,怀抱用夏变夷、拯济苍生的雄心壮志,一部分文人选择了出仕为官,希求通过自己的努力重整纲纪,挽救苍生,这部分文人以赵孟頫为典型代表。赵孟頫是宋太祖的十一世孙,秦王赵德芳的后裔。他自幼聪慧,更富于才情,书画修养极为深厚。宋亡元兴,他居家湖州,闭门读书。至元二十三年(1286)行台侍御史程钜夫奉诏搜访江南遗佚,被赵孟頫的才华所动,便向元廷举荐。得世祖重用,一路官升翰林学士承旨,从一品,历经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五朝。以“比唐李白、宋苏子瞻”的才华风度赢得了蒙古统治者的优容礼遇。
秉承儒家“三纲五常”的礼法观念,无论君主仁德与否、开明与否,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都有视君如父、以君为纲的责任与义务。蒙受元朝统治者的知遇与优待,赵孟頫怀着知恩图报的心情,尽心竭力报效元廷,“胄子何多士,明公特妙年。诗书师法在,簪绂相门传。曳履星辰上,分光日月边。帝心知俊彦,群望属莫贤。大木明堂器,朱丝清庙弦。……知己诚难遇,扪心益自怜”。心怀知遇之感,赵孟頫对元廷赤心输诚,竭忠尽职,积极参与政事,力图有所作为。然而,元廷对赵孟頫的礼遇多出于安抚江南人心的意图,因此并未将其纳入决策圈。《元史》记载,“帝初欲大用孟頫,议者难之”。生活在蒙古人与色目人的夹缝之中,赵孟頫虽然力求忠君爱民,报效朝廷,却不免遭人猜忌、嫉妒,甚至引起倾轧排挤的官场风波,行走仕途如履薄冰。
同时,因为赵孟頫身为宋室后裔,时人多以“宋裔仕元”为由指斥其变节,“子昂以宋亡孙仕元为显官,其从兄子固耻之,闭门不肯与见”。赵孟頫在自己的心中也有着对故宋的追怀,他的《岳鄂王墓》一诗即流露出无限的悲怆,“莫向西湖歌此曲,山光水色不胜悲”。对自己的出仕元廷也往往怀着强烈的负罪心理:
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古语已云然,见事苦不早。平生独往愿,丘壑寄怀抱。图书时自娱,野兴期自保。谁令堕尘网,宛转受缠绕。昔为水上鸥,今为笼中鸟。哀鸣谁复顾,毛羽日摧槁。向非亲友赠,蔬食常不饱。病妻抱弱子,远去万里道。骨肉生别离,丘垅谁为扫。深愁无一语,目断南云杳。恸哭悲风来,如何诉穹昊。
身为宋室宗亲出仕元廷,赵孟頫一方面遭受到蒙古人与色目人的猜忌和排挤,虽官居一品,却壮志难酬;另一方面又要承受变节辱身、有亏道义的鄙夷与指斥,这种道德的压力更让他内疚自惭,痛苦万分。正因此,徐子方师称赵孟頫是一位痛苦的“精神贵族”。
其实,不止赵孟頫,整个元代文人的命运都颇富悲剧色彩。深染儒家修身治世的传统思想,元代文人心系修齐治平,坚守君子情志而终生不仕却又无法泯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使命感;为了用夏变夷而入朝为官却处处遭遇掣肘,无以施展抱负。真可谓出世亦苦,入世亦苦。如果说艺术活动是中国古代文人徘徊于出世与入世之间的矛盾心理的寄寓与抒写,那么,元代则是中国历史上这种矛盾心理表现得最为强烈的时期。正是由于元代文人挣扎于出世与入世的二维张力之间进退维谷,所以,元代出仕文人所选择的生活也才表现为建立世功与游戏世俗相交错,追求政治功利与标举退避隐逸相伴随。他们虽然出仕为官,却在艺术活动中寄寓着向往隐逸超脱的君子情致、游戏笔墨进而游戏人生的创作观念和任情娱适聊以慰藉的功能观念。而出世入世的矛盾纠结也让他们在追求自由游戏、向往自由娱适的笔墨书写之间,流露出一份淡泊、孤寂、萧条与落寞的审美心境。
二、夷夏大妨
宋元易代,蒙古贵族统一了大江南北,少数民族第一次掌握中国政权,“夷夏大妨”的传统观念敲打着汉族文人内心深处的道德底线,成为困扰元代汉族文人的历史境遇之一。
“夷夏大妨”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伦理价值观。夷,指少数民族,有时也泛指异邦;夏,即华夏之邦。夷夏,指民族区别,尤指文明程度与伦理道德方面的分野”。夷夏之辨的观念在我国春秋以前就已经存在。傅斯年认为夏商周三代由部落到帝国的政治演进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这里的地理形式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其中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三代之时的夷夏之争主要是部落盟主的争夺战,包括益启之争、羿少康之争和汤桀之争。及至春秋时期,夷夏观念有了多方面的内涵,《礼记·王制》有云:“中国戎夷,五方之民。”是民族意义上的“华夏”与“夷狄”之分;同时,夷夏之别还具有文化意义上的“华夏文明”与“蛮夷之邦”的区别,“中国者,聪明睿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战国策·赵策二》);孔子以文化差异为基础,出于对周礼的维护,对“夷夏之辨”作了理论上的阐释,提出“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把是否奉行孝亲忠君之道作为划分夷夏的标志。这样,“夷夏大妨”的观念在我国古代先民的思想中,逐渐具有一种张扬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的民族意识。
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起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秦王朝辽阔的疆域囊括了原来的蛮夷之地,中原之内的夷夏之分基本消除,夷夏之辨的地理含义由中原内部发展为中国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界限。以“天下一统”为指导思想,秦王朝对诸夷狄采取军事征服行动,夷夏之辨主要体现为一种“治边”策略,“夷夏大妨”由文化上的差异逐渐演变为具有政治意义的概念。此后,东西两汉、魏晋南北朝以至唐五代时期胡汉之间,无论是和亲共处,还是刀兵相见,也都属于边防军事的政治斗争,“夷夏之辨的观念虽以种族为表达形式,实已渐成文化为体、政治为用的格局了”。
南宋偏安一隅,夷夏各据一方,夷夏之辨不再仅是边疆问题,政治军事的攻守异势,夷狄异族的进据中原,士人阶层的民族自尊受到打击,如陈亮所言,“既不能却夷狄于塞外,又不能忍一日之辱,坐视民生之涂炭”,不能够再以疆域定正统,颇感“致夷夏之辨亦难矣”。此时的夷夏观念已经不再强调夏可以变夷,而是“要夷狄之好,以见中国之无霸”,如果夷狄“越疆而来参,窃中国之文以自尊异”,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夷狄参与中国政事,以便能够保留中原正统的“人道”,至于严夷狄、“扶皇极”只能等待后世了(《贺新郎酬辛幼安,再用见寄》)。夷狄的武力冲击了严守夷夏之别的传统观念,也打击了汉族文人的文化自尊心。
原本以汉民族本位意识为基点的“夷夏之辨”是一个关涉文野之分、君子小人之别的文化层面的概念,钱穆言:“在古代观念上,四夷与诸夏实在另有一个分别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此即是以文化为‘华’‘夷’分别之证明。”夷与夏的区别不在地域,也不在民族,而在文化。以中原汉族儒家文化为本位的夷夏观念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积淀了汉族文人的民族自尊与文化自信。但是,经过晚唐五代的割据分裂,宋与金的南北对峙,文化与道统的尊严在异族的武力面前显得颇为虚弱。及至蒙古贵族一统天下,完全进驻中原,汉族文人的自尊心与自信力更受到了空前的打击。如何划分夷夏,如何保存礼仪道统成了困扰元代文人的精神重负。
要保守汉族道统而“严分夷夏”,还是要顺应新的大一统而“用夏变夷”,围绕着如何卫道,元代文人有着不同的思量。以郑思肖为代表的激愤遗民源于故国的思绪而严格保守夷夏大妨,拒绝仕元,更在书文诗画之中痛诉夷狄的蛮荒,张扬中原的文明;以郝经为代表的用世文人则秉承着“以天下为己任,救生民于水火”的儒家济世情怀,主张“王道之所在,正统之所在也”,他们大多为了维护王道,发扬儒家正统文化,力图用夏变夷而出仕元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