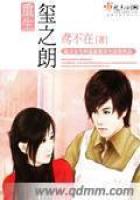这种艺术视角的下移所带来的民间趣味在元代的绘画艺术中主要表现为日常生活题材的广泛引入。从优裕的四民之首沦为平民百姓,元代文人在走向下层社会的过程中发现了俗世生活的美,在艺术活动中,把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作为了审美的对象。例如钱选自题《秋茄图》云:“忆昔毗山爱写生,瓜茄任我笔纵横。自怜老去翻成拙,学圃今犹学不成”,喜爱写生而描绘瓜茄入图,平庸无奇的日常生活被赋予了浓厚的艺术气息;丁鹤年《画菜为马上舍作》曰:“蔬畦新雨过,小摘称居贫。若入君王梦,琼林第一人”,题《画崧菜》曰:“老圃青青甲,平生味饱谙。本无食肉相,岂是厌肥甘”,题《画萝卜》曰:“高氏贤兄弟,常将备夕餐。如何清列士,今作画图看”,在这些题写蔬菜画的诗中,高尚的品质与鲜活的形象融为一体,于世俗题材中寄寓高洁之志;吴镇的自题《写菜》云:“菜叶阑干长,花开黄金细。直须咬到根,方识淡中味”,咬断菜根的民间生活中显然寄托着画家孤傲不屈的儒士情怀。如果说元代画家的走向民间是受时代所迫,那么,将日常生活融入画中则是元代画家的主动选择。在对田园乡野之间的日常事物和平民景观进行描画吟咏的过程中,元代文人寄托了内心的情致,展开了生活的情趣。
与元代画家选择隐逸田园的乡居生活而展示出元代艺术的平民色彩异曲同工,元曲艺术家们大多跻身市井,在元曲创作中选择了平民视角,张扬了平民伦理,通过展示城市平民的价值标准与审美趣味而彰显出元代艺术的平民色彩和艺术观念的世俗倾向。
杂剧和散曲本都是民间的艺术,沉抑下僚的元代文人在跻身市井的平民生活中不仅对下层社会的民间生活充满了同情和理解,更被普通百姓的思想感情与伦理观念所深深感动,他们的价值标准和审美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淡化传统、立足民本成为他们从事艺术创作的思想前提。元代杂剧和散曲的审美视角已经不再是传统的文人士大夫,而是混迹民间的“在野士大夫知识分子”;所表现的思想内容也不再是修齐治平的传统文人生活,而是反映社会现实的下层民众普通而多彩的日常生活;所张扬的伦理观念也不再是儒家传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三纲五常,不仅将传统儒家伦理的善、仁、礼、信等观念民间化、世俗化,更有着与封建礼教相抗的自由、平等的民主意识和勤恳、开拓的奋斗精神;彰显出的艺术精神也不再是温柔敦厚的传统审美情趣,而是通俗晓畅、谐谑幽默、泼辣直爽的市民情趣。
诚如吴梅所言,“曲虽小艺,实陈国风”。立足民间的元曲艺术家们在其艺术作品中展示了平民生活的各个侧面。关汉卿的《窦娥冤》讲述一个善良温顺的平民妇女被无辜迫害的悲苦故事,通过描述平民女子窦娥的悲剧命运表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境遇的恶劣,深刻揭露出封建制度的腐朽与封建社会的黑暗,并通过窦娥刑前发愿与死后托梦的故事情节,真切地表达了平民百姓对人格尊严的维护和对人间正义的呼唤。素以文化承担者自傲的文人阶层走进了民间,不仅用民间社会的价值标准和思想眼光来评判社会、抒写人生,更将寒窗苦读的满腹才情寄托在了民间艺术的创作之中。民间社会被遮蔽已久的不满与反叛、理想与追求终于有了如泉涌一般喷薄而出的历史契机,成就了元代艺术民本思想的精神主调。
无名氏的《陈州粜米》杂剧真实地反映了元代人民在抗旱年代“几至相食”的苦难,表达了人民群众敢于反抗压迫、要求解脱苦难的愿望和理想。作品不仅勾勒了陈州干旱三年的严重天灾,揭露了赈粮官贪污害民的贪酷与凶残,描写了正直善良却饱受迫害劳动人民不肯逆来顺受,敢于反抗奸佞的斗争精神,而且还按照人民大众的愿望,把包公塑造成一个刚正而有智谋,伸张正义而又肯灵活变通的清官形象,包拯假扮“村老子”微服私访,途遇私娼王粉莲,不惜屈身替她笼驴套驴而套出案件故事的情节描写,更是妙趣横生。爱民如子、疾恶如仇,勇敢机智而又幽默风趣的包公形象,不仅增强了作品的戏剧性,更使得整个作品充满了浓郁的民间文学色彩。
“元以功利诱天下”,元代商品经济的发展造就了许多繁华的商业城市,元曲作品也有着对城市生活的描写。例如乔吉的《扬州梦》杂剧、郑廷玉的《一百二十行贩扬州》杂剧、关汉卿的散曲【南吕·一枝花】《杭州景》等等,都对城市生活的繁荣富裕和城市文化的歌舞娱戏作了真切的艺术写照。同时,投身市井的先进文人也在描写城市经济生活的过程中塑造了新崛起的市民形象,呈示出市民社会伦理观念的新变化。秦简夫的《东堂老》就是这样一部杂剧作品。剧作虽然不免有着封建传统的道德劝诫色彩,但是,东堂老这一善良精明的商人形象却深刻地动摇了“重义轻利”的道德观念,表现出追求物质、肯定财富的商人观念和积极进取、勤恳开拓的商人生活观念。
立足平民视角,运用世俗俚语,元曲艺术家们展示了世俗的生活情态和平民的喜怒哀乐,肯定了普通民众的情感与理想,认可了普遍人性欲望的合理性,破除了封建伦理道德对人性的禁锢,张扬了平民社会的伦理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适称元曲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第六次革命,认为“文学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极。其时,词也,曲也,剧本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世”。这种极具平民趣味的“活文学”在展示民间生活的过程中,既呈示出艺术思想的平民气息,也推动了中国非正统礼乐文化--世俗艺术的发展,同时更将审美标准由传统的“温柔敦厚”发展为平民的泼辣谐谑、洒脱直率,将艺术创作由传统的“经世致用”发展为张扬“情欲”、抒写性灵,将艺术功能由传统的“匡世济时”发展为观照生活、自娱自适,彰显出元代艺术观念的世俗化倾向。
四、元代艺术的综合性与艺术观念的开放性
在艺术作品中,艺术形式是极其重要的因素,它既是表现作品内容的组织结构和表现手段,也是艺术作品外在形态的综合,是艺术内容的内在结构与外在表现的有机融合与统一。现代艺术学理论认为,艺术形式是划分艺术门类的标准之一,同时,不同门类的艺术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也会相互作用,“在所有艺术样式的形成和发展的现实过程中,两种对立的力量--互相吸引力和互相排斥力--相遇并相互作用。一方面,每种艺术样式独立自存的条件是制定出不重复的、只为它所特有的对现实的艺术掌握方式,这要求它’排斥‘其他所有艺术;另一方面,同其他艺术的经常接触迫使它掌握它们的经验,体验它们所制定的手段,而首先和主要的是寻求和它们直接结合、形成综合艺术结构的途径”。这种相互吸引,相互渗透的作用在古代社会就经常发生,“这后一种任务在古代混合创作中就曾经自发地得到解决,这远在人类艺术发展开始自觉地、为了创造艺术综合体而解决这项任务之前”,中国的元代就是这样一个艺术形式相互渗透、艺术门类趋于综合的历史时期。
苏联学者叶·查瓦茨卡娅在探讨中国古代美学问题时就曾经指出,中国艺术发展到元代“出现了一种艺术融合的趋势:雕塑变成绘画性的,而建筑变成雕塑性的”。走向综合的趋势确是元代艺术的一个显著特征,不止发生在雕塑与建筑领域,其他门类的艺术也都出现了交流综合的现象,而且,元代艺术的综合趋势除了表现为形式因素的相互渗透之外,还有着艺术门类的综合与不同文化的融合等现象,使得元代艺术在普遍意义上具有走向综合的发展趋势。艺术形式的相互影响、艺术门类的趋于综合与不同文化的渗透融汇,既彰显了元代艺术的综合性特质,也呈示出艺术观念的开放性特征。
元代艺术门类的趋于综合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元代的杂剧艺术。周贻白在《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中就将戏剧艺术称为一种“综合艺术”:戏剧,向有“综合艺术”之称,或亦名之为“,由演员们装扮剧中人物,用歌唱或说白等六项艺术直接或间接地相与联系,逐渐地相与融合。
在这种成熟的综合性艺术出现之前,原始歌舞、祭祀巫优,秦汉俳优、汉代百戏、魏晋角抵戏和隋唐歌舞和参军戏等形成综合艺术的各元素都是彼此独立地发展着的,虽然其中的某些艺术样式已经出现或集合歌舞、或集合表演故事等合流发展的趋势,却并未成为成熟的戏剧形态。直到北宋杂剧、南戏和金院本等一场两段的结构体制、五个行当的角色体制和曲牌联唱的音乐体制,以及时空转移、假定性、程式化的舞台手段的完全融合,才实现了中国古代戏剧艺术的成熟形态。而元杂剧之所以能够成就中国古代戏剧艺术发展史上的第一座高峰,并且成为一代艺术的标志,不仅因为戏剧艺术的扮演机制在此完全成熟:杂剧四大套的音乐体制、一人主唱的单本结构体制以及时空处理的表演手段和服装砌末等舞台机制也都获得完整实现;还因为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优秀的作家作品和演员及戏班,特别是文人阶层参与到戏剧文本的创作之中,更增加了剧本书学性,使得元杂剧终于发展成为一种融文学、音乐、舞蹈、说唱、表演、舞台美术与戏台建筑等多门类艺术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样式。
在“观念开放”的元代,融为一体的不同艺术门类也能够承载起不同内涵的文化因素,使得元代的戏剧艺术更体现出多元文化交相融汇的综合特性。例如元杂剧所唱的“曲”既吸收了唐宋大曲、诸宫调,也吸收了多种民间“里巷歌谣”的曲调;既有【阿那忽】、【也不罗】、【忽都白】等少数民族的曲调,也有【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等异域曲调,还有【华严赞】、【好观音】一类的佛曲等宗教音乐的曲调。再如元杂剧所念的“词”既有对古代乐府歌词传统的继承,也有对民间说唱艺术和当代歌词的借鉴;既有精致典雅的文人诗歌辞章曲文,也有幽默诙谐的市井乡下俗词俚语。“乐府语”、“经史语”、“天下通语”融汇合流,“文而不文,俗而不俗”。又如元杂剧所表演的舞蹈,既继承了胡旋舞、霓裳舞等古典乐舞,也吸收了滑稽、百戏等民间乐舞;既有“拜舞科”一类被美化为舞台动作的日常行为,也有“做战科”等具有武术色彩的舞蹈动作。
元杂剧之所以称“杂”,既包括胡祗遹所说“上则朝廷君臣、政治之得失,下则闾里市井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厚薄,以至医药、卜筮、释道、商贾之人情物理,殊方异域风俗,语言之不同,无一物不得其情,不穷其态”的复杂内容,也包括它杂糅多门艺术,融文学、音乐、舞蹈、说唱、表演、舞台美术与戏台建筑于一体的综合形式,还包括兼容文人文化、民间文化、少数民文化、宗教文化、异域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于一身的多元文化内蕴。
艺术形式的相互渗透,在元代的绘画艺术中也体现得较为突出。为了彰显寄寓情致、抒写性灵的审美观念,元人不仅将书法艺术引入绘画的创作之中,更吸收了诗歌艺术的审美意境,创造了诗书画合一的文人画艺术,并在吸收其他艺术形式于绘画创作的过程中,彰显了艺术观念的开放性特征。
赵孟頫是开元代书画新风的领袖人物,他的《秀石疏林图》不仅在笔法上实践了“以书入画”,更在笔意上创造了“石如飞白”的审美意境,并且在画上题诗“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进一步在理论上明确了“书画同法”的艺术创作观念。正因此,陈振濂将赵孟頫的《秀石疏林图》赞为中国绘画史上书画同源观念的“完整崛起”。与“以书法为画法”的创作主张异曲同工。元代艺术家们以抒写性灵、任情娱适为艺术追求,也将诗歌艺术引入了绘画之中,正如易顺鼎所言:“诗莫盛于唐,画莫盛于元,然唐人能诗者多不能画;宋人能画者多不能诗,惟元人兼而有之,能画者多能诗,能诗者多能画”,题诗于画可以说是元代文人画一大特色。
诗歌与绘画共同具有表达心声的审美特征,正是元代文人题诗入画的主要原因,在元人看来,画面题诗不仅可以彰显画意,更能传达出画面景物中所深蕴而未能明确指出的意味,正所谓“清幽到处画不出,自遣数语人间传”。在蒙元入主的特殊历史时期,元代文人所承载的人生境遇是自文人阶层产生以来所不曾遭遇的,他们内心深处的情志意绪也更加深沉复杂,为了表达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特定心境下的意绪情志,元代文人经常在绘画中写入大篇幅的诗词题跋,并且借助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将诗词题跋融入整个画面的构图之中,与绘画一起营造出蕴藉深永的艺术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