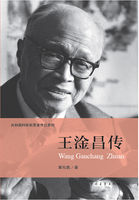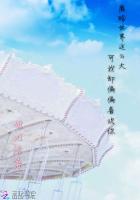不过,这同样是军统的人对她玩弄的骗术。两天后,余立教乘坐原来的车子回到安江,高高兴兴地从陈恭澍手里领走两百块白花花的银元。
第二天(二十二日),陈恭澍一路风尘仆仆驱车去执行第二项任务,当天晚上十点抵达湘潭。这里驻扎着国民党第九战区所属第十九集团罗卓英部的一个旅,因旅长石佛尊与陈恭澍是河北宁河县同乡,又是初中时代的要好同学,他就住在石佛尊家里。石佛尊于十天前收到陈恭澍自安江发给他的信,戴笠写给罗卓英的信也在同一个时候转到他手里,已知道陈恭澍的来意和自己肩负的责任。
“周佛海的母亲已被你们弄到息烽去了?陈学长!”石佛尊颇有兴致地问。“是的,还算顺利。”陈恭澍自鸣得意地微笑着,把如何将马老太太骗走的情况扼要说了说。“我的第二项任务的完成,全靠老同学帮忙了。”因他比石佛尊大三岁,故没有称他为“学长。”
“一定尽力而为。”石佛尊满口答应,“收到学长和戴先生的信之后的第二天,我就派出四个士兵化装,日夜潜伏在杨卓茂住处的四周,暗中控制他。”他顿了一会,“我的机要秘书朱理直,是杨卓茂的儿子杨惺华的内弟,近十天来,他去过杨家两次。朱理直第二次去杨家是大前天,杨卓茂告诉朱理直,说他第二天要去长沙看望一个在美国留学时的同学,那人已定居美国,最近从美国回长沙,写信给杨卓茂,说他回国后病了,不能来湘潭拜访他,邀他去长沙面晤。”
“杨卓茂去长沙了?”陈恭澍急了。
“没有,他被朱理直稳住了。”石佛尊说,“朱理直谎说日军正准备进攻长沙,将有一场残酷的战争在长沙展开,把杨卓茂吓住了,他没敢去。”“感谢老同学和朱先生鼎力相助。”陈恭澍满意地笑着,“我来湖南执行任务之前,去重庆待了三天,戴先生吩咐我,事情办妥了,由军统上海区拿出四千元法币,作为对老同学的酬谢。钱,我已经带来了。”他将搁在桌子上的小皮箱打开,从中拿出一包钞票递给石佛尊,“请你点一点,给我写个收据。”
“哎呀!我们是同乡加同学,协助你办点事还用得着拿报酬吗?”石佛尊心头一喜,但尽量用理智控制两只手不伸出去。“再说,这是事关党国利益的大事,我作为党国一名军事职员,也是应尽之责呀!”“老同学不必客气!有劳必有酬,理所当然,只是情重礼轻,请你原谅!”陈恭澍把钞票塞在石佛尊手里。“这怎么行?哎呀!这么多的钱,哪里还能说礼轻!”石佛尊心里热呼呼的,“再说,事情还没有办妥呀,现在怎么好收钱呢?”“有老同学的鼎力相助,事情的办妥,那是肯定的。请点一点,看是不是四千元。”“不用点,不用点,我还信不过陈学长!”石佛尊问,“用什么办法把杨卓茂弄到息烽去,请学长吩咐。”钱到了手,他的感情又深了一步。
“你怎么使用‘吩咐’二字来了?我们磋商磋商。”陈恭澍将自己准备冒充周佛海的秘书,拿着周佛海一家的合照和模仿周佛海笔迹的信件,说杨淑慧重病住医院,日夜思念父亲,周佛海特地派他秘密来湘潭,接杨卓茂去南京看望女儿的计划说了一遍。
石佛尊沉思一会,说道:“学长的意见值得磋商。”“欠妥?”陈恭澍眼睁睁地望着石佛尊。“是的。”石佛尊点点头,“一来,杨卓茂清华大学毕业后又留学美国,是个很有头脑的读书人,他不会像马老太太那样容易受骗;二来,据朱理直告诉我,周佛海考虑丁默邨的姨太太张艳容是杨卓茂的继室何芝俐的亲表侄女,曾经于今年五月上旬,让她带着他的亲笔信和他一家的合照,秘密来湘潭接杨卓茂夫妇去南京居住,却被杨卓茂拒绝了。这是张艳容离开湘潭回南京约一个月之后,杨卓茂透露给朱理直的。看来,杨老先生还很有爱国心和正义感,曾几次要朱理直写信劝杨惺华脱离汪兆铭汉奸政府。当然,朱理直这样做了,但杨惺华死心塌地,连信都不回。”他顿了一会,“因此,上个月九战区薛岳代理司令长官和罗卓英司令来湘潭时,还把杨卓茂夫妇接到我这里,与他们共进午餐哩!”
“噢,噢!”陈恭澍感到意外,“那么,老同学你说怎么办?”“让我想想,我们俩都想想。”石佛尊凝神沉思,那神情的确变成一尊石佛了。钞票,在石佛尊的智慧结晶体中,起到神奇的催化作用。很快,一个为陈恭澍极为乐意接受的意见便想出来了。
十二月的浓黑夜幕,笼罩在湘潭城区上空。下午五点多钟一断黑,就很难分辨出是上半夜还是下半夜,因为几乎延长到十四个小时的冬夜全是一片漆黑。寒气袭人,但没有风,到处是冷清清和静悄悄的。从城区东面流过的湘江河段,白天平静得像文静而缄默的少女,可是在这静夜里也能听到它日夜奔流的汩汩流淌声。这流淌声,像一首抒情诗,像一曲轻音乐,像阵阵喘息,像声声幽咽?这要看谛听者的心境了。
近来,杨卓茂心境不那么好。他原是上海的大富商。上海沦陷后,遭受到日本侵略者的种种敲诈勒索。如当时担任日本驻华中侵略军司令的松井石根,一次就从他手中索走了二百两黄金,土肥原贤二更甚,两次索走了他二百五十两黄金和二百二十万元现钞。他想到侵略者的贪得无厌,永远不会有满足的时候,今后松井和土肥原还会向他索取钱财。可以预见,将会有更多的日军高级将领向他伸手。因此,他于周佛海未投靠汪精卫抵达上海之前,也就是他年纪六十有六时,忍痛变卖了自己苦心经营近四十年的洋行恒产,带着继室何芝俐和两个保镖、一个女佣、一个轿车驾驶员回到湘潭老家。
老年人本来睡眠时间短,杨卓茂因心境不好,今晚十点上床,睡了四个小时就醒来了。不知为什么,近来他特别留恋在上海时那段黄金般灿烂的生活,也特别怀念死去的前妻。她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眼见日本人的巧取豪夺,又急又气又伤心,病情日趋恶化,使她提前离开了人世。如果不是日本侵略者打到中国来,他那日进千钞的大洋行怎么会舍得变卖?他贤惠的前妻又怎么会早逝?那湘江的流淌声,成了声声幽咽,句句哭诉!
这时,一阵紧急的敲门声,无情地把杨卓茂的依依思念之情打断了。他一惊,轻轻摇醒酣睡在自己身旁,比自己小三十岁的何芝俐。
“是土匪?”何芝俐睁着两只惺忪的眼睛,本能地轻轻惊叫一声,赶忙扭亮了床头的电灯,披上衣服。因为他们回湘潭近三年来,土匪已来骚扰过几次了。
一阵紧急的敲门声之后,有人叫喊:“请快开门,我们查户口来了!”“玉贵,振生!请你们去开门,警察局查户口来了!”杨卓茂半信半疑,他以为两个保镖未醒,边喊边捶了两下床边的木板墙壁。
睡在隔壁房间里的刘玉贵和喻振生早就醒了,并已经迅速穿好衣服,把手枪捏在手里,准备保卫杨卓茂夫妇的安全。两人听主人这么喊叫他们,都把手枪放在裤口袋里,答应了一声,一齐走出房门,扭亮阶檐下的电灯,走过足有一亩宽的嵌有青砖的地坪,来到四合院的大门口。
可是,门一开,冷不防冲进一个拿着手枪和四个端着冲锋枪的便衣武装,使两个保镖大吃一惊,“查什么户口,土匪!”两人这么想着,感到寡不敌众,身上的手枪没敢拿出来。便衣武装们对杨家的情况十分熟悉,一齐疾步向杨卓茂夫妇的卧室走去。两个保镖赶紧关上大门,紧紧地从后面跟上去。“请杨先生起来,我们要在你睡房里进行搜查!”持手枪的那人站在杨卓茂的卧室门口,砰砰敲了两下门。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要搜查什么?”杨卓茂惊疑地问。他已经穿上衣服,与妻子坐在皮沙发上。他年近古稀,但身体还可以,只是头发已经谢顶,两鬓和后脑勺的头发已经花白。
“我们是反共锄奸义勇队第五分队的行动小组,特地从长沙赶来,搜查你秘密勾结南京汉奸政府的罪证。”持手枪的说话瓮声瓮气。
“反共锄奸义勇队?哪有这个组织?”杨卓茂暗暗思忖着,“一定有人诬告!”但是,他很坦然,因为由张艳容带来的周佛海亲笔信和那张合照,他早就烧毁了。于是,他起身开门,淡淡地说:“请诸位先生进来搜查吧!”并且把书桌抽屉、立柜和保险柜的锁统统打开。
“你们两位负责搜查!”持手枪者手朝着两个年轻人指了指。
那两个年轻人把手里的冲锋枪靠墙壁放下,开始搜查。他们把抽屉、立柜和保险柜搜查了一遍,然后来到两个书柜面前,开始翻书。其中一人拿着厚厚的一本《辞源》翻了几页,忽然,他高声叫道:“搜到罪证了!《辞源》里夹着有大汉奸周佛海的信,信里还夹着周佛海一家的合照!”
杨卓茂和何芝俐暗暗一怔,但很快镇静过来,显得泰然自若,但两个保镖却以为主人闯了大祸,为杨卓茂夫妇捏了一把汗。
“拿来看看!”持手枪者神气地伸手把信和照片接过去。他将信和照片看了看,然后凶狠狠地递给杨卓茂:“你自己看看,这是不是你私通南京汉奸政府的确凿罪证?”
杨卓茂不慌不忙地戴上老花镜,将信和照片连看两遍,感到大惑不解,这信和照片是怎么来的?
信是用毛笔写在印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公用信笺”字样的红色直行信笺上的,信的内容大意是:汪精卫集团认为杨卓茂是德高望重的中国著名工商界人士,特地任命他为中央政治会议经济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考虑杨卓茂年事已高,可以住在湘潭不必去南京办公,只要求每月给中央政治会议写次信,对经济工作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杨卓茂的信每月由南京派专人采取,同时为杨卓茂送来月薪两千元法币。但要求杨卓茂从四月起,每三个月的月中,必须亲自赴南京一趟,参加例常的各专门委员会的正副主任会议。信的落款是“愚婿周佛海顿首”,“时间是四月四日”。
“信中说从四月起,每三个月的月中杨先生去南京一趟。那么,你在六月十五、九月十五、十二月十五共去了三次南京。”持手枪者把信和照片从杨卓茂手中夺过去,“现在你必须如实招供,每次去南京干了哪些祸国殃民的叛国投敌活动!”
“冤枉啊!天大的冤枉。”杨卓茂对周佛海的笔迹是熟悉的。他一眼看得出来,信中的笔迹有的有点像周佛海的,有的则很不像。他明知信和照片是这些不速之客有意带进来害他的,但他不敢直言,担心引起更大的麻烦。于是他气愤地说:“这不是周佛海的笔迹,是居心不良的人摹仿他的笔迹,捏造事实陷害我!”
其实,这是陈恭澍的笔迹。那持手枪者是石佛尊的副官梅固基,四个便衣是石佛尊手下的四个士兵。
“杨先生口喊冤枉,说这信不是周佛海的笔迹,那就请你把周佛海的真笔迹拿出来,对照对照,鉴别鉴别,好吗?”梅固基歪着身子,手抱着两个膀子,两眼斜视着杨卓茂。
“我与周佛海虽然是翁婿关系,但由于我与他走的道路不一样,早已势不两立!”杨卓茂申辩着,“我知道他叛国投敌以后,就将他过去写给我的信统统烧毁了!”
“是的,统统烧毁了,是我和他亲自烧毁的。”何芝俐边哭边做无效的证实。
“那只能说明杨先生夫妇在狡辩!”梅固基冷笑一声,“难道这张照片也是假的?”
信,杨卓茂有口难辩;照片,他无法否定。他感到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但是,他心中无愧,冷静地想了想说道:“我与周佛海的不共戴天,连薛岳代司令长官和罗卓英司令都十分清楚。”他把薛岳和罗卓英来湘潭时,请他共进午餐的事拿出来挡架,“诸位若不相信,石佛尊旅长可以作证。”
“是的,我也去了!”何芝俐抹着眼泪指着丈夫说,“薛代司令长官和罗司令还夸赞他,夸赞他是‘冰炭不同炉,薰莸不同器。’爱憎分明哩。”
“好吧!那就请杨先生和我们一道去见石旅长,如果他能够为你作证,我们马上送你回来。”梅固基脸上露出一丝笑意。
“行!我跟你们去。杨卓茂起身望着梅固基,请你坐我的轿车去。如不放心,还加一个弟兄同车。”
“可以。”梅固基手向一个中年人一指,“你与我同去。”
“穿上皮大衣。”何芝俐把狐皮大衣递给丈夫,“是冬天,又是深夜,冷哩!”
十分钟以后,杨卓茂等人驱车到了石佛尊旅部。车子一停,陈恭澍就高兴地走过来,与梅固基低声说了几句,就来到杨卓茂身边,说道:“鄙人名叫田宏德,是石旅长的副官。刚才听‘反共锄奸义勇队’的刘先生说,杨先生有要事找石旅长。可是,真不凑巧。今天下午三点,他接到十九集团军司令部的电话通知,马上带着机要秘书朱理直先生到长沙开会去了,三天以后才能回来。这样吧,明天早饭后,旅部派车由我和刘先生送杨先生去长沙见石旅长。”
“好,那还可以见到罗司令。”杨卓茂很高兴,想到还有罗卓英为他说话。
陈恭澍看看手表,说:“噢,只差三个小时就天亮了,杨先生不必回去了,就在我们旅部的客房里睡几个小时。”他手往亮着电灯的二楼一指,“客房就在楼上,请杨先生随我来。”
杨卓茂感到自己已经失去了自由,只好无可奈何地跟着陈恭澍上楼去。
“你就回去吧,”梅固基对杨家的轿车驾驶员说,“请你将刚才田副官说的情况转告杨夫人。杨先生问题一搞清楚,我们就派车送他回去,请杨夫人放心。”
现在,陈恭澍和梅固基坐在石佛尊家里,将下一步的行动方案研究了一会。末了,陈恭澍拿出两百元钱来递给梅固基,笑着说:“梅副官和四个弟兄辛苦了!这两百元钱梅副官得一百元,四个弟兄每人二十五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