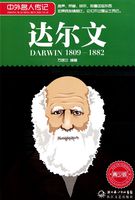“不敢当,不敢当!”梅固基迟疑了一会,“这一百元钱只能给石旅长。”他把钱塞在石佛尊手里。
“好吧!这一百元钱就算我和陈先生两人送给你的。”石佛尊又将钱塞在梅固基手里。
第二天早晨,石佛尊与罗卓英通了电话。罗卓英告诉石佛尊,戴笠已于两天前从重庆到了息烽间谍训练班,他为了早日控制周佛海,也是考虑杨卓茂过去的身份和社会地位,要罗卓英派飞机送杨卓茂去息峰。罗卓英想到这件事的来头是蒋介石,自然满口答应。
上午八点三十分,杨卓茂怀着问题将很快获得解决的愉快心情,登上旅部的军用吉普,与陈恭澍和梅固基去长沙。可是,到了长沙,并没有去十九集团军司令部,而是去了长沙机场,一种受骗上当的懊悔和大祸临头的恐怖油然升上心头。当陈恭澍和梅固基强行将他推上飞机时,他放声痛哭起来。直到飞机进入湘西上空,他才停止哭泣,再一看,飞机里不见梅固基,只有陈恭澍坐在他的身旁,用惊疑的目光哆哆嗦嗦地问:“你,你不是石旅长的副官!你到底是什么人?你要把我送到哪里去?”
“飞机一着陆,杨先生一切都明白了。”陈恭澍淡淡一笑。
杨卓茂无可奈何地深深叹口气,感到问也无用,只好听天由命。
三个小时以后,飞机在息烽机场着陆。杨卓茂正惶惑不安地向舷窗外张望,判断自己到了什么地方时,忽然,一个亲热的声音传过来:“杨伯伯!您老人家受惊了!”
杨卓茂扭过脸来一看,是戴笠上来了。周佛海在蒋介石身边担任要职时,他在女婿家里多次与戴笠见过面,戴笠还热情地请他吃过饭。他望着戴笠,似乎一切都明白了,又似乎更加糊涂了。他惊叫一声:“戴先生!”
戴笠手指陈恭澍,说道:“陪同杨伯伯同机来的这位是陈恭澍先生,军统上海区区长。他之所以原来没有向您说明他的真实身份,也没有直说请您来贵州息烽,都是我的主意。杨伯伯要骂,请狠狠地骂我;要打,请重重地打我!我毫无怨言。”他一副负荆请罪的神态。
“你们这是玩的什么把戏?把我弄到息烽来干什么?”杨卓茂很生气。“等会再详细向杨伯伯汇报,您老人家一路很劳累,请先下飞机休息吧。”戴笠显得感情真挚地说。接着,他亲亲热热地与陈恭澍各挽着杨卓茂一只胳膊,搀扶着他走下飞机舷梯,然后乘坐轿车去间谍训练班。
戴笠安排杨卓茂的住房与马老太太一样,有卧室兼书房、客厅兼餐厅和卫生间的三大间窗明几净、光线明亮、墙壁洁白的房子。摆设在各个房间的家具,也与马老太太使用的一样精美。不同的,马老太太识字不多,书架上的书刊少了一点和俗了一点。戴笠和陈恭澍陪同杨卓茂一进入房间,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好比这房间里的主人一样和蔼可亲地从卧室里端来了高级点心、香烟和茶。
“杨伯伯!您在息烽期间就屈住在这里。抗战时期,条件不好,敬请原谅。”他手指正在泡茶的姑娘,“生活上由她伺候您老人家。我们一定想方设法让您老人家吃好,睡好,玩得也好。余碧英,你要好好服侍杨爷爷!”
“我一定像伺候自己的亲爷爷一样伺候他老人家,请戴老师放心。”余碧英甜甜地笑着。戴笠兼任息烽间谍训练班的班主任,她是第十期结业的学员,故这样称呼戴笠。戴笠派这个女特务伺候杨卓茂,更重要的是监视他的言行。
“戴先生把我长期软禁在这里?”杨卓茂一怔。
“不能说是软禁吧!”戴笠一阵语塞,“当然,见仁见智,这是杨伯伯的认识。至于是不是长期让您老人家住在这里,很难说。”
“很难说?”杨卓茂反感地说,“如果戴先生真的还与过去一样尊重我为杨伯伯,尊重我为长辈,那么,你就应该把你很难说的话坦率地说出来。”
“好吧!我说。”这正是戴笠所期望的。他顿了一会,示意余碧英离开,然后对陈恭澍说:“请陈先生去把周佛海先生的母亲马妈妈请到这里来,有些话,我面对两位老人一起说。”“周佛海的母亲也被你们弄到这里来了?”杨卓茂心往下一沉,感到问题的严重,又设身处地感到马老太太的可怜。
“是的,马妈妈比杨伯伯早来两天。”戴笠说,“听她老人家说,你们两个亲家还互不认识。现在,在这么个特殊环境让你们两亲家见面,着实感到遗憾。唉!这叫作历史的捉弄吧!”
“是你们捉弄我们!”杨卓茂很气愤。戴笠并不生气,却满面笑容说:“其实,我们这样做,也是从眼前这段特定的历史,或者说是从眼前这个特定的时代考虑的,是出之不得已呀!”
杨卓茂还想发泄一通,满脸憔悴的马老太太已出现在眼前。她住在这栋房子的西头,听陈恭澍说请她去见一位亲戚,揣摩着这位亲戚是谁,快步走过来了。杨卓茂一见到这位因生活的折磨仿佛已年过古稀的亲家,一种特殊的感情促使他赶忙起身。
“马妈妈,这位就是周佛海先生的泰山……”戴笠怕马玉凤不懂“泰山”这个词的含义,马上改口说,“是周佛海先生的岳父大人杨卓茂老伯伯。”“是亲家?噢,您也来了!”马玉凤感到意外,心里一怔,满腹酸楚,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是的!亲家,我也来了!”杨卓茂也痛哭流涕,双手握着马玉凤那粗糙如树皮的手。“怪只怪我不该生了明凡,哦,生了佛海这个祸胎,连累了亲家,也把您老人家害了!”马玉凤以泪眼望着泪眼。“亲家!不怪您,不能怪您!”杨卓茂心情十分难过,“怪只怪佛海自己不争气,也怪我女儿淑慧与佛海臭味相投。”
“亲家!我没有与儿媳见过面,但佛海写信告诉我,由于您老人家的家教好,淑慧很能干,很贤惠,书也读得好,是个好媳妇,怪只怪我那个祸胎!”马老太太自责道:“老话说:‘夫唱妇随’哩,不能怪淑慧呵!”
“亲家!我女儿并不贤惠,也不是佛海的贤妻,因为她没有阻拦佛海离开重庆呢!”杨卓茂的话是真情。戴笠见两亲家说得差不多了,示意陈恭澍扶着杨卓茂坐下,他自己扶着马玉凤坐下,又亲自给马老太太泡了一杯茶。“好吧!现在请戴笠先生说说吧。”杨卓茂终于从痛苦中挣脱出来。“好,我说。”戴笠一本正经,“我们让杨伯伯和马妈妈来这里,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挽救周佛海先生。”他略一思索,感到还是把蒋介石抬出来为好,“我们这样做,是征得蒋委员长同意的。过去,蒋委员长一直器重周先生,现在,他一直关心着周先生。他对周先生近三年来的失足,感到十分痛心和难过。”戴笠也是一副痛心的样子,仿佛说话的就是蒋介石。“为了挽救周先生,蒋委员长同意让两个老人到息烽来,让周佛海先生和杨淑慧女士来一次震惊,来一次猛醒,然后毅然决然叛离南京,重新回到蒋委员长身边去。蒋委员长是宽宏大量的,他多次对我,对许多中央要员讲过,只要周先生弃暗投明,他不咎既往,仍然与过去一样器重他,栽培他。”他边说边注视杨卓茂和马玉凤的脸部表情,见两个老人脸上有几分体谅和欣慰。下边的话因高兴而带着激动的颤音,“我想,等两位老人休息两三天之后,给周先生夫妇写封信,说说你们的近况和来这里之后的生活起居,规劝他们速战速决,采取果断措施,尽早返回重庆。”他望着愁眉开始舒展的杨卓茂,“刚才我说两位老人是否长期住在息烽很难说。所谓很难说,就是不知道周先生夫妇是当机立断,还是优柔寡断,抑或是死心塌地地跟随汪兆铭走到底!”
“好,好,我理解,戴先生!感谢你和蒋委员长的一片好意。”杨卓茂一副大彻大悟的表情,“这样吧!我和亲家马上给佛海和淑慧写信,规劝他们回心转意,弃暗投明!”他显得急不可耐,巴不得快点离开息烽回湘潭。其实,他想得太天真了。
“我肚子里无文墨,信,亲家您写,我在上面写个名字。我那歪歪扭扭的字,佛海他认得出来。”马老太太仿佛服了特效兴奋剂,满脸皱纹喜成了层层笑波。
“好,好,信由我写,请亲家签个名。”杨卓茂微笑着说,“我和亲家的信,用什么办法送到南京去?戴先生!”
“杨伯伯不用操心,我们会用特殊手段,将你们的信妥善而迅速地送到周先生手里。”戴笠说。
五天以后的晚上九点左右,在南京颐和路三十六号。在周佛海和杨淑慧的卧室里,好比战争刚刚结束的战场,到处狼藉不堪,还笼罩着硝烟尚未完全消散那样一种气氛。周佛海穿着的深灰色呢料西服,从左胸处的口袋起,往下撕破两寸多宽,布片挂在下边的口袋上,他的脖子上有几道被手指划破的血痕,左手捏着被咬破还在冒血的右手背,他像一只斗败的公鸡,垂头丧气地瘫坐在皮沙发上,他感到脖子痛,手背痛,下身也痛。坐在床沿上的杨淑慧披头散发,额头上鼓起两个鸭蛋般的包,她身上的墨绿色呢料夹旗袍下摆,从左大腿开衩处横撕到五分之四处再挂下来,好在是冬天,穿着过膝盖的肉色紧身短毛线裤,大腿没有露在外边。她呜呜咽咽地抽泣着,越哭越起劲,浑身上下抽搐着。
事情似乎已经过去,但那丑陋而难堪的一幕,仍然在夫妻俩的脑海里浮现。
那场恶作剧发生在一个小时前。昨天下午,周佛海告诉杨淑慧,说他要去上海税警训练班主持第三期结业典礼做报告,要三天以后才能回南京。今天晚上七点四十分,丁默邨来到周佛海家里,说特工总部于下午五点半,在南京中华门破获了一个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点,要向周佛海汇报有关具体情况。
“他不是去上海了吗?说是去主持税警训练班的结业典礼呢!”杨淑慧直言相告,“噢!丁先生不知道他去上海了?”
“周先生没有对我说。”丁默邨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我上午还向他请示过特工总部的工作问题。他是今天下午去上海的吗?”
“不!是昨天下午去的。”杨淑慧顿生疑惑,“丁先生上午还见到他?”
“噢!是我记错了,可能是昨天上午见到他。”丁默邨似乎意识到了什么,马上改口,“好,我走了,等周先生从上海回南京之后再向他汇报。”
丁默邨走后,杨淑慧想起丈夫拈花惹草,不仅情妇多,而且经常出进花街柳巷,已经三次住医院治疗过纵欲贪色的花柳病,对他的上海之行更加满腹疑团了。顿时,许多令她痛心疾首的事情,猛地从心底里翻腾上来。去年八月在上海,周佛海为了便于与越剧演员严似柳通奸,居然把她藏在他的书房里,五天后才被杨淑慧偶然发现;他与罗君强的妻子孔艳梅厮混已经三年了,至今难分难舍;女特务李玉英从重庆返回南京后,安排她在财政部当机要秘书,几乎每天都与她发生肉体关系,直到一个月前李玉英再秘密潜入重庆为止;李玉英走后第四天,周佛海又从武汉特工人员训练班的学员中,物色到比李玉英还要风流俏丽的陈良英,代替了李玉英。所有这些,杨淑慧怀着女性在性爱上绝对自私的心理状态,曾经当着这些女人的面臭骂过,也多次臭骂过自己的丈夫。然而,周佛海如同一只永远改变不了好吃鱼腥的猫,依然故我,而且一味狡辩,甚至矢口否定。
现在,杨淑慧如同万箭穿心那样痛苦。她心一横,这回非捉奸拿双不可!
她平常外出,都乘坐丈夫的轿车。她判断,那辆轿车肯定停在财政部的车库里。于是,她向女佣刘妈说了几句什么,就独自一人离开家里,叫了辆出租轿车直奔财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