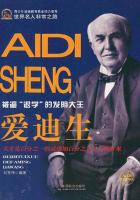安江,是湖南湘西群山环抱中的一座古老城镇,黔阳县政府和第十二专员公署设在这里。近来,在专署接待处住着两个中年男子,因无事可做,着实闲得无聊,每天不是进妓院玩女人,就是打麻将消磨时间。
“余立教先生!今天是十二月十五日,我们已在这里住了半个月,早饭后,你可以去邮电局给周佛海的母亲拍电报了。”说话的是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他望着墙上的日历,对刚刚起床正在洗漱的余立教说。
一个月以前,唐生明给戴笠写了封信,派女秘书张素贞专程送到重庆。唐生明在信中介绍了周佛海是汪精卫集团的中央常委、行政院副院长、军委副主席和财政部长,特工总部也控制在周佛海手里,他不仅是南京政府三巨头之一,而且是最拥有实权的人物。唐生明建议把周佛海控制在手中,而控制他最有效的措施是把他的母亲马玉凤和岳父杨卓茂,分别从沅陵和湘潭老家骗出来,然后将他们软禁在军统的一个什么组织里。这样,周佛海的鼻子就可以由军统牵着走。
唐生明的信,很快通过戴笠转到蒋介石手里。早在高宗武和陶希圣叛离汪精卫集团时,蒋介石就吩咐戴笠设法把周佛海拉过来,因为汪精卫的南京政府日益巩固,周佛海的叛国投敌更加死心塌地,使戴笠无从着手。因此,蒋介石对唐生明的建议大加赞赏,特地奖赏他五千元法币,并吩咐戴笠按照唐生明的意见火速行动。于是,戴笠就将把马玉凤和杨卓茂从家里骗出来的差事交给了陈恭澍。
陈恭澍从上海来到安江以后,由专署出面,指定凉水井乡乡长把周佛海的表弟、时任保队附的余立教带到专署接待处,以两千元法币把他收买过来,由他具体执行行骗马玉凤的任务。任务完成了,再赏他两百块银元。他们施行的骗术很简单,就是陈恭澍模仿周佛海的笔迹,给余立教写了封信,说有紧急要事,要余立教立即秘密赴南京一趟,以及附在信中的一张周佛海和妻子杨淑慧、儿子周愚海、女儿周慧海的合照。照片是一个月前,张素贞遵照唐生明的吩咐,利用拜访杨淑慧的机会,以留做纪念为由,向杨淑慧要来一张,再经过陈恭澍的复制洗印出来的。余立教回到沅陵,拿着信和照片去见马玉凤,这位识字不多而忠厚老实的老太太,果然信以为真,她叫着周佛海的小名高兴地对余立教说:“已经三年没有见到明凡的信和照片了。他把信和照片寄给你,也等于寄给我一样。立教你这回去南京告诉明凡,我也想去南京看看,等你从南京回来就陪同我去。明凡是我生的,我要他听娘的话,赶快离开南京回重庆去。”她巴不得立即见到儿子,急不可耐地问道,“你这一去大约什么时候打回转,我好准备点熏红薯干,明凡最喜欢吃的。”
余立教按照陈恭澍的吩咐,说道:“半个月左右。我从南京回到安江就给舅母拍电报。为了避嫌疑,我不说南京,就说我从长沙回来了,电报里的今天是指明天,上午是指晚上,去看望您就是去接你,电报这样拍,说明表哥同意你去南京。如果电报落款是个‘余’字,就是第二天动身,若落款是个‘教’字,请舅母做好一切准备,连夜出发。”
“记住了,我在家等你的电报。”马老太太连连点头。
因此,余立教与陈恭澍在安江渡过了半月清闲生活。眼下,余立教见陈恭澍吩咐他去给周佛海的母亲拍电报,含着满口牙膏泡沫问道:“这电报怎么拍?陈先生!”
“就按照你们事先约定的暗语,说你已从南京抵达安江,明天晚上去沅陵接他,要她做好一切准备,连夜与你动身。”陈恭澍又将注意事项和将马玉凤送往何处吩咐一番。
沅陵县凉水井乡有个小山村,因村前有条小溪流从群山之间流过,时隐时现,故名窝溪村,它就是周佛海的故乡。
十六日晚上,马老太太与周佛海的前妻郑妹和她生的儿子周少海、女儿周琼玉,以及周佛海的弟弟周佛深、妹妹周佛珍等一家老小,守着一盏昏黄的桐油灯光,默默地等待着余立教的到来。夜愈深,每个人神秘而胆怯,喜悦而依恋的感情愈深刻。
“噢!鸡叫了,冬月寒鸡叫半夜,怎么立教还没有来?”六十四岁的马老太太,提心吊胆地用福建蒲田口音悄声说,“明凡名声不好,我去南京的事该没有被乡公所的人发现吧?立教该不会在路上出什么事吧?”
她十九岁与时在蒲田县当典史的周夔九结婚,十二年后,因周夔九积极参与禁烟活动,得罪了当地一批贩卖鸦片烟的商人,他们用金钱买通了林则徐被革职后的继任两广总督,然后捏造事实,以贪污罪告发周夔九。周夔九感到强龙斗不过地头蛇,在他被拘留审查的当天晚上,解下裤带上吊死了。一个星期后,马玉凤在亲友帮助下,携带十岁的周佛海、八岁的周佛深、五岁的周佛珍,扶着丈夫的灵柩,无限悲痛地千里迢迢回到窝溪村,依靠十四亩水田和八亩旱地抚养三个子女。三十三年来,马玉凤在悲喜交集中由少妇变成老妪。她既为周佛海的聪明好学,成为凤毛麟角的日本留学生而自豪,又为他抛弃前妻与杨淑慧结婚,从此一连二十年来未回家看望过她而伤心。她既为周佛海成为蒋介石的红人,出任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而骄傲,也为他投靠汪精卫,使她成为大汉奸的母亲,在乡亲中抬不起头而痛苦。近两年来,她怀着一颗可贵的慈母心和崇高的爱国心,多次请人代笔给周佛海写信。规劝他弃暗投明,重新回到蒋介石身边去工作,可是信去如泥牛入海无消息。昨天下午,她终于收到余立教的电报,满以为真的有了去南京当面规劝儿子的机会,兴奋不已。今天清早起来,就将熏好的红薯干洗干净,又将它烤干包好,换上了只有外出做客才舍得穿的衣服,准备与余立教一道去南京。现在,已是深夜十二点过了,还不见余立教的踪影,她惴惴不安了。
“娘!立教拍来的电报别人看不懂,乡公所不会怀疑您将去南京。”周佛深安慰母亲说,“立教从安江来也不会出什么事,您老人家放心好了。如今兵荒马乱,汽车时开时不开,可能因此耽误了时间。”
郑妹蹑手蹑脚地在门外听了一会动静回来,又把窗帘布拉了拉,生怕有灯光透出去,然后对家里人说:“村子里的人家早就睡了,到处息息静静,只有凉水井西村那边有狗叫,可能是立教来了。大概是立教想到明凡名声不好,担心来早了出事,特意晚一点来接娘。”
她是周佛海的启蒙私塾老师郑靖华的侄女,读过几年私塾。她与丈夫是同年,十六岁两人成婚。她“烈女不嫁二夫君”的思想刻骨铭心,已经守了二十年活寡了,天不怨,地不怨,只怨自己命苦。
“郑妹!娘当着全家人的面再问你一句,如果明凡要接你去南京住,你对娘说句真话,去不去?”马老太太痛惜地望着因忧郁、孤寂和劳累的折磨,四十三岁仿佛年过半百的儿媳。
“有那个狐狸精在明凡身边,我才不去吃那份怄气饭哩!明凡对我没良心,我死也不见他的面。如今,背个大汉奸老婆的臭名声,就是去南京天天穿绫罗绸缎,餐餐吃海参燕窝我也不去。”郑妹说着说着,呜呜咽咽痛哭起来。
琼玉依偎在郑妹身旁,也一个劲地陪着娘哭。她为母亲的命运哭,也为自己的命运哭。三年前,她与一个国民小学的教师定了婚。父亲当了大汉奸的消息传到沅陵后,她被退婚了。现在已是二十二岁的大姑娘了,还找不到匹配相当的丈夫。一个月前,有人说媒让她嫁给一个比她大十岁的独眼龙,气得她要上吊!
“只望娘去南京后,直截了当地告诉明凡,儿女都受了他的害。”郑妹越哭越伤心,“琼玉二十二岁,少海二十了,都还没有成婚。大汉奸的女儿哪个敢娶,大汉奸的儿子哪个敢嫁来!”
“娘还要告诉大哥,因为他,县政府不给我们一家人发良民证哩!”周佛深怨恨地说,“如果将来日本鬼子打到沅陵来要逃兵荒,我们走投无路,只好等死哩!”
“唉!就连我这个嫁出去了的妹妹,也受连累让人看不起,我一家人也同样没有良民证。”周佛珍也很抱怨。
“我爹在蒋委员长手下当大官的时候,我没有沾到他半点光,连一分学费钱也不给,他的钱都给那个狐狸精花了。亏我娘省吃俭用,才让我高小毕业。”周少海怨声怨气,“如今,却沾上‘光’了,人家指着我的背皮,骂我是大汉奸的大少爷哩!”
“唉!都怪我肚子不争气,生了明凡这个祸胎。”马老太太深感内疚,也痛哭起来。这些平淡朴素而感情真挚的语言,不似檄文胜似檄文,是对祖国的叛逆者的有力声讨!
“都是我那个祸胎害了你们!不过,哭也无用。”马老太太停止哭泣,“郑妹不要哭了,琼玉也不要哭了。我到了南京,如果明凡不听劝告,我就痛骂他,痛打他,也为全家人出口气!”
老人说到这里,门外传来了狗叫声。接着,有人轻轻敲门。是余立教来了。
“立教!你大表哥南京那一家子都还好吗?”马老太太关切地问。母亲毕竟是母亲,她牵挂着呢。没等余立教回答,她又问:“明凡那一家子都欢迎我去吗?”
“欢迎,都欢迎您老人家去。”余立教满嘴谎言,“大表哥和外面那个表嫂、两个表侄都好。”周佛深见郑妹母子三人听余立教讲起周佛海的南京一家人,都痛苦地把头低下去,有意转过话题,问道:“你怎么挨到这个时候才来?立教!”
“找车,耽误了。想到舅母年纪大了,路途又远,乘坐客班车不舒服,特地托朋友在专署借到一辆吉普车,直接开往南京,又舒服又方便。”余立教说的吉普车,其实是陈恭澍从上海乘坐来的,“小车子停在马路上等我们,舅母都准备好了吗?可以马上动身吗?”
“可以,接到你的电报,说要连夜动身,早就准备好了。”马老太太两眼含着泪水与亲人告别,“大家在家要安分守己,不要胡作非为,也不要牵挂我,我顶多住半个月就与立教一道回来。”
老人哪里知道,她这是与亲人们诀别,永远回不来了。
接着,余立教提着那包熏红薯干走在前面,老人由周佛深搀扶着上了路。他们借着月光走了几里山路,黎明前到了公路上,然后由余立教陪同上车。
小车行进的方向与去南京的方向背道而驰。然而,从来未去过南京的马老太太,一切都蒙在鼓里。吉普经芷江、晃县进入贵州境内,第三天下午五点抵达息烽。这时,迎面走过来四个荷枪实弹的宪兵,其中一个高个子挥着手,气势汹汹地大喝一声:“停车!听候检查。”“喊停车的是什么人?立教!”马老太太诚惶诚恐。余立教自然很明白,但他却悄声说:“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您老人家不用害怕,但要注意,不管是什么人,千万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
四个宪兵走过来,高个子拉开车门,喝道:“车上的人都下来!”等马老太太战战兢兢由余立教扶下车来,高个子问:“你们两个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我们是湖南安江乡里的种田人。”余立教说,“我名叫李玉生,她是我母亲,名叫周金莲,我们母子俩去贵阳走亲戚。”
“有良民证吗?”另一个宪兵问。
“有。”余立教把两份事先准备好的良民证递过去。
“假的!两份良民证都是假的。”那宪兵说。
高个子走到马老太太身旁,故意将她打量一番,说道:“嘿嘿,我认出来了,老人家不是安江乡下人,是沅陵窝溪村人,老人家的名字不叫周金连,叫马玉凤,是吗?”
“不是,不是,老总认错人了。”马老太太更加惶然不安了。“的确是老总认错人了,她是我母亲,名叫周金莲。”余立教也假惺惺地矢口否定。“你还狡辩!”高个子啪啪给余立教两耳光,“她不是你母亲,是你的舅母,你不叫李玉生,叫余立教,是凉水井乡第五保保队附!”
马老太太见余立教挨了两耳光,感到心痛,浑身颤抖着面对高个子,哀求说:“老总不要打他,他的确是我的儿子,老总你的确认错人了。”她大惑不解,这高个子怎么会知道她和余立教的底细。
余立教想到两耳光换来了两千元法币,值得!但他却装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说道:“我不是余立教,也不是什么保队附,请老总调查。”“我们早就清清楚楚,还调查什么?”高个子高腔高调为余立教开脱责任,“你们大前天深更半夜从窝溪村动身时,我们就收到沅陵县政府的报告,告发你余立教与大汉奸头子周佛海有书信往来。这回,又亲自护送你舅母去南京,你自己也投靠南京汉奸政府当什么处长去!”他对同来的三个宪兵手一挥,“把吉普车扣押起来,把大汉奸的母亲和表弟扣押起来!”“我认了,我是窝溪人,我是马玉凤,我去南京是为了规劝儿子明凡,对,他在外边叫周佛海,我去规劝他离开南京回重庆,回到蒋先生身边去做事。”
马老太太哭哭啼啼,苦苦哀求,“老总行行好,不要扣押我和我的表侄两个!”
“你儿子在南京当了那么大的官,你还规劝他回重庆?我们信不过你!”高个子又神气地手一挥,“把他们押走!”
老人有口难辩,无可奈何地痛哭着,被宪兵们押送到半里外的军统息烽间谍训练班。
使老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是,到了训练班之后,这里的当官的都对她十分客气和亲热,不仅安排她住在陈设讲究的三间房子里,而且派一个年轻的姑娘伺候她。可是,对余立教却不同了,二十分钟以后,却给他来了个五花大绑,说是拉出去枪毙。大约过了五分钟,从左边山坡上传来了一声枪响,她放声大哭,为自己害了余立教一条命而悲伤,而痛苦,而内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