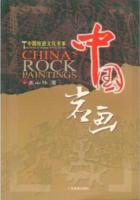古典音乐会鲜有报幕员禀报演出开始的,我们听众的谛听开始于演奏家们或弹出或拉响第一个音符。
每一个音乐家都有自己召唤观众的方式,郎朗一定会以以夸张的动作开始他音乐会的第一个音符。那天晚上,与斋藤纪念乐团合作的钢琴家是美国人彼得·赛尔金,曲目是巴托克的《第三钢琴协奏曲》。对照节目单上的介绍我算了算小赛尔金的年龄,已过花甲。你就可以理解了,为什么他触键奏响的第一个音符会那么低矮,一下子就躲到了云端里。可是,彩云追月煞是漂亮呵,所以,那么微弱的一声钢琴声,就让整个上海大剧院里只有他的演奏和同样低低地衬托着他的的斋藤纪念乐团了。小赛尔金少年成名,在21岁可以狂飙世界乐坛的时候突然销声匿迹。现在,我们知道他用了差不多10年的时间逃离西方世界浪迹于南美、中东,但他在彼时彼地做了什么,我们不知道。只知道他现在坐在钢琴前表达自己的方式不仅仅是用力量去触键。没有办法,不经过岁月的淘洗,你又怎么懂得控制远比放肆要难得多,尤其是呈现巴托克《第三钢琴协奏曲》这样差不多是作曲家临终嘱托的作品。
听过这场音乐会的下半场,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我相信了一种说法:斋藤纪念乐团是一支好乐队。他们在年仅27岁的指挥迪戈·马修斯带领下,层次那么清晰地将柴可夫斯基纠结的情怀一一展示,给我感触最大的,是乐队的控制能力。虽说迪戈·马修斯是阿巴多的助手,可我固执地认为27岁的年轻人是无法识见节制的妙处的,所以,我宁愿相信是斋藤纪念乐团的素质,以及大和民族的隐忍,让斋藤纪念乐团版的老柴《第四交响曲》成为我听过的最舒服的版本之一。你就看大鼓吧,为了不让声音多一点点,他一次次地扑向他的乐器——我听现场,难得注意管乐后面的人和事,昨晚这位大鼓,让我动容。
还让我动容的,是音乐会的曲目安排。
巴托克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想到自己这一辈子总是贫穷,而今又是病魔缠身,身无长物拿什么慰藉跟着自己一路受苦的妻子?于是,就开始写这部绝唱,《第三钢琴协奏曲》。
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人们提及这部作品总会想到老柴生命中的两个重要女人,梅克夫人和他的妻子。现在我们知道了柴可夫斯基的性取向,所以能够理解婚姻对他而言是一件尴尬而又痛苦的事情,可是,他妻子的痛苦又有谁知?柴可夫斯基还有梅克夫人做他的解语花,他妻子呢?都说老柴的《第四交响曲》是他最伟大的作品,他自己也屡屡感叹这是一部他最成功的作品,女人成就了柴可夫斯基,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通过这部作品来纪念一下他的妻子,一个以为自己得到了真爱后发现自己的真爱看得见摸不着的痛苦的女人?
其实,在音乐史上为女人创作的作品又何止这两部?李斯特因为卡洛琳·维特根斯坦而创作《节日之声》,已成音乐界的一段佳话。看样子,作曲家中虽鲜有女人的身影,但,女人与音乐的关系,是如影随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