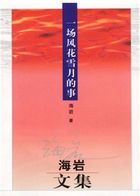枫垭坪,是这一带几十个大大小小村庄的总名称,其中枫垭坪村为最大的一个村庄。它四周有道像宽围墙似的土堤,有人说这是三国时代关云长驻扎过兵马的寨墙,又有人说是用来防山洪的水坝,也有人说是早年有钱人修来防土匪的工事。说来说去,因为年代已久了,谁也没有考证过,只是证明了这个村子很有些年代了。现在的这圈土堤已是高低起伏,坍塌残缺,上面七零八落地长着一些灌木和杂草。
土堤里,有上百户人家,他们住的都是青一色的干打垒的土墙、草顶或灰瓦顶的房屋。由于这里基本属于周围几十个村庄的中心,在交通不便利的情况下,人们需要购买一些油盐酱醋和杂货,需要用自己的农副产品交换一些生活的必需品,人们选中了这个离四周都近的地方。久而久之,这里就形成了一个物品交流中心,形成了一个集镇,加上国民党的乡公所设在这里,因此也有人把枫垭坪村称为枫垭坪乡,或枫垭坪镇的,但大多数人则是直呼枫垭坪。
乡公所在村子的最西头,其实就是一幢挂着乡公所牌子的单门独户的大瓦房和两间用来堆放杂物、关押“犯人”的小矮房,它紧靠着土堤边。堤外不远处就是山脚。
原来,乡公所里也养着十一二个乡兵。后来鲍显仁仗着有土匪撑腰,只要有事就可以叫土匪来帮忙,就干脆把乡兵全交给了熊武,让乡兵也当上了土匪,为“大布衫”扩充实力。
当刘秀北带着工作队员们来到乡公所时,已是天黑时分。他们没想到,鲍显仁已招集了十几个乡坤和财主打着火把在这里等候着他们。
鲍显仁一看到他们的到来。殷情地迎上前:“敝人是这里的乡长,你们远道而来,是贵客……贵客……欢迎……欢迎呐……”
刘秀北感到奇怪:“你们怎么知道我们今天要来?”
鲍显仁:“贵军攻克康阳城后,敝人已料到共军会派人来……早有准备,早有准备……”
刘秀北嘲讽地说:“那你还真有先见之明呐!”
鲍显仁尴尬地:“不敢,不敢……”
其实鲍显仁哪有什么先见之明。他是听儿子鲍元才估计的共军要来后,有些心虚,就特意安排人在康阳城通往枫垭坪的路上打探消息。今天看到工作队员真的来了,打探消息的人就赶过来向鲍显仁报告。鲍显仁一了解工作队员人数不多,就灵机一动,来个先礼后兵。他心里想,不管哪个朝代,什么人当了权,还能离开他们这些人?!再说,他还想摸一摸来人的底。
刘秀北指了指来的乡绅老财:“你们这是干什么?”
鲍显仁:“特地来欢迎你们。……这些都是敝地的头面人物。共军初来乍到,还需要他们的鼎力相助……”
刘秀北没好气地:“都散了吧!我们可担待不起……”
鲍显仁厚着脸皮:“这位想必是长官了,不知应该怎么称呼?”
一位工作队员横了他一眼:“什么长官?这位就是这个区新上任的刘区长。”
鲍显仁:“哦……刘区长……真是难得来到穷乡僻壤……敝人在寒舍准备了一点薄酒,请刘区长和你的部下赏光……贵部住的地方,敝人也在府上安排好了,请吧……”
“不必了!”刘秀北说着走进乡公所,他看了看宽大的房间,说,“我们就住在这里了……”
鲍显仁还不甘心地:“那怎么行……刘区长。太见外了……别人会说我鲍某不近人情……”
刘秀北:“怎么不行?!……收起你那套吧……我见得多啦!……同志们,进来吧,我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了……”
鲍显仁一听说工作队要在乡公所里住下,赶紧讨好地说:“贵军执意要在这里住……那看有什么需要的?我马上差人送来……”
刘秀北:“什么都不需要……我们自己都带着……”
鲍显仁试探地问:“刘区长。不知贵军要住多久?我们好有个照应……”
“既然来了,就不走了!”刘秀北说得十分肯定、坚决,“我们是来这里工作的,根本用不着你们照应。……我现在正式通知你,这里我们接管了!将作为一个区来管理。你这个乡长就到此为止吧……今后必须老老实实听从区政府的安排……”
一名工作队员把枫垭坪乡公所的牌子摘了下来,扔在了一边。
听到这一席话,看到乡公所的牌子被摘了下来,鲍显仁有些不知所措:“我……我这个乡长可是国民政府任命的……”
“那已经是旧皇历啦!”在一旁一直没有说话的丁俊山没好气地说,“这一带已经解放了,国民政府已经被推翻了……”
鲍显仁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他只觉得全身发冷,手脚冰凉。
刘秀北厉声地:“统统回去吧!……有什么事,我们会去找你们的……”
鲍显仁讨了个没趣,碰了一鼻子灰,只好带着乡绅老财们灰溜溜地走了。
轰走了地主老财后,刘秀北立即布置了岗哨。然后吩咐工作队员们找来一些麦草铺在乡公所的地上,再把各自的背包打开,把被褥铺在麦草上。他用手拍了拍:“很好嘛!比我预料的要好多了……我还以为今晚会睡在露天里呢……”
同志们都笑起来。
副区长丁俊山说:“我来为大家做饭……粮食和做饭的家伙我们自己都带着哩……自己动手,吃穿不愁……”
丁俊山四十来岁,原来是游击队的副队长。他个头不高,皮肤黝黑,身板健壮结实。饱经风霜的脸上布满与实际年龄不相符的皱纹、给人一种老成实在的感觉。他到这个区担任副区长,与刘秀北搭班子,是孙玉华经过考虑后精心安排的。因为他就是本地人,虽然家住在离枫垭坪村很远的一个山村,但他在这一带打过游击,对这一带情况很熟。刘秀北是北方来的干部,有地方工作的经验,只是在大平原上生活惯了,难免对山区的情况不甚了解,更谈不上熟悉这里的风土人情、各阶层情况。他们两人在一块合作,会弥补一些各自的不足,应该说是很合适的搭配。
刘秀北:“是啊!同志们一整天都在啃干粮,没吃一点热乎的东西了……”
丁俊山:“我来做。马上就好……”
刘秀北拦住了他:“老丁,让别的同志去做吧……咱俩把明天的工作合计合计……”
“好的。”丁俊山把做饭的活交待给了其他人,就跟刘秀北一起坐上刚铺好的地铺。
刘秀北:“你看看,刚才来的都是些什么人?……他们这分明是虚张声势,做给老百姓看的……让群众不敢接近我们……”
丁俊山:“这里的情况很复杂……刚才来的那帮人,没有一个好东西。尤其是那个什么乡长,他儿子就是山上土匪的头目,他们父子勾结,不知残害了多少老百姓,完全是一个十足的恶霸……”
刘秀北:“那我明天就带几个人去把他抓起来!”
丁俊山:“王书记要求我们要注意政策。我们刚来,第一阶段的工作主要是摸清情况……”
刘秀北:“这个乡长的情况不是明摆着嘛……”
丁俊山:“我看,先不要打草惊蛇。他早晚跑不掉……”
刘秀北:“既然我们来了,还怕什么打草惊蛇?”
丁俊山:“凡事千万不能太着急,一定要注意工作方法……”
刘秀北:“那好吧……你看,我们明天怎么开始工作?”
丁俊山:“还是按我们的计划,把人员分成两个队,分头开展工作。我带一个队先到较远的村庄去找群众谈谈,了解情况,然后由远到近。你带一个队就从这里开始把情况模清楚……我们争取尽快把这里的情况向县里汇报……”
刘秀北:“好!就这么办。”
丁俊山:“你一定要小心点……这里的群众已经被坏人搞怕了,可能还不敢接近我们……地主、老财可能还会出来捣乱……”
刘秀北:“我们在老区开展工作时,一开始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只要我们把地主老财打到了,群众很快就会站到我们一边,那我们的工作就好开展多了……”
丁俊山:“这里有些情况和老区还不太一样,土匪势力较大,各村匪属也比较多,我们人少,目前还比较孤立,要防备土匪的偷袭……”
刘秀北:“他们要敢来偷袭,得问问我手中的枪会不会轻饶了他们……”
两人都笑了起来。
回到家里,鲍显仁坐立不安。工作队员们的神情,特别是新上任的刘区长那咄咄逼人的目光,让他心里像插了一把刀,胆颤心惊。……真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他越想越可怕,毫无睡意,一个人在堂屋里来回踱着,不停地吸着旱烟。
“老爷。都大半夜了,你该回房睡觉了。”鲍显仁的老婆叶氏披着衣服从里屋走出来对他说。
“睡觉?……共军就在门外,能睡安稳吗?”鲍显仁没好气地说。他把胸中的气都撒在老婆身上。
“你不睡,我可要去睡了……”叶氏不高兴地转身欲走。
“慢着……”鲍显仁喊住了她。
“怎么啦?”叶氏问。
“我想了……我们决不能坐以待毙……”鲍显仁说,“我们得提前采取行动……”
“什么行动?”叶氏不耐烦地说,“你既然这么害怕他们,就马上派人上山,叫儿子带人回来把他们赶走就是了……”
“你懂个屁!这还不到时候……”鲍显仁生气地说,“共军敢派这么几个人到枫垭坪来,说不定是来探路的,大头还在后面……得看看情况再说……”
“那你说怎么行动?”叶氏也生了气。
“你听我说……”鲍显仁吩咐着,“明天你和家丁、家佣们都到村子里去,给穷鬼们先打个招呼,说共产党长不了,不要听他们的……谁要是敢跟工作队来往,‘大布衫’就会灭了他们全家……”
“好吧……该睡了……”叶氏打着哈欠回答。
桂子金为了防止共军登岛,一连数日,带着人马沿江搜寻船只。他知道共军要想登上野鹭岛,没有船只是不行的。他要把所有的船只都控制起来,能带回岛的就带走,带不走的就炸掉,他决不能给共军留下渡江的工具。
这帮穷凶极恶的家伙,连渔民用来打渔的小船也不放过。渔民们挺身护船,他们就开枪杀人。有一家三口,吃住都在船上,抢走了船,就等于砸了他们的灶,拆了他们的房。这一家就会流离失所。他们哪管那些,往船里扔进一捆手榴弹,将船炸碎,将这一家三口全部炸死……一时间,天昏地暗,搞得怀江上到处可见漂浮的断桅破板,到处可闻岸边渔民悲恸的哭声……
荷塘镇是离野鹭岛最近的一个大镇。桂子金不能不想到,也不会不来。他带着人乘船来到了荷塘镇的码头,他一看码头上正停靠着大大小小七八条木船,把手一挥,恶狠狠地命令着:“弟兄们。把这些船统统开回岛上去,绝不能留给共军!”
匪兵们听到命令后,如狼似虎地跳到码头上停靠的船上,挥着枪就把船上的人往岸上赶。船老大古水生和一帮船工、渔民们奋力阻止他们。许多船上的船工、渔民和匪兵们扭打起来。
桂子金一看这种不利的局面火了,他站上船头,掏出手枪对空中连放几枪。
人们一听到枪声都静了下来,瞪着眼睛直愣愣地看着他,有些不知所措。
桂子金假惺惺地大声说:“乡亲们——我桂某这样做也是出于无奈……共军要和我们作对,我只好暂时把你们的船全拖走,不能留给共军,不然会对我们造成威胁……等共军走了以后,我会还给大家的……”
“你这是放屁……”有个老渔民跑到自家的船头,冲着桂子金大声吼着,“你们就会欺负老百姓!有本事对付共军去……”
桂子金脚下的机枪响了,老渔民身中数弹倒进江里,转眼间被水流冲得无踪无影。各船上出现了骚乱。
桂子金恢复了凶神恶煞的面孔:“老乡们。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限你们半个时辰内马上离开船,不然老子就连船带人一起炸掉……”
船工和渔民们迫于国民党匪兵的淫威,只好收拾起铺盖或拖儿带女愤愤地离开了自己赖以生存的船只上了岸。
桂子金立即指挥着匪兵把码头上的几条船只全部抢下,然后用绳索把它们系在自己的大船后面。此时,他余兴未尽,并没有返回的意思,他还要上镇里去看看、去玩玩。
“弟兄们。想不想到镇子里去逛逛?”桂子金故意问着。
“想……做梦都想……”士兵们七嘴八舌地回答。
“那好!……弟兄这几天辛苦了,我现在就放你们半天的假……”桂子金大声说,“……让你们去镇上痛痛快快地玩玩……再把那好吃的、好喝的、好用的,给老子搬回船上来,带回去……不能留给共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