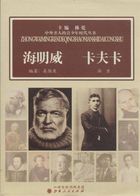许都城内街市的热闹与百姓的平和,让他忆起了上陆浑山时路过的平县,他感叹,即便是在乱世,只要有心,依旧能创出一个安泰之所。
三人边走边聊,不觉已到了司空府,荀彧上几步台阶,跟门丁耳语了一番,随后领着三人进了府。早有家仆前去通报,曹操这个时候正抱着曹冲读《孙子兵法》,以解秋乏,听说荀彧带着孔明先生来了,大喜过望,将曹冲交与通房丫头,不及换衣,只踩着木屐就迎了出来。
司马懿老远就听到曹操的笑声,等看到他本人时,不觉一乐,比起司马懿头回见他,曹操明显胖了不少,那双眼睛看上去更加小了。
曹操一心放在胡昭身上,竟没有注意到跟在胡昭身后的司马懿,直到胡昭走进内堂,向外头招招手,才看到有个小后生垂首立在门外。
“这不是洛阳令的二小子嘛!”曹操在主位上冲他招手,司马懿这才跨进门槛,走到胡昭身后,然后向曹操深深作揖。“河内司马氏诗礼簪缨之家,繁文缛节就是多,来人,给这位司马公子也备上一席,他旁边那后生,你也进来!”
曹操声音高亢,中气十足,即便是离内堂较远的地方,也听得见他的说话声。没一会儿,家仆双手端着两套席榻放到胡昭一侧。曹操随后面朝胡昭,直截了当地说道:
“先生莫怪,曹某已为先生在司空府预留主簿一职,参与军机,总领府事,先生愿屈就否?”
“荀令君对老朽言,曹司空知人善任,唯才所宜,今日得见,果真不同凡响,这也正是短短数年,曹司空麾下便聚集这么多大才高士的奥妙所在啊。”胡昭向倒茶的侍女微微点点头,以示谢意,“只是主簿一职,位重权高,世人常言‘三十年看儒书不如一诣习主簿’,曹司空高看老朽了。不过老朽此番并不是奔此而来,原本想劳烦荀令君带个话,但一想老朽心意怕荀令君难以传达,徒增彼此烦恼,便携两位愚徒,当面说与曹司空听。”
“哦?”
曹操端起耳杯呷了一口,转了转眼珠子。
曹操自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起兵,虽然遭受过诸多坎坷,几近丧命,但在获取人才方面,从没遇到困难,这里面大半的功劳要算荀彧,挟天子入许都,受封司空开府治事后,那些身怀一技,欲建功业的人更是纷至沓来。
因此,当他听出胡昭话里的意思后,觉得有些奇怪,莫非他真的如陈群所说,才过管仲,性似老聃?苦读圣贤书,练就文武艺,不就是为了闻达诸侯,以光宗祀吗?难道此人没有半点之念?想及此,曹操放下耳杯,朗声说道:
“先生是想拒绝曹某吗?”
“曹司空快人快语,老朽也不虚套。”胡昭直起腰身,“老朽就隐深山时,曾立下誓言,只做田园翁,不入公府门,平日以籍自娱,闲时便与这些后生谈天论地,倒也快哉。”
胡昭指指坐于自己下首的司马懿和蒋济。
“千古江山,金戈铁马,更适合年轻后生,老朽这等皮囊就莫再出来见笑了,况且老朽一介野生,无军国之用,即便入了公府,也只是浪费钱粮,空负了曹司空的美意。”
曹操瞥了眼荀彧,侧着脸,露出浅浅的但意味深长的笑容,胡昭端着茶碗吃茶,不看荀彧,更没正视曹操。蒋济一个劲儿地朝司马懿抛眼色,但司马懿全无理会,双手安于双膝,端坐席上。
荀彧略感心慌,招贤之事一向顺利,曹操看中的人没有不应的,这次却被胡昭当面拒绝,心中肯定不喜,说不定会大发雷霆,这要是传到外面,定会影响士人们的评断,进而影响他们的抉择。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曹操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张开他那张薄唇大嘴,大笑不止,边笑着边拿起自己的茶碗,来到胡昭面前,扫了几眼司马懿,说道:
“先生高逸,不是像曹某这等人物能理解的。”随后叹道,“曹某虽然仰慕先生,但从不强人所难,人各有志,出处异趣,强扭的瓜不甜,只要先生记得曹某慕贤求才之心,曹某也就知足了。”他饮尽杯中茶,将胡昭三人送出司空府。
此时,陈群、郭嘉已在府外恭候多时,原来,荀彧在进府前,吩咐门丁将今天休沐在家的二人请来府前,又差人回家,备下家宴。曹操揉着额头进去后,荀彧便将几人请到私邸欢宴。
途中,司马懿悄声对蒋济说道:
“荀彧办事周到,却又不着痕迹,曹操让他总领许都诸事,是找对人了。”
“曹司空得荀彧辅佐,天下事难说啊!”
蒋济口称“曹司空”而不是“曹操”,让司马懿很诧异,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想法,本打算细问,眼见就快到荀彧家,于是闭口不言。
荀攸出门迎候,众人随主人家绕过萧墙,穿行石砖铺就的甬道,往前再走片刻,便是正堂,有三级台阶,阶前冒着一些杂草,像是刻意留的。
大家上得台阶,脱下鞋子,走进正堂,荀彧推开二堂的门,将众人请入里间,食案已摆放妥当,宾主就座。
司马懿一路走一路瞧,虽说是当朝尚书令的私邸,但与温县老家的房舍比起来,不仅素旧低矮,而且还十分窄小,庭院自然也没家里宽阔,更别说栽有奇花异草。
荀彧先去沐浴更衣,回来时连连拱手,嘴上直说:
“招待不周,招待不周。”
“荀令君,方才我们老少正聊得高兴,被你这么一喊,竟扰了兴致。”
“先生取笑了,咱们吃茶还是吃酒?”
“在曹操那里吃了茶,这回就来点酒吧。”
惜命避祸虽也是人之常情,但几个弟子竟弃师而去,将胡昭平日的照顾与教诲抛于脑后,他心里必定是不好受的,如今眉开眼笑,谈笑风生,司马懿久悬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荀彧在自己位子上坐下,吩咐侍女倒酒,酒满杯,心满意,直到戌时方散。
辰时醒来,头还是有些昏沉,口干舌燥,不知道已经咽了多少口唾沫。
司马懿穿戴整齐,走出屋门,蒋济已在檐下练开拳脚,见司马懿出来,问道:
“你昨天说梦话了,你知道吗?”
“既然是梦话,我如何知晓。”司马懿问道,“我都说了什么?”
“就听你喊‘娘、娘’,你是想你娘了吧。我从小没爹没娘,是大伯一手将我带大的,唉,好几年没去看看他老人家了。”
被蒋济这么一说,司马懿似有些怅然若失,一会儿自我宽慰似的笑笑,拍拍蒋济的肩膀,喊道:
“走,给先生问安去。”
两人往左穿过一段回廊,看到胡昭住的屋子竟敞着门,往里一瞧,不见有人,心下想着会不会在正堂,过去一看,果然在里头,只是除了荀彧、胡昭,客位上还坐着一人。
那人眉粗额宽,目秀神清,面色如玉,鼻势丰隆,福相喜人,鼻下的胡须虽然有些稀疏,但并不碍观瞻,一对元宝大耳,垂落双肩,让人过目难忘。
在他身后站着两人,左边一个赤面长髯,风度不凡,右边一个白脸厚唇,器宇轩昂。正寻思这两人定不是凡品,那人已起身告辞,荀彧送客。
司马懿从廊柱后跳出,问胡昭:
“先生,那人是谁?”
“那人是刘玄德(刘备表字),中山靖王之后,当今天子的皇叔。”
“皇叔?”蒋济一惊,问道,“他是来探望先生的吗?”
胡昭点点头。
“他一早在司空府听曹操说起我正在荀彧家,于是就来看望。刘玄德仪貌俱佳,谈吐不凡,让人耳目一新,要不是他身上还有事,真想跟他再多聊聊。”
“他也是从长安一直跟随皇帝到许都的吗?”
荀彧送完客人进来,听到司马懿这么一问,解答道:
“刘玄德曾牧徐州,年初反被寄居的吕布夺了去,此后便来许都依附司空,司空表奏朝廷,任他为豫州牧。”荀彧说起刘备的事来,面带崇敬之色,“刘玄德虽屡遭坎坷,但心系汉室,令人感佩,多一个像刘玄德这样的忠烈人杰,天下何愁不安,汉室何愁不兴。”
众人点头称许,随后几人简单用过早饭,小叙了一会儿,告辞回山。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九月里的一天晚上,蒋济熟睡在榻,半张着嘴,看他那副模样,说不定正做着什么美梦。司马懿凑在油灯下,读完最后一行字,来到自己的榻前,摸了摸打着轻鼾的阿昭的脸蛋,熄灭灯,倒在榻上,合上眼皮,眼看就要睡着,突然“啪”的一声,虽然很轻微,但在万籁俱寂的夜晚,显得格外清晰。
司马懿睡意全无,抬头向上望去,那记响动分明就是从房顶传来的,有人在上头?什么人三更半夜地跑到山上来,还跳到房顶上?
他感觉不对劲,不走大门而上房顶,可以肯定决不是山上的人,然而却能在一片漆黑中穿过红石峡,摸到山上,定是有人指明了路径,那个人对陆浑山了如指掌。
那个人会是谁呢?
他继而想起当年在客栈的遭遇,急忙推醒蒋济、阿昭,与蒋济从各自的榻下抽出环刀,屏气凝神。发生贼人寇山一事后,学馆里每人都打了一把环刀,以作防身之用。阿昭双手抱腿,缩成一团躲在榻后。
咯……咯……
现在开始撬窗户了,蒋济握刀的双手微微颤抖,司马懿咬着牙关,看得出也相当紧张。少顷,司马懿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叫了一声,伸手点燃灯火,从墙上取下铜锣,“咚咚锵锵”敲打起来。蒋济也不管不顾地高声喊叫,学馆里随之锣声四起,喊声震天,并有几个同门跑到屋里。
这种由胡昭制定的自警方式,同样是贼人寇山后建立起来的,只在洞口立下一面木鼓远远不够。
也不知敲了多久,喊了多久,等众人停歇下来时,房顶上已没了任何声响,司马懿架上梯子,手持一盏灯爬到房顶,冲着下面的人摇摇头,胡昭拉着阿昭的手,站在众人后面,脸色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