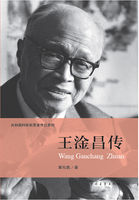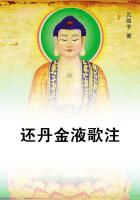中国古代科学发展至宋元时期达到高峰后,自明代开始,进入缓慢发展时期。作为思想家,王廷相对许多自然现象都进行过研究,并有不少创见。从近代科学的观点看,王廷相的研究主要是对自然现象的解释,缺乏系统的科学实验和观察,且他的解释带有较多的思辨性,因此只是属于古代意义的科学研究。但是,王廷相对许多自然现象的解释毕竟也包含有不少合理的成分,因而成为中国古代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天文历法
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发展至明代开始趋于衰退,天文学的研究主要在于对以往天文学理论和观点的阐释发挥。王廷相对天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宇宙结构的探索、对天象的观测和解释、对岁差的分析等三个方面。
(一)浑盖合一论
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发展到汉代,在宇宙结构学说上形成了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三个主要流派。盖天说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商周之际,浑天说和宣夜说约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三种学说均在汉代趋于成熟。汉代的盖天说以《周髀算经》为代表,其基本要点是:天地均为拱形,北极星所在的位置是天顶,日月星辰均附在天上平转;当人们看不见日月星辰时,它们并不是转入地下,而是离人较远;太阳离人所在位置较近时,为昼,较远时,为夜。汉代的浑天说以张衡的《灵宪》为代表,其基本要点是:天是一个球体,地在天球的中部。张衡的《浑天仪注》进一步指出:“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汉代的宣夜说认为,天不具有形质,是无边无际的广袤空间;人所见的蓝天属视觉上的问题;日月众星依虚空中的气而悬浮和运行。
汉代之后,浑天说成为天文学宇宙结构论的主导,虽然在南北朝时期也曾出现过浑盖合一论。宋代的朱熹持浑天说,并以天球中气的旋转运动而使地得以浮空,克服了以往浑天说所谓地“载水而浮”的缺陷。
王廷相持浑盖合一论。他说:
《周髀》之法,谓天如覆盖,以斗极为盖枢,今之中国,在枢之南。天体中高,四旁低下,日月旁行绕之,其光有限。日近则明而为昼,日远则暗而为夜,恒在天上,未尝入地,但以人远不见,如入地耳。盖器测景而造,用之日久,不同于祖,术数虽在,多有违失,故史官不用,遂失其传,其理实与浑天无异。《南史》曰:“浑天覆观,以《灵宪》为文;盖天仰观,以《周髀》为法:覆仰虽殊,大归一致。”是也。《王氏家藏集》卷三十四《玄浑考》。
王廷相认为,盖天说与浑天说在实质上是没有差异的。因此,他认为南北朝时期的浑盖合一论是正确的。同时,他还以浑盖合一论解释各种天文现象。
关于天是否有质体的问题,无论盖天说或是浑天说,都认为天是具有形状的质体。而宣夜说则认为天不具有形质。对此,王廷相说:
天体正圆,半在地上,半在地下,北极为枢,自东旋西也……天之形远不可测,观经星不动,乃知有体耳……观三垣、十二舍、河汉之象终古不移,非有体质,安能如是?《王氏家藏集》卷三十四《玄浑考》。
这是认为天有形状,有质体的。对于宣夜说的天不具有形质的说法,王廷相持否定态度。他说:
愚尝验经星河汉位次景象,终古不移。谓天有定体,气则虚浮,虚浮则动荡,动荡则有错乱,安能终古如是?自来儒者谓“天为轻清之气”,恐未然。且天包地外,果尔,轻清之气,何以乘载地水?气必上浮,安能左右旋转?《内台集》卷四《答何柏斋造化论》。
王廷相认为,宣夜说所谓天为轻清之气,日月星辰悬浮在气中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他还说:“天运于外,无一息停,虚空之气未尝随转,谓地上皆天,恐非至论矣。”《内台集》卷四《答何柏斋造化论》。认为日月依虚空之气而运转“恐非至论”。需要指出的是,王廷相虽然主张天有质体,但是这并不等于否认宇宙无限。浑天家张衡认为天有质体,但他又在《灵宪》中说:“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汉代王充认为天地均为平面,因此天有形体,但又认为宇宙无限。王廷相虽认为天有定体,但是他又说:
天之体在外者,不可究测;在内者,可以数推理度……天体之外,运有南北东西,则不可得而知。《雅述》上篇。
这是认为在天之体之外还有无限的空间,世界是无限的。王廷相还说:
或曰“无穷”,既有形度,安无穷尽?或曰“有穷”,天际之外,当是何物?或曰“天外有天”,彼天之外,又何底止?夫人在天内,耳目所加,心思所及,裁量知识,亦止天内。覆帱之表,茫芴限隔,一言何施?何也?神识之所不能及也。《王氏家藏集》卷四十一《答天问》。
这是认为宇宙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就人在一定阶段的认识而言,人们看到天有形体,因而认为天是有限的;但是在天际之外,又有无限的空间,因而宇宙又是无限的。
关于天何以不坠、地何以不陷的问题,张衡在《浑天仪注》中说:“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这是浑天说对天何以不坠、地何以不陷的经典解释。王廷相持浑天说的说法,认为“天自是一物,包罗乎地,地是天内结聚者,且浮于水上”(《王氏家藏集》卷三十七《答孟望之论慎言》。)。大地在天内浮于水上。针对宋代邵雍所谓“天依附地,地附乎天,天地自相依附”的说法,王廷相说:
愚谓地附乎天则可,天依乎地则不可。何也?天乘气机,自能运,自能立,非藉乎地者;况地在天内,势不能为天之系属乎……今以理揆,天行健疾,有刚风生焉,故能承水不泄;地有洞虚之气,水不能入,故浮而不沉,观瓶盎倒浮水上可知也。天之转动,气机为之也。虚空即气,气即机,故曰天运以气,地浮以虚。《雅述》下篇。
这就是说,天乘气而能立,而不下坠;地有洞虚之气而浮不下沉。他还举例说:
硙之转于水,机在外也;匏之浮于水,空在内也。观此则天之所依可知。瓶倒于水而不沉,瓮浮于水而不坠,内虚鼓之也。观此则地所附可知。《王氏家藏集》卷三十四《玄浑考》。
关于日月星辰是否入地的问题,浑天说持肯定态度,并用以解释昼夜的更替;但是,这也产生了难以克服的致命弱点:一方面是大地浮于水上,另一方面是日月星辰绕到地下,那么当日月星辰绕到地下时,如何从载浮大地的水中通过呢?在这一问题上,王廷相持盖天说的说法。他说:
天左旋,处其中顺之,故日月星辰,南面视之,则自东而西,北面视之,则自西而东。北极居中,日月星辰四面旋绕,非就下也,远不可见也。日月星辰恒在天也,人远而不及见,如入地下耳。《论衡》曰:“日不入地,譬人把火,夜行平地,去人十里,火光藏矣,非灭也。”此语甚真。《雅述》下篇。
在这里,王廷相采用了盖天说的日月星辰未尝入地的说法,以克服浑天说的缺陷。他认为,日月星辰绕北极旋转,恒在天上,人们之所以有时看不见,是因为它们离人们远去,并非入地下。他说:“日月在天,似无一时而不相见,观月之受光可推。但人处卑下,于日月有见不见之时耳。”《王氏家藏集》卷三十七《答顾华玉杂论》。需要指出的是,在王廷相所述的盖天说中,北极星所在的位置被视作天极,他说:“北辰乃天体之中,观极星不动而众星四面旋绕,可知。”《雅述》下篇。这种说法还停留在汉代盖天说的水平。自汉代之后,许多天文学家都已发现,北极星所在的位置并非天极。南北朝时期的科学家祖冲之的儿子祖暅已测得北极星离天极尚有一度有余。宋代科学家沈括也测得北极星所在位置并非天极。当然,王廷相采用盖天说的观点,其目的在于说明日月星辰恒在天上,非入地下。王廷相用盖天说解释日月星辰恒在天上,因此在解释昼夜更替时,他并不采用浑天说所谓太阳绕到地下的说法。他说:
北辰乃天体之中,观极星不动而众星四面旋绕,可知。中国在天之南,日月之光有限,故光照之处则为昼,光不到处则为夜。明亦以次而明,暗亦以次而暗,非在一处而天下皆明也。然亦常常在天,非入地下……但人以眼所及见处为论,而不推及所不见者,故谓日入地下尔,其实不然。古以《周髀》之法论天,言天如覆盖,日月绕盖缘而行,正合予之所论。《雅述》下篇。
王廷相认为,昼夜的更替是由太阳绕天的北极旋绕时,离人所在位置的远近而决定的;太阳离人所在位置近,“故光照之处则为昼”;当太阳离人所在位置渐渐远去,则“光不到处则为夜”。这就是所谓“日近则明而为昼,日远则暗而为夜”(《王氏家藏集》卷三十四《玄浑考》。)。因此他认为,“非必日入地下,为地掩蔽而后为暗也”(《王氏家藏集》卷三十七《答顾华玉杂论》。),提出不必用日入地下来解释黑夜。在解释“日照三面而北面不照”时,他说:
七曜之躔,极外方,一昼一夜,旋转一周。近极则日躔当天体之高度,故昼日照三面而北面不照;远极则日躔当天体之低度,故昼日照南面而三面不照。所不照者,非日不历也,日远而低,人自不见耳……日月随极而转,夜不于北而何往?使极之下无人则已,有则必见日之环照而无夜矣。《雅述》上篇。
王廷相认为,“日照三面而北面不照”是由于太阳在天球近天极的高纬度旋转时,“日远而低”,人看不见太阳旋转至北面的情形,“非日不历也”。在这里,王廷相还指出,太阳在近天极的高纬度旋转时具有极昼现象,认为天极之下有人“则必见日之环照而无夜”。因此王廷相认为,并非日不照北面。他还举例说:
尝观夏至之时,日由东北方出,西北方入,自中国视之,其行度已在北。如此,以北虏阴山之际视之,当亦又更北矣。阴山之北,岂不又更北乎……观夏至前后,半夜时望北天,如日之将晓,与冬至半夜黑暗不侔,则日在北方明矣。但人去日远,不及见其光,而日光所及有限,亦自不能远及于人耳。《王氏家藏集》卷三十七《答顾华玉杂论》。
北方有国,日落煮羊髀,未熟而日已出。由此观之,彼国之日亦有北照者矣。《雅述》上篇。
在这里,王廷相用事实说明并非日不照北面,而是由于日照北面时,离南面的人较远,人看不见日光,且“日光所及有限,亦自不能远及于人”,因而误以为日不照北。
关于昼夜为何有长短变化的问题,王廷相认为,昼夜的长短变化是由太阳绕天的北极运行时,离北极的远近而决定的。他说:
经星、井、鬼近极,斗、牛远极,此南北两端,日黄道必经之处。日躔井、鬼之次,当天极高之体,且于人近,见日之度常多,故昼晷长。日躔斗、牛之次,当天最低之体,且于人远,见日之度常少,故昼晷短。《王氏家藏集》卷三十四《玄浑考》。
天体近极者高,远极者下。黄道横斜交络,故日行近极,则光之被子人者久,故昼长夜短而气暑;远极,则光之被于人者不久,故昼短夜长而气寒。行两极之中,则昼夜均而气清和。《慎言·乾运》。
王廷相认为,太阳运行至近极时,人见日的时间长,故昼长夜短;反之,太阳运行至远极时,人见日的时间较短,故昼短夜长。在这里,王廷相还解释了季节变化与昼夜长短变化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都是由太阳绕天极运行时离天极的远近所决定的。
从中国古代宇宙结构理论的发展看,汉代之后,浑天说一直占统治地位;但是,浑天说自身包含着欠缺之处,这就成为后来天文学家所要解决的问题。王廷相试图用盖天说中合理的成分来弥补浑天说中的不足之处,提出浑盖合一论,有其积极的方面。但无论如何,王廷相的浑盖合一论与浑天说一样,与科学的宇宙结构论相去甚远,而最终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而成为历史。
(二)对天象的观测与研究
在天象的观测与研究方面,王廷相对月亮、恒星或星座、流星等有过细心的观测和研究。
在对月亮的观测与研究方面,王廷相认为,月亮表面的暗斑是由于月亮本身具有杂质所致。他说:
月中暗黑,非地影也,质有查滓,不受日光者尔。月行九道,势有高下东西。果由地形,则人之视之,如镜受物,影当变易。今随在无殊,是由月体,而匪外入也。《慎言·乾运》。
这是认为月亮表面的暗斑并非地影所致。而在王廷相之前,宋代的朱熹认为,月亮“中心有少压翳处,是地有影蔽者尔”(《朱子语类》卷二。)。显然,王廷相的解释更为科学。关于月相,王廷相认为,月的盈缺是由月亮与太阳的相对位置变化而决定的。月光藉日,相向常满,人不当中,时而弗见。远日渐光,近日渐魄,视有向背,遂成盈缺。王廷相说:
月之晦、朔、弦、望,历于日之义也。月会日而明尽,故曰晦;初离日而光苏,故曰朔;月与日相去四分天之一,如弓之张,故曰弦;月与日相去四分天之二,相对,故曰望。《慎言·乾运》。
在解释日、月食时,王廷相说:
月食日,形体掩之也;日食月,暗虚射之也。日光正灼,积晕成蔽,故曰暗虚。观夫灯烛,上射黑焰,蔽光不照,足以知之。《慎言·乾运》。
在这里,王廷相用月亮掩太阳的说法解释日食,这属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传统解释。至于对月食的解释,早在汉代的张衡就在《灵宪》中指出:“当日之冲,光常不合者,蔽于地也,是谓暗虚。”认为当太阳光受到地的遮掩而不能合于月亮时,就会产生月食。宋代的朱熹则说:“火日外影,其中实暗;到望时,恰当着其中暗处,故月蚀。”《朱子语类》卷二。显然,王廷相沿袭的是朱熹的不科学的说法。
在对恒星或星座的观测与研究方面,王廷相于明武宗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八月作《夏小正集解》十二篇。《夏小正》是夏代记述四时变化的典籍,记载了一年中每月的物候、天象情况和相应的生产活动安排。就天象而言,《夏小正》提及一些恒星或星座,其中有:参、昴、南门、大火、织女、北斗和银河等;指出每月的月初黄昏或黎明时,这些星或星座所处的方位、出没、见伏或中天的状况,以及北斗星座柄斗的指向。王廷相在《夏小正集解》中对有关天象问题作了研究和阐发。其中在解“正月”中“初昏参中,斗柄县在下”时说:“斗魁枕参首,参中则斗柄在下矣,言斗柄垂下,所以著参中也。”在解“三月”中“参则伏”时说:“初昏时,参已西下而没也。”在解“四月”中“昴则见,初昏,南门正”时说:“孟夏之月,日在毕、觜之间,故旦则昴见……亢宿中南北两大星曰南门。《月令》:‘是月昏翼中,旦蝥女中。’今言南门正,盖后一舍中矣。”在解“七月”中“初昏,织女正东乡”时说:“织女三星在天纪东端,当斗柄之东,斗柄南指,则织女正东也。”在解“八月”中“参中则旦”时说:“仲秋之月,昏,牵牛中,旦觜觿中,觜一度,在参上,旦正参中也。”在解“九月”中“内火”时说:“大火入地下也。”在解“九月”中“辰系于日”时说:“氐、房、心谓之大辰。季秋日在房,大火之次也,故曰辰系于日。”在解“十月”中“初昏,南门见”时说:“定星方中,则南门伏,非昏见也。”等等。
在对流星的观测和研究方面,王廷相认为:“‘星陨如雨’,予尝疑之。今嘉靖十二年十月七日夜半,众星陨落,真如雨点,至晓不绝……所陨者,星之光气,星之体实未陨也。”《雅述》下篇。王廷相又说:
星之陨也,光气之溢也,本质未始穷也,陨而即灭也……陨而散灭者,光气之微者也。堕而为石,感地气而凝也,阴阳妙合之义也。上下飞流不齐者,陨之机各发于所向也,如进激而喷也。《慎言·乾运》。
在王廷相看来,流星的出现是“光气之溢也”,所陨者,并非星体,而是星之光气,而星之光气“感地气而凝”成为陨石。这种解释显然牵强附会。
(三)岁差考
岁差是指由于地球自转轴的运动而使冬至点(冬至时太阳在恒星间的位置)缓慢西移的现象。在中国古代,人们最初认为冬至点的位置在牵牛初度,是永恒不变的。汉初邓平的《太初历》认为冬至点在建星。西汉末的刘歆修《三统历》认为冬至点进退于牵牛之前四度五分。东汉的《四分历》将冬至点定在斗二十一又四分之一度。但是,汉代人并不知存在着岁差现象。直至晋代的虞喜,才明确提出冬至点有缓慢移动,并提出岁差的概念。他根据观测分析,认为五十年冬至点西移一度。南北朝时期的何承天认为岁差为每百年差一度。祖冲之将岁差概念引入历法的推算之中,并得到四十五年十一个月差一度的岁差数值。隋代的刘焯,在他的历法中使用七十五年差一度的岁差数值。唐代的一行,在《大衍历》中取八十三年差一度。元代的郭守敬,其《授时历》的岁差为六十六年八个月差一度。
王廷相曾撰《岁差考》一文,对岁差概念的提出以及历代天文学家对岁差研究的历史作了叙述。他说:
汉自邓平改历之后,洛下闳谓八百年后当差一度。当时史官考诸上古中星,知《太初历》已差五度,而闳未究。盖古之为历,未知有岁差之法,其论冬至日躔之宿,一定而不移……至晋虞喜始觉其差,乃以天为天,岁为岁,立差法以追其变而算之,约以五十年日退一度,然失之太过……至元朝郭守敬算之,约六十六年而差一度,算已往,减一算,算将来,加一算,而岁差始为精密。《王氏家藏集》卷三十四《岁差考》。
在叙述了岁差研究的历史后,王廷相又转到当时的现状,认为至今二百余年,台官推演,又多不合天道,识者往往奏请再改历元,以正岁差。对此,王廷相提出:“天,动物也,进退盈缩,未免小有不齐,一定之法,不可拘也……当时以为精矣,至今又复有差。然则一定之法,顾可拘执也哉?”认为以往所定的岁差值“不可拘也”(《王氏家藏集》卷三十四《岁差考》。)。他还进一步认为,定岁之法、定日之法、定朔之法、日月交食之法等,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与实际有所差失。因此,他说:
以天道不齐之动,加以岁久必差之法,欲守一定之算,夫安可得?是故随时考验,以求合于天,此为至当。《王氏家藏集》卷三十四《岁差考》。
在这里,王廷相通过对岁差研究历史的考察,以及对历法中各种推算方法的分析,进一步提升出“随时考验,以求合于天”的科学认识论原理。
二、地学与生物学
在地学与生物学方面,王廷相亦有所研究。他提出“寒暑由日进退”,否定“地有四游”之说,等等,反映了他在地学方面的研究。
关于大地的形成,王廷相以他的元气本体论进行解释。他说:
天者,太虚气化之先物也,地不得而并焉。天体成,则气化属之天矣……是故太虚真阳之气感于太虚真阴之气,一化而为日星雷电,一化而为月云雨露,则水火之种具矣。有水火,则蒸结而土生焉。《慎言·道体》。
他认为,天与地并非同时形成,而是天先形成,地为天形成之后的水火二气凝结而成。他又说:
先儒谓“太虚之气,轻清上浮者为天,重浊下者为地”,似是一时并出,仆乃著此以明其不然。盖天自是一物,包罗乎地,地是天内结聚者,且浮在水上。观掘一二十丈,其下皆为水泥,又四海环于外方,故知地是水火凝结,物化糟粕而然。《王氏家藏集》卷三十七《答孟望之论慎言》。
这就是说,大地是天形成之后水火二气凝结,物化而成,并浮于水上。王廷相还说:“四海会通,地浮于上,水虽日注,安得而盈。”《王氏家藏集》卷四十一《答天问》。认为正由于地浮于水上,所以水不断流入大海,而不溢。
关于寒暑的形成,王廷相说,他起初信守古人所说“阴阳升降,一岁寒暑之候”;后来,他仰观俯察,考见日躔之次,发现“日近极而暑,日远极而寒,故著为说曰:四时寒暑,其机由日之进退,气不得而专焉。”《王氏家藏集》卷三十七《答孟望之论慎言》。他还进一步论证说:
尝考之历家矣:其曰日躔某次立春,某次立秋,某次大寒,某次大暑,如持左券,不爽毫厘,岂非日有进退,而气之在两间者为所驱而变耶?何也?日,真火也,阳之精也。太虚之中,冲然皆气,上为日火所烁,则蒸然而暖,地气亦由此而达,故日近北极而暑生焉。及夫立秋之后,日渐南退,暑亦渐消,太虚清冽之气日渐以盛,故日至牵牛而寒生焉。《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九《与郭价夫论寒暑第二书》。
这是认为,寒暑是由于太阳在天球上运行时离北极的远近不同而造成的;太阳离北极的远近不同,则离人所在地的距离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导致寒暑。他说:
日,大火也,真阳之精也。人于木火,近之则热,况近真阳之火,有不热者乎……故日近而暑,则日远而寒,理不过此。《王氏家藏集》卷三十七《答孟望之论慎言》。
这是认为人所在地与太阳的距离决定着寒暑,远日而寒,近日而暑,四方都是这样的。王廷相进一步指出:
在极之南,则北多寒而南多暑;在极之北,则北多暑而南多寒;在极之东,则东多暑而西多寒;在极之西,则西多暑而东多寒,无疑矣。《雅述》下篇。
在这里,王廷相还认为,人所在地的寒暑日的多少与该地所处的方位有关;离北极近的地区,多寒,离北极远的地区则多暑;而这些状况都是由于“远日而寒,近日而暑”所造成的。对于所谓“阴阳二气自能消长,自能寒暑”,“寒暑之运,乃二气自为之,日不得与”之类的说法,王廷相批评说:
谓阴阳自能寒暑,何不脱另自为运行?何日近而暑,日远而寒,如影之随形,响之应声,不相戾耶?仆亦不须他证。《书》曰:“日月之行,则有冬夏。”以日月之行而得冬夏,则寒暑由日之运行致之矣,而又何疑乎?《王氏家藏集》卷三十七《答孟望之论慎言》。
王廷相还说:如果寒暑为阴阳二气所决定,则普天之下同此一气,热则同热,寒则同寒。但是为什么却是向南偏热、向北偏寒?又何至南有不识霜雪之人,北有不消冰雪之地?此其故何耶?这不过是日之行有远近,气有及不及之殊罢了。王廷相进一步指出:
日有南北之躔,故阴阳有寒暑。然寒而暖,暖而暑,暑而凉,凉而寒,其所由来渐矣,非寒与暑会于一朝也。若曰二气旋转坱圠,以胜负为寒暑,谓之阴阳必争,是以二气各相逞力拒斗,负者退而胜者主,非因日进退自然之数矣,然乎?今观大寒之时,暑气灭尽无遗,大暑之时,寒气闭藏无迹,如参伐大辰,了不相接,安得并立相激而斗?《雅述》上篇。
王廷相反复揭露用阴阳二气解释寒暑成因在理论上的矛盾,并以此反证用日之进退解释寒暑成因的正确。最后,王廷相认为,以阴阳二气解释寒暑成因的说法是“万古糊涂之论,原未尝仰观俯察,以运人心之灵,用体天地之化也”(《王氏家藏集》卷三十七《答孟望之论慎言》。)。王廷相用日之进退对寒暑成因的解释试图摆脱传统自然哲学用阴阳二气解释的束缚,对于科学的发展是有意义的。
关于大地的运动,王廷相否认所谓地有升降以及四游之说。宋代张载说:“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地虽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气升降其间,相从而不已也。阳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虚也;阳日降,地日进而上者,盈也;此一岁寒暑之候也。至于一昼夜之盈虚、升降,则以海水潮汐验之为信;然间有大小之差,则系日月朔望,其精相感。”《正蒙·参两》。张载以地的升降运动与太阳的升降运动解释寒暑的形成,甚至认为昼夜之间也有地的升降,并以此解释潮汐现象。对此,王廷相予以批评。他说:
地在天内,浮于水上,冬夏之平,犹一日也。儒者不达乎此,遂以日之修短,以地之升降隐蔽而然,误矣。《正蒙》曰:“阳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虚也;阳日降,地日进而上者,盈也;此一岁寒暑之候也。”自今观之,二气之通塞,皆日之进退主之。日,大火也,故近极而暑,远极而寒。寒则地气闭塞而不达,暑则地气畅达而发育,此一岁寒暑之所由也。若如《正蒙》所言,不惟寒暑不由于日,而日之修短亦不由于天体之高下,皆地之升降主之矣,可乎?《王氏家藏集》卷三十四《玄浑考》。
王廷相以日之进退解释寒暑的成因,认为大地“冬夏之平,犹一日也”,并以此否定以地之升降解释寒暑的成因,否定地有升降的说法。“地有四游”的说法早在汉代就已被明确地提出。纬书《尚书考灵曜》说:“地有四游,冬至地上北而西三万里,夏至地下南而东复三万里,春秋二分则其中矣。地恒动不止,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闭牖而坐,舟行而人不觉也。”对于“地有四游”之说,王廷相认为,“此缘地有升降相因而误者也”,并且说:
既曰“日之修短由于地之升降”矣,而日之行道,又有南北之殊,不以地有四游形之,则与地有升降为日之修短;未免相碍。故以立夏为南游,近日也;立冬为北游,远日也。今迹其说论之。《王氏家藏集》卷三十四《玄浑考》。
王廷相认为,“地有四游”之说是为了克服地有升降说的理论矛盾而提出的。他接着说:
其曰“春游过东三万里,夏游过南三万里”,周公测日,自阳城至日南一万五千里,而日在表下无景,况三万里,其星辰河汉之位次,宁不有大变移者乎?而北极、北斗、天汉之位次,其高下东西,未尝有一度之爽,所谓“四游三万里”之说,岂不谬乎?《王氏家藏集》卷三十四《玄浑考》。
显然,王廷相既否认大地有升降运动,也否认大地有平移运动。
关于地表的变化,王廷相虽然否认大地有升降、平移运动,但是并不否认地表的变化运动。他认为,山是古地结聚,观山上石子结为大石可知。“山石之欹侧,古地之曾倾坠也。”《慎言·乾运》。认为山是古地的运动变化而造成的。他说:“山有壑谷,水道之荡而日下也。地有平旷,水土之漫演也。高峻者,日以剥;下平者,日以益;江河日趋而下,咸势之不得已也夫!”《慎言·乾运》。“高陵深谷,地道本体。流水冲激,川谷以下,石亦崩裂,况尔疏壤?”《王氏家藏集》卷四十一《答天问》。“土是新沙流演,观两山之间,但有广平之土,必有大川流于其中可知。”《王氏家藏集》卷三十七《答孟望之论慎言》。认为地表的变化与水流密切相关。
关于各种气象的成因,王廷相说:
风扬尘土于下,濛雨自上而降,遇结而为霾。风之微不足以散雨,雨之微不足以敛尘,阴阳缓弱之气也夫。
雹之始,雨也,感于阴气之冽,故旋转凝结以渐而大尔。
阴遏乎阳,畜之极,转而为风。大遏则大吹,小遏则小吹。夏无巨风者,阳盛之极,阴不能以遏之也。阳伏于阴,发之暴,声而为雷。其声缓者,厥伏浅;其声迅者,厥伏固。冬而雷收其声者,阴盛之极,阳不得以发之也。时有之者,变也,非常也。
雪之始,雨也,下遇寒气乃结。
地气夜则郁达,故遇物而凝。清则氛氲,为霜,为露;浊则烟雾,为濛,为木稼。日高而散,风冽而不凝者,阴化于阳之义也。《慎言·乾运》。
在这里,王廷相以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解释霾、雹、风、雷、雪、霜、露等的形成。他认为,“阴乘乎阳,云升而雨,即地水之气,升云无穷,降雨无穷”(《雅述》上篇。)。在这里,王廷相又用阴阳二气解释云、雨的形成。用阴阳二气解释各种气象的成因可以追溯到秦汉之际,世代沿袭,几乎没有大的变更,而成为经典性的解释,王廷相基本上采用了以往的说法。但是,他对这种解释时常产生怀疑,正如他否定以阴阳二气解释寒暑的成因,他对以阴阳二气解释雷的形成也持怀疑态度。早在汉代的《淮南子》和王充,就已开始用阴阳二气解释雷的形成。直至宋代张载也说:“凡阴气凝聚,阳在内者不得出,则奋击而为雷霆。”《正蒙·参两》。朱熹说:
“阳气伏于阴气之内不得出,故爆开而为雷。”《朱子语类》卷九十九。对此,王廷相说:
雷,说者曰阴遏乎阳,不得出而暴裂者,此近理也。求其声之仿佛,迅而急者似矣;其缓漫而大,殷殷呼呼,引长而不绝者,皆不似焉。若曰阴阳搏击之声,此尤无谓。阴阳气也,安得搏击成声如此?余尝疑其为物之所为,乘云雨之时而出,或而交,或争而斗,但非人间可得而见者。《雅述》下篇。
王廷相对以阴阳二气解释雷的形成表示怀疑。他接着说:雷“或者乃龙之类所为乎?惜不知龙能声雷口火如彼麟否也,或别是一物乎?”似有非科学的东西。
王廷相的《夏小正集解》除了对《夏小正》中有关天象问题作了研究和阐发外,更多的是对其中有关物候方面的知识作了研究。物候知识是人们对自然界动植物与自然条件的周期变化之间所存在的关系的认识。对于《夏小正》中所涉及的各不同月份、季节植物的不同生长特性和动物的不同生活习性,王廷相一一予以明确注释;对诸家注解中的错误之处,则予以纠正;同时,还形成了他的物候思想。
首先,王廷相认为,不同月份、季节动物的不同生活习性与气候的冷暖密切相关。冬月水上冷而下暖,故鱼潜于水底。正月以往,日渐近北,水面渐暖,故鱼陟水上,冰未解而鱼已上。至三月愈暖,鱼则出游而浮于水面。不光单独鱼是这样,万物皆然。蛰鸟、蛰兽,冬藏而春见,蚯蚓冬结而春鸣,鸿雁秋南而春北。人也这样,冬则塞垧墐户,深藏以避其寒;春则露处野游,毕出以趁其暖。王廷相还举例说:冬季,“田间之鼠穴于地中”,春季“以地暖而出也”。《王氏家藏集》卷三十八《夏小正集解》。对于动物的生活习性与气候冷暖的关联性,王廷相认为,“此物理之必然者”,“皆性之不得已而然者”,因此他反对以阴阳之说解释动物的生活习性。《雅述》下篇。
其次,王廷相认为,在特定月份、季节里,某些动物的形态会发生变化。“鹰化为鸠,鸠复化鹰;田鼠化,复化鼠;兔以潦而化鳖,鳖以旱而化兔;鹞化为鹯,鹯化布谷,布谷复为鹞;鱼卵之化蝗,蝗子之化鱼,阴阳以时相胜,故交化也。雀入海为蛤,雉入淮为蜃,腐草为萤,老韭为莞,男化为女,女化为男,阴阳偏胜,故一化而灭,不复再化。蜣螂为腹育,腹育为蝉,蝉之子为绿蠓;粪壤为蛴螬,蛴螬为土蛹,土蛹为蝴蝶;松脂为茯苓,茯苓为虎珀,阴阳杂揉,故屡化而极。”《雅述》下篇。王廷相认为,许多动、植物因阴阳的变化而发生形态的变化;而这些相互变化又是在特定的月份、季节里发生的。因此,他赞同《夏小正》所谓正月“鹰则为鸠”,三月“田鼠化为”,五月“鸠为鹰”,八月“为鼠”,九月“雀入于海为蛤”,十月“雉入于淮为蜃”的说法。《王氏家藏集》卷三十八《夏小正集解》。并强调某些动物之间的交互变化。
再次,王廷相认为,某些动物生活习性的变化可以预示季节的变化。在《夏小正集解》中,王廷相提出见鸿雁之往来,则知寒暑将变之候。“燕蛰于山岩或悬岸之隙,春则起蛰,入人家粥子。始来也高飞,将去也高飞,惟粥子之时其低飞。故高飞者,始来将去之候也。”“盖大蝉身黑而声直,五六月先鸣;寒蝉身绿色,其声蝭然,今始鸣,故一名蝭,俗谓之秋凉。”
第四,王廷相认为,植物的生长也与季节的变化密切相关。这在《夏小正集解》中有大量的事例。如正月,韭“此时有露见者”;芸“至此月可采矣”;“梅杏杝桃,先生华者也”,等等。与此相关,农作物的生长也有相应的季节。如二月,“种早黍”;五月,“种菽黍糜”,等等。
王廷相继承和发挥《夏小正》的物候思想,把动、植物的生长、变化与季节、气候的变化统一起来考察。同时,他又反对对《夏小正》的思想作牵强附会的解释,而将季节变化中的反常现象与人事结合起来。他说:
尝谓《月令》之书,出于《夏小正》,成于周《时训解》,其日次、星中、东风解冻之类,皆以天时授民事,与《夏小正》义同,至当而不可易者。其反时令,则有大水、寒气、寇戎来、征夫多、沉阴、淫雨早降、兵革并起之类,即《时训解》所谓“风不解冻,号令不行;獭不祭鱼,时多盗贼;鹰不化鸠,寇戎数起”之类是也,此皆术士灾应诬罔之论,非圣人之所拟。《雅述》下篇。
显然,王廷相的自然科学研究和他的科学思想的形成与他的无神论思想是密不可分的。
三、音律学
音律学是古代声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研究乐器发音高低比率的学问。早在西周初期,就已经有了十二律和七声音阶(或五声音阶)。十二律,即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七声音阶,即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五声音阶,即宫、商、角、徵、羽)。如果以黄钟为宫,则七声音阶(或五声音阶)与十二律的配合关系如下:律名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今日音名cc#dd#eff#gg#aa#b七声音阶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春秋时期,已经使用三分损益法来确定管或弦的长短与发音高低之间的关系。《管子·地员》说:“凡将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以是生黄钟小素之首,以成宫;三分而益之以一,为百有八,为徵;不无有三分而去其乘,适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复于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去其乘,适足以是成角。”也就是说,先确定为基音的管或弦,然后乘以三分之二,或乘以三分之四,以确定另一律的长度,照此类推,直到得出比基音略高一倍或低一倍的音为止。
音律学在古代很受重视。王廷相对音律学也有颇深的研究,著有《律吕论》(十三首),还曾与一些学者讨论过音律学的有关问题,撰有《与范以载论乐书》、《与韩汝节书》、《答何粹夫》等。
关于十二律的数值,明代以前的音律学家大都以黄钟数为九寸,然后按三分损益法计算出其他律的数值。对于十二律的数值计算,王廷相说:
《汉志》以黄钟九三之法起十二律之周径。其长九寸,空围九分,径三分。九九八十一分,以九分乘之,实积得七百二十九分。以九分之寸为度,分厘丝毫,并以九论。是十二律制虽有长短,其径三围九,以空其中,皆然也。且寸九而三分之,皆参停而无余赢,故三分损益,皆得全数。制律之法,莫要于此。《王氏家藏集》卷四十《律吕论》。
王廷相也主张以黄钟为九寸,并根据三分损益法计算出其他律的数值;但他提出“以九分之寸为度”,也就是采用九进位制进行计算。他认为,采用九进位制可以得到较为精确的数值,而“以十分寸算之,则数有奇零,而大万大千之寸难以施巧,误矣”(《王氏家藏集》卷四十《律吕论》。)。采用十进位制,误差较大。以下是王廷相采用九进位制计算的十二律的长度参见《王氏家藏集》卷四十《律吕论》。与采用十进位制计算的十二律的长度之比较:
律名/按九进位制计算的数值/按十进位制计算的数值
黄钟9寸9寸
林钟6寸6寸
太簇8寸8寸
南吕5.3寸5.33333寸
姑洗7.1寸7.11111寸
应钟4.66寸4.74074寸
蕤宾6.28寸6.32099寸
大吕8.376寸8.42798寸
夷则5.551寸5.61866寸
夹钟7.4373寸7.49154寸
无射4.8848寸4.99436寸
仲吕6.58346寸6.65915寸
以上按九进位制计算的数值均为精确数值,按十进位制计算的数值只是取小数点后五位,除黄钟、林钟、太簇的数值外,其余均为近似数值。可见,王廷相提出的按九进位制的计算方法是有一定价值的。
关于五音问题,王廷相认为,五音本于人的自然声气。古人制作五音,不是无中生有,都是有所本的。宫本喉,商本舌牙,角本舌,徵本舌齿,羽本唇。故凡人呼而出声,不论歌唱言说,必自宫而徵,而商,而羽,而角。角者,气平之声,是音之最后了。因此,宫音始而浊,羽音极而清,落而收于角,清浊平。此声气自然之妙,非人力强而能为的。参见《王氏家藏集》卷二十八《与范以载论乐书》。在论及五音的相生之序时,王廷相说:
人之音声,随气而吐,故气呼而声出,必自宫而徵,自徵而商,自商而羽,自羽而角。角者,气平之声,音之终事也。故曰:发于宫,达于徵,返于商,极于羽,而收于角。盖声气自然之机理,非一毫人力可以强而为之者。圣人以五音在人,有序而不可乱如此,故像人之声气,以为制律之节度。是以宫动而徵应,徵动而商应,商动而羽应,羽动而角应。其五音以次相生,顺而不乱,古人声律之本旨如此,盖出于至和,而原于天机者也。《王氏家藏集》卷四十《律吕论》。
关于变宫、变徵问题,王廷相认为,五音之间又有变宫和变徵,这也是“神理自然之节度,非人力之所强合者”。他说:
律之作也,本于人声,故乐曲之奏,其声必自宫而徵而商而羽而角,则五音一周。然声气有抑扬高下之节。乐句初发之声,或抑或扬,其气皆平,一二句之后,声气必有极扬者。扬则宫徵皆清,非初发之宫徵,安得不谓之变宫变徵乎……故声气有抑扬高下,而五音之用有变宫变徵焉。《王氏家藏集》卷四十《律吕论》。
至于除宫徵之外的商角羽为何无变,王廷相说:
呼有声,吸无声。人气一呼,可当二律,扬以一呼再呼必平,抑以一呼再呼亦平,中有极扬者,乃变宫变徵也。宫徵相接,一呼而尽,再呼必平,平即原商羽角矣。此宫徵有变而商羽角之无变也,亦天机之妙自为之者。《王氏家藏集》卷四十《律吕论》。
关于旋相为宫问题。“旋相为宫”又称“旋宫”,是音律学中重要的概念,是用以表述五声音阶或七声音阶与十二律的相互搭配关系。在五声音阶或七声音阶中,可以以黄钟为宫音,也可以以其他律为宫音,从而构成各种音高的五声音阶或七声音阶。因此,从黄钟到应钟的十二律可以轮流作宫,这就是“旋相为宫”。关于“旋相为宫”这一概念,王廷相说:
人声之发,必起于喉,而达于舌齿,再呼而换气,必返于舌本及腭,而极于唇与舌中,是七律旋转,皆可以为声始也。由是观之,不惟黄钟发声自喉始,或自林钟而及黄钟,或自太簇而及黄钟,或自黄钟而及林钟,其发声皆自喉始。喉者,宫之分也。故曰“旋相为宫”,非曰宫调十二,而商角徵羽皆十二也。《王氏家藏集》卷四十《律吕论》。
曰“旋相为宫”,言各律皆可作首也。如黄钟为主律,则必林钟为徵,太簇为商,南吕为羽,姑洗为角,其音以次而和。《王氏家藏集》卷二十八《与范以载论乐书》。
但是,按照三分损益法所计算的十二律的数值,其相邻两律间的比不完全相等,被称为十二不平均律,因此,在固定音高的乐器上,实际上并不能实现旋相为宫。这一问题直到王廷相之后的音律学家朱载堉(公元1536—1610年)发明十二平均律才得以彻底解决。
关于律管的制作,王廷相主张以铜为材料,他说:
古者断竹为管,后世易以铜玉。自今论之,玉不可以多得,嶰谷之竹出自昆仑,亦非人力可以卒致。中国之竹,其空围之度,岂能恰好悉与律合?不如范铜易施其巧。《乐书》曰:“铜乃至精之物,不为燥湿寒暑变其节,不为风雨暴露改其形。其质虽殊竹,用以宣畅雅音,实与竹等。”是也。《王氏家藏集》卷四十《律吕论》。
至于制作过程,王廷相说:
欲制律,先卷他物为筒,使空其中,以中妇人手指之寸约量其周径之数,取上党羊头山之黍,择圆实者一千二百粒实其中而剪齐之,即以空中径三之数为法,量直长九寸之数。若长数得二十七径,则周径是矣。使太过,则径之度长,则再促之;使不及,则径之度短,则再衍之。如此参两周悉,务使长径之数相合,则律之大较定矣。乃实筒之孔以为范,而铸管焉。再以原黍实之如一,然后协之人声,较之周尺。声太浊,则稍为加短,不必以黍为拘,以尺为准。盖黍有丰歉大小之异,而尺有古今分寸之差故也。《王氏家藏集》卷四十《律吕论》。
关于律尺问题。音律涉及计量问题,需要研究律尺。王廷相著有《律尺考》,考察了律尺演变的历史。他说:
古人制尺以调律,累黍以定尺,然随代变易,讫无定准。《汉志》云:“律本起于黄钟之长。”以羊头山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黍,为黄钟之长。盖一黍约一分,九十黍九寸律也。此必上古以来有所传授,故历代因之,以定律尺之度。《王氏家藏集》卷三十四《律尺考》。
但他接着又说:“尺随代更,律随尺异,虽有慕古之君出而正之,终然不能归一。”他还列举了各朝代所使用的各种尺,并以晋朝荀勗(公元?—289年)依据《周礼》而制的所谓“晋前尺”为准,考察了其他各种尺的长度。他说:
按晋荀勗依《周礼》制尺,谓之晋前尺,与刘歆铜斛尺、建武铜尺、祖冲之铜尺、汲冢玉律尺,其度皆合……田父玉尺、梁表景尺加勗尺七厘,汉官尺加勗三分三厘,始平铜尺、杜夔尺加勗四分,浑仪尺加勗六分四厘,蔡邕铜龠尺加勗一寸五分八厘,元延明尺加勗五分八毫,开皇水尺加勗一寸八分六厘,刘曜土圭尺加勗一寸五分。《王氏家藏集》卷三十四《律尺考》。
王廷相还对造成各种尺的长度不同的原因作了分析。他说:
以为校黍,则黍有大小之异,累有长广之殊,黍不可尽信矣。以为定于人之声,则喉有长短之不齐,音有清浊之各异,声不可以尽依矣。故历代以来,尺之长短杳无定准,乐之高下茫无定声,拟议纷纷,率莫能决如此。《王氏家藏集》卷三十四《律尺考》。
至于制律时量度的确定,他说:
今之制律者,必曰“累黍定尺”,固无恰好符契之妙;若曰“弃黍为尺”,亦无持循默契之理。予谓先守累黍之法,以为律尺大分资藉之地,后参古人耳听心会之术,以为考声命尺之本,庶几所谓元声者必于此而得之。不然,止据区区累黍之法,以为定尺之要,恐未免毫厘之差,遂致千里之谬矣。《王氏家藏集》卷三十四《律尺考》。
他认为制律不能仅仅局限于累黍之法,而且还要根据人的听觉感受进行适当调整。
王廷相对以累黍之法制律提出疑义,有其合理的方面。后来的朱载堉也说:“累黍之法,名为最密,实为最疏。”朱载堉:《律学新说》卷二《审度》。因此,朱载堉转而采用数学方法。但王廷相却是在怀疑累黍之法时,提出辅之以“耳听心会之术”,不仅没能解决问题,反而有倒退之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