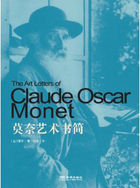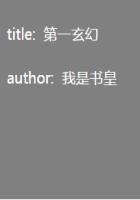二零零一年初,美国的eBay拍卖网上的一个祭蓝碗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个瓷碗约六、七寸口径,削足齐整,釉色特别肥润,碗底双圈青花楷书款:大明宣德年制。
几年前的eBay与现在不同。那时虽说假货也有,却也不时出现一些上眼的古董,这主要因为众多仿制高手当时尚未涉足eBay。有些美国人家里有了老旧的东西,弄不清什么价值,便放到eBay上碰碰运气。由于一般美国人懂中国瓷器的不多,在网上竞拍中国瓷器在数年之前也不多,我那时不需激烈竞争,也能拍下不少自己喜欢的瓷器。
现在的eBay网看了令人烦躁,成百上千的宋、元、明、清各代瓷器,尊,罐,瓶,碗,一应俱全,要什么有什么。通常起拍价只有九点九美元,让人不愿细看浪费时间。有兴致买这些东西的人,多半是为了放在家中做一般性的装饰观赏。真正收藏古瓷的行家和古董商,绝不会随便花几个闲钱买上一件凑个热闹。
上面说的这个祭蓝碗,照片拍得好,釉水光泽拍得清楚生动,造型看上去相当顺眼,卖碗的是亚特兰大市一位名叫肯福斯特的人。
与其他在eBay上卖古董的人相比,肯福斯特起价高,起拍就是五百美元,并注明底价尚未达到。这个价格,在初期的eBay上,实属少见了。另外,他对这个瓷碗的描述十分内行、详细。肯福斯特声称,这是中国十五世纪明代宣德朝烧制的皇宫用器,并说明了当时中国景德镇烧制工艺的水平和历史背景。
这个肯氏是什么人呢,中国人?美国人?我没有把握。但这个碗我喜欢。我将照片放大,仔细端详琢磨,似乎有这个把握:是个古瓷,不是新仿,远到宣德,近在康熙,于是我下了决心上网去竞标,待我出价方才发现,对此碗感兴趣的不止我一个,网上你来我往一番争夺。最后,我出价过千,高于所有其他竞标者而成为最高出价者,不料,却还是没有达到肯福斯特为这个碗设的底价。
没有赢下这个碗,不免叹息一番。可是我并没有太难受,也没太往心里去,毕竟未见到实物,也不知肯福斯特的底价高悬于何处。
拍卖结束后的一天,我发现卖碗的亚特兰大市的卖主发来一个电子短邮件:亲爱的最高出价者,您所感兴趣的这件瓷器,是个真品,感谢您出了最高价,如果您仍有兴趣的话,请与我联系。
这种情况,在eBay网拍上时而出现,卖主虽设有底价,只要最高出价与底价相差不远,也愿意私下成交。
我回信表示有兴趣,并询问底价究竟是多少。肯福斯特很快答复说,底价多少无所谓,就这个蓝碗的市场拍卖价而言,至少以万元计算,我的收藏不止这一件,你还是按照你原来的出价买下这个碗,看后不喜欢就退给我,没有丝毫风险。
我与肯福斯特互相不熟识,为了避免私下交易的风险,他与我约定,他将瓷碗再用“一口价”的方式重新列上拍卖网,我遂用他提供的链接信息将碗一举拍下。一个星期不到,邮件就到了我的手上。
打开严实的包装,取出层层包装里面的碗,放在灯光下认真地观察,仔细地抚摸,我觉得这碗上了手以后,比照片上更好。碗内外光泽鲜嫩,釉水肥厚欲滴,但以我的眼光,这应该是个康熙朝仿宣德年的祭蓝碗。
这个祭蓝碗釉厚若堆脂,首尾相衔的两条龙,用的是蓝中留白的画法,仔细观察可见龙身上有若隐若现的细小鳞片。康熙仿宣德祭蓝仿的有模有样,就手上的这件而言,可谓是惟妙惟肖,品相和手感皆为上乘。只是,康熙朝是断不能烧制出宣德窑瓷器的,年代不同,瓷土不同,柴火不同,烧制工艺不同,无论怎么像,到底只是像,不是一回事儿。从这件祭蓝碗看,康熙祭蓝厚重深沉,而宣德祭蓝鲜亮自然,再则这件康熙祭蓝碗没有宣德碗的灯草口。此外,这个碗的六字楷书款少了几分宣德的沉稳,多了几分康熙的娟秀。
我马上回信给肯氏,“碗收到,我很喜欢。”仅此而已,并没有点破以我之见它不是宣德本朝瓷器一事。原因很简单,这个碗十分美丽,我欢喜。依照我的经验,向美国人买古董,好就说好,卖主听了高兴,愿意继续和你做生意。这和国内相比有所不同,见到好古董就不一定能马上说好,得讲究策略,尽量挑毛病说不是,绷他练他,耐下性子磨,你若是说好,要多少钱给多少钱,卖家反而会觉得吃了亏,改变主意不卖了,或者给买卖制造出困难麻烦,结果一句赞赏的好话能弄的双方都不愉快。买古董是一门学问,除了得有好眼力,还得买得巧。古董价钱相差很大,同样的东西买好了就能捡漏,买坏了赔本不说,还损了你积攒古董的心气儿。
这个肯福斯特是个外国人,还是中国人用的外国人的名字?单凭一只碗是看不出来的。他的英文非常地道,像是美国人,可他用在描述瓷器上的汉语拼音准确无误,又令我生疑。
又过了一个星期,肯福斯特用电邮给我发送了一个大邮件,由于我的电脑尚未用宽带,下载这个邮件,花了我二十几分钟。肯福斯特通过这次的邮件,传送过来十几张照片,以不同的角度拍摄了一个菱边青花大盘,青花发色似中东进口的苏麻离青料,挥笔处艳丽,驻笔处深沉,青花略见晕散,积厚处能看出明显入胎的黑色铁锈斑,所绘图案是池莲鸳鸯戏水。肯福斯特没有报价,也未对此盘做详细描述,只说了这个盘子是他父亲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叙利亚大马士革一家店里买到的。
同一信中,他开始简单地介绍自己的家庭背景。据他介绍,他的祖父与父亲两代都热衷于古董收藏,祖父倾心于古埃及古罗马的古董;父亲则喜爱中国古瓷。他还随信一并发来了几年前他们家族收藏的中国瓷器,在佛罗里达州一个博物馆参展的内容介绍影印件。
看来这肯福斯特是道地美国人。我回了一封短信,表示感谢并询问这个盘子什么价钱。肯福斯特等了几天,才郑重地回信,他提醒我说:此一时,彼一时。这个大盘的卖法不可混淆于上次的那只碗,它的收藏价值远远超过了那只蓝碗。从买卖的角度,他要说的就是一个字,贵。他提议,此类的交易最好见货付款,欢迎我去亚特兰大。如若不便安排行程,他可以带着盘子到纽约来面谈,至于盘子如何贵法,他始终没有给价。
看完肯福斯特短短几行字,我合计,得,这老肯把我当大户了,我不能去也别让他来。当然,这都是一时赌气的话,赌完了气还是放不下这个盘子。我暗自斟酌,不亲眼见一见这个艳丽的大盘,恐怕以后会和自己交代不过去,既然如此,请肯氏来纽约不如我去一趟亚特兰大,肯福斯特真的抱个盘子来到纽约,我买不买都不是太自由。若能自己去他那儿,不仅思想没有负担,也可以看一看他的家族收藏,看一看他祖辈三代积攒了多少宝物。
从纽约飞到亚特兰大用了两个小时,我在亚特兰大机场寻找肯福斯特也用了两个小时。他既不在接机的人群中,也不在取行李的地方。我又不认识肯福斯特,只好到处找手中举着牌子的人,在这些牌子上找我的名字。
找了两个小时,我找遍了四通八达的亚特兰大机场大厅和长长的走道,心情从期盼到焦虑,从焦虑变成了失望。这个肯福斯特怎么可以言而无信呢,这以后交道怎么打?
既来之,则安之。回程票是第二天晚上的,亚特兰大的旅馆我早已订好,不如借此游览一下这个我从未涉足过的城市,第二天还可以逛一逛那里的古玩市场。
我出了机场大厅,排在等计程车队伍的后面,这时,我在一个长头发大胡子人手上拿着的纸板上,看见了我的名字。拿牌子的人站在队伍的前头,面对着排队上计程车的人群,一脸傻乎乎的表情。
我出了队列,上前问道,“你是肯福斯特?”
他的两只眼鼓了起来,张开嘴却没有说出话,手上还举着我的名字。
我说,我是纽约来的。
肯福斯特这才放下牌子,伸出手来。
当天已来不及去看他家的收藏,肯福斯特开车将我送到旅馆休息,第二天一早他再开车到旅馆接我,一同驱车前往他的家。
肯福斯特的家离市区不远,屋大院深,蜿蜒的台阶周围长满了枯萎的杂草,秋天的落叶尚未清理,仿佛是电影里那种败落的世家。开了门,一位步履蹒跚,容貌端庄的老太太从侧房走了出来。肯福斯特介绍说,这是他的母亲,并说如今这个家里只有他们母子共同生活。
穿过客厅是餐厅,餐厅右侧是书房,书房里没有书,大大小小的玻璃橱柜里堆放着许多小件古董,多是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的小铜人、金人、石人及各种装饰品。这些古董上落满了灰尘,像似经年累月无人打理。我猜,这应该是他祖父的收藏了。
书房往里,穿过一个走道,有一扇门,开了门就是地下室的楼梯,肯福斯特引领我走下了地下室。也许肯福斯特做了准备,地下室的布置比起落满灰尘的书房干净整洁得多。这个地下室是个单间,比起楼上小了许多,想必是肯福斯特专门隔出来作为陈列古董用的。这间屋子里陈设简单,四周墙边放置着窄长的条桌,桌上桌下都是我所熟悉的中国瓷器。肯福斯特打开一盏大灯,霎时间,绚丽多彩的瓷器仿佛花儿一样都开了。那一件照片上的青花瓷盘,就在其中。肯福斯特双手端着那个盘子,递到我手上,让我细细观赏。
这盘子直径约四十厘米,很沉,盘子上艳丽深沉的青花色彩异常夺目。以手抚之,青花积淤之处略略凹陷,深入胎骨。如此纯正的“苏青”料,实在难得一见。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我坐下来把盘子放在腿上,翻转过来看底足,圈足短而尖,砂底无釉。我从口袋里掏出随身带去的放大镜细看,特别寻找白釉的堆釉处,看是不是有水绿色,这是宣德青花瓷的另一个特征,但往往由于太过隐蓄而被忽略。当我在每一朵白釉牡丹花瓣的积釉处看出隐隐约约的水绿时,心中立刻起了惊喜。
“这个青花是明代宣德年的盘子,”肯福斯特边说边坐下,与我面对。
等他坐定,我扭头看着四周的东西问,“都是你的收藏?”
“这是我父亲的,中国瓷器是他的爱好。”肯福斯特开始平静地说起他的祖父和父亲。
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美国军人,祖父曾在中东和埃及服役,父亲是空军情报官,他的父亲二次大战后被派遣到日本当占领军。他家收藏的多数中国瓷器都是二次大战日本投降后的那段时间,在日本获取的。怎么获取的呢,肯福斯特没说。不过他偶然冒出一句话,“我的父亲说,战后的日本,美国人是老大,找几件中国古董比起收集情报容易得多,况且这些古董本来就不是日本人的财产。”
我猜是不是日本人抢了中国人,美国人又抢了日本人。
我继而又问,“为什么你父亲会对中国瓷器产生兴趣呢?”
“古董收藏这个爱好,融在我们肯福斯特家族的血脉中,所不同的是我的父亲早在二次大战之前就去过中国,见识到了神奇的中国古瓷文化。美国占领日本后,他有了很多机会。”他指了指我手上的盘,“不过,这个盘子是个例外,这是他退役之后,偶然在叙利亚的大马士革的一家古玩店里买到的。”肯福斯特又指了指靠门的墙,墙壁上挂着一顶美国军帽和一个镜框,镜框里镶着一个翅翼图案的臂章。他说,“我父亲早已过世,留下了他的荣誉和收藏。”
不知什么原因,他的话没有让我完全相信,掂量着手上的这个盘子不能决定买还是不买,肯福斯特开出的价钱很高,我对这个盘子却反而不能有十足的把握了。
正在犹豫之间,我看见对面桌子上一个小小的青花壶,静气中散发着一种特殊的艳丽,不由得你不全神贯注。我不由自主放下手中大盘,问肯福斯特,能看看那个壶么,肯福斯特走过去顺手一拿,把那个壶递到我的面前。
这是个青花瓜楞小壶,壶上一面画着四朵牵牛花和两束芦苇花,另一面画着四朵芙蓉花,完好无损的壶嘴壶盖,壶嘴上绘卷草纹,壶盖上是螺旋纹,壶脖子上一圈茶花枝叶纹,小心翻过来,壶底双圈六字楷书款:大明宣德年制。
我仔细端详触摸手里这个青花瓜楞小壶,看着壶上花卉野趣,暂却忘记了肯福斯特、肯福斯特的家和肯福斯特说的故事,整颗心都在这个壶上,我控制着心情,问他,这个壶卖么?
收藏的人口头一句话:打眼是痛心的,但可以原谅,老实承认,下次注意;然而漏货却不可原谅,失之交臂,无可弥补。
肯福斯特说卖。我马上请肯福斯特开价,要买这个壶。
肯福斯特看着我,有点儿懵懂,他还未说要多少钱,我就这么急着说买,不是我说错了,就是他听错了,不过他还是随口开了一个不高不低的价,我说好,我买了。
直到今天,这个壶仍是我的至爱,常常放在大餐桌上,细细端详,百看不厌。
与此同时,我看了这间屋子里的其他小瓷器,从中挑出三、四件,请肯福斯特一同作价。他点了点头,指着一个水草鱼纹罐,说,“实在抱歉,这一件不能卖。这是我母亲最心爱的。”
这件精美的鱼纹罐底上有八字青花款:康熙辛亥中和堂制。
去亚特兰大之前,我原先准备了几个让肯福斯特解释的疑问,一个也没有提起。要问的是:肯福斯特本人对中国瓷器的烧制与鉴赏的术语为什么如此熟悉?汉语拼音又是从哪里学的?他为什么不通过苏富比和佳士得拍卖这些收藏?
这些疑问,当时没有问,至今也没有答案。
二零零四年年底,肯福斯特发给我一个简短的电子邮件,他的母亲已于当年十一月去世。(蔡苏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