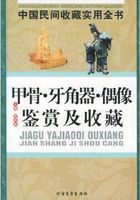纽约皇后区北方大道的一个街角上,有一家古玩店,以卖桃木家具为主,兼卖其他小古玩。推门进去,门上的小铃响起来。听见女店主用英语“Hi”招呼,待她的脸从里面的柜台上露出来时,又用韩语招呼了一遍,尾音一扬,温和悦耳,当得知我们是中国人时,她不好意思笑笑,说:对不起。然后开始用生涩的英语介绍店里的东西。
店是小店面,留着极为狭窄的走道,卖的东西多半是桃木家具,古色古香,造型典雅,工很精致,有美式,也有英式。店里兼有瓷器、水晶玻璃器、老式手表、挂钟、书画,盘子里散放着胸针、耳环和戒指,质地各个不同,来自不同的国家。他们的店不像唐人街中国人开的古玩店,那里只卖中国古玩,而他们是什么都卖。女人说她叫凯西,韩裔。凯西把她认为是“很老”的东西指给我们看。指到瓷盘、瓷瓶的时候,她微笑着说:我不知道这是哪个国家的,是不是中国的?很老。那次我们去是为买家具,就只注意家具。有书橱,五斗柜,三角柜,酒柜,早餐小桌,都让人心动不已。
凯西的先生叫杰瑞,他主要在外淘货,那些家宅拍卖通常有经纪人,总是跟这些开古玩店的人保持联系,每有拍卖,先通知他们,他们是近水楼台的买主,我们这些在报纸上得到消息的人,是赶不上他们的步伐的。
忽然一激灵,发现凯西身后不远的一个柜子里,有几件瓷器,很像朝鲜瓷,其中有一只青花梅瓶,最为抓眼。我立即走近去看,那梅瓶的形状是我从未见过的,跟拍卖会图录上的梅瓶,跟在古玩店和朋友家看到的梅瓶,跟我们收藏的几件梅瓶,都迥然相异。但是,这个梅瓶有着独特的美,像一个美人身着高肩披风,两手从里面拢紧披风下端,显出披风的肩端丰满阔绰,下端含蓄敛约的丰姿。青花发色不是苏麻离青,而是平等青。我基本肯定这梅瓶不是鲜瓷,而是中国瓷器。一时就看得出了神。先生走到我身边,问我看到什么了,怎么一直不出声。我指着柜子里的梅瓶,要他细看。他看了没有说什么。我用中文问先生:你看这个梅瓶好看吗?他想了一下也用中文说:很好看,但是说不准。凯西仍旧微笑着,好像不介意我们要不要买。
我对自己说:简直太美了。
先生问:你看是什么瓷呢?
我没有回答。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我走出这家店,而没有带走这个梅瓶,日后会懊悔。
凯西说:很老吧?很好看吧?
我由衷地点头。这时,门铃叮当响了一声,一个很精神的四十岁上下的男子走进店里。凯西忙招呼他,这就是凯西的丈夫杰瑞。杰瑞听说我们买了一个大件桃木柜子,很高兴,表示当晚就送到家里,还会带着专门擦拭桃木家具的液剂去。
随便聊了一会儿,安排了送家具的时间,我们就离开了古玩店。我恋恋不舍走到门口,门推开一半,心底突如其来一阵冲动,那种在茫茫人海中与一见倾心的人即逢即散的感伤的冲动,于是骤然停下步子,回头看着那梅瓶,毫不犹豫地走回去对凯西说:凯西,对不起,能把上面的那个瓶子拿给我看看吗?凯西表示可以,便小心地把瓶子拿下来。梅瓶在手上掂量着,感觉瓷土很坚密,有分量,瓶高大约十二、三寸,瓶口微微外撇,有唇,瓶肩极为饱满,圆熟,到瓶身下部收拢,圈足敛收,收得很圆,十分俏丽。青花发色沉着含蓄,青中闪蓝灰,火气褪尽后依旧闪烁光芒,瓶身上绘人物庭院花卉,石凳上坐着的书生衣裾飘逸,姿态慵懒却放达自如,庭院里的芭蕉寥寥数笔便如有微风穿过,逶逶摇曳。每一笔都娴熟到不经意。梅瓶她娴静地立于柜台,古往今来,通身散发古老气息,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凯西笑眯眯地问我:你喜欢吗?我告诉她,是的。
我问凯西,要多少钱。没有料到的是,凯西告诉我们,橱里所有的瓷器都被别人买走了,定金都交了,明天过来付余款取货。“你说什么?卖了?”我着急了。卖掉的东西是不能再卖给别人的,这个在生意场上是不兴的,除非我跟买主本人协商。
先生安慰我,说算了,好东西还有,以后会碰到的。我肯定地说:不会的,也许我们再也碰不到呢。于是追问凯西,买主是什么人。凯西说,是一个韩裔美国女人,专门收藏古玩,特别喜欢朝鲜瓷,“但是她看中这个瓶子,说很老,很好看。”再一问,那女人的丈夫是犹太人古董商,家里东西很多,常常到他们店里找东西,“不在乎钱贵,”凯西抱歉地告诉我,并答应我以后有了中国瓷器,“我给你打电话。”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沉默,惦记着那只梅瓶。冥冥之中,我觉得我和她不该就那么即逢即散。如果我不该得到她,那么我为什么会在她被人买走之后还能见到她呢?如果我该得到她,她怎么就已经出什么钱都买不到了呢?先生觉得奇怪,说我从来没有对一样瓷器痴迷到那样的程度。于是问我,是不是非要不可。我说,是非要,你有什么办法?他说让他想想,看还有什么办法。依他所想,出一个高价跟别人买,兴许是可能的,但如果你的对手是一个收藏家,那么钱在她不重要,重要的是东西。
晚上吃过晚饭,杰瑞把橱柜送到家里,彼此道谢后,走了。家里一时安静,我坐在餐桌边,左思右想没有良策。先生从楼上下来,手里抱一样东西,走到餐桌边放下那东西,说:想要把那个梅瓶取来,只有这个办法了。
他放在桌上的是一只青花玉壶春瓶,朝鲜瓷器。我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但还是问他:什么意思?
他说:“换。”
“拿这个玉壶春瓶换那个梅瓶?”
他说:“你还有其他妙策吗?”
那只朝鲜青花玉壶春瓶,是年前从加州的邢子手上买来的。邢子把十几张从各个不同角度拍摄的瓷器照片发过来,其中就有这件青花玉壶春,两只丰肥的青花雀子站在梅花枝头上,朝同一个方向张望,又憨又甜,青花发色十分清淡,是典型的朝鲜瓷青花釉色。邢子介绍时也说明那是朝鲜瓷,要价相当高。他卖的瓷器,要价最高的是明清彩瓷,其次是鲜瓷。
十二、三世纪的韩国,就有了制瓷工艺。那时,中国的朝廷每年都要派内务大臣,到那个以烧瓷驰名全国的小村庄,选拔在年度的瓷器竞赛中作品获得第一名的工匠,带到京城去,专门给皇宫烧制瓷器。合同为期三年,三年之后,重新选拔。韩国的制瓷工匠,都以能够被选去京城给中国皇帝烧瓷器而感到荣耀。到了京城,韩国的工匠必须按照中国的烧瓷工艺来制瓷,纹饰和釉色也要依照宫中的要求来制作。那些三年合同期满从京城回到故乡的瓷器工匠,便把中国的烧瓷技术带了回去。所以,朝鲜瓷深受中国瓷器的影响。世界上,中国瓷为最,鲜瓷次之。
收到玉壶春瓶之后,看瓶身上的梅花树和一对雀子,比照片上更为清新怡悦,青花釉色淡泊清雅,跟中国的国产青料相近,青中闪浅灰,翻过来一看,底子上的窑沾跟糯米锅巴一样,胎瓷则细密而油润,让人爱不释手。
后来还从邢子那里买过一只青花虎罐,非常美,很少见瓷器上画老虎的,因此很珍稀。不久以后,在《世界日报》看到一条拍卖消息,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场拍卖会上的,一只朝鲜青花海水云龙纹梅瓶,以一百多万美元成交,说明鲜瓷的珍稀和受追捧。
邢子卖鲜瓷,价格往往高于中国瓷,不知是加州的买主多,还是他本人更珍爱鲜瓷。没有从邢子那里买下他所有的鲜瓷,手里仅有的两件便成为我们收藏品中的稀罕之物。现在,先生建议用韩国青花双雀玉壶春瓶调换中国的梅瓶,我一时没办法做出取舍。可是,那只青花梅瓶更是让我放不下来。我摩挲着玉壶春,不说话。先生说:有失才有得,你只要想通了,你更想要哪个。
睡觉之前,我做出了决定。
第二天一早,接通了凯西的手机,把我的意思告诉她,好不容易凯西听懂了我的意思,说马上给佩笛去电话,问问她是不是愿意调换,如果佩笛同意,她就打电话回头给我。等待的时候,心情仍旧是复杂的,人有时的确就是鱼与熊掌想要兼得。不一会儿,凯西来了电话,听说佩笛愿意考虑,但要先看看那只梅花双雀玉壶春,才能决定。
凯西听说我手上有鲜瓷,非常兴奋,那是他们韩国的瓷器,要是做成这笔生意,一定能够赚钱。
包好玉壶春去了凯西的小店。杰瑞出去淘货了,佩笛也不在店里,也许我和她之间需要回避一下。我把玉壶春放在柜台上,打开包袱给凯西看。凯西尽管很高兴,却不很懂行,笑微微地说:对的啊,真是我们鲜瓷。但是是哪朝哪代的却说不清。她问我这件老瓷器有多少年了。我跟她说:佩笛和她丈夫都是收藏家,如果她喜欢瓷器,应当看得懂,让她断代吧。
接下来凯西问我向佩笛要多少钱。但其实在这场未见分晓的交易中,有资格开价的,不是我不是凯西,而是佩笛。
玉壶春瓶交给凯西,我就走了。
交易是当天傍晚谈妥的,佩笛出了一个高价买我的玉壶春,青花梅瓶“奉送”,说奉送是个礼仪说法,其实是以物易物,但究竟各自值多少钱,是无法计算了。对我来说,这是狸猫换太子。对佩迪来说,也是狸猫换太子。
我们连忙赶到北方大道,小店里灯光通明,门铃叮当响起来像个圣诞夜。凯西和杰瑞的脸上都露出欣喜的笑容,把梅瓶从柜子里取出来。我看看四周,那只梅花双雀玉壶春瓶,已经不在了。
韩国玉壶春瓶出门回家,中国青花梅瓶也出门回家。
把梅瓶放在卧室近窗的三角柜上,入夜,月光洒在她身上,莹莹有玉色,半是透明,半是沉郁,越看越觉得岁月久远,却历久而弥新。
换回的这个梅瓶,是明代万历的梅瓶,每一个特征都符合万历青花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梅瓶底部画的马,更像驴子。万历年间画马就是这种画法。
那天傍晚,佩笛自个儿给我来了电话,问我家里是不是还有鲜瓷。我告诉她还有一个青花岁寒三友虎纹罐。她问我,能不能让给她,她出高价买。我抱歉地告诉她,只有这一个鲜瓷了,我也很珍视它,所以希望能够留在手里。她叹了一口气,遗憾地请求我:你再考虑考虑好吗?(谢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