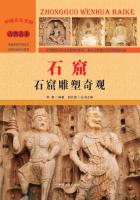适逢恩师丁善德八十华诞,真想为他作一幅“音乐素描”——将他的为人与从艺的“轮廓”勾画出来。只是,他的外表并不像那些曲线多角,个性张扬的“艺术家”,不那么好画,而我则更不是个好画师。因此,就只能信笔开河,随意涂抹,画他一个七八成,介于“似与不似之间”,也就心满意足了!
丁老有本传记,叫《东方的旋律》。东方,固然可以把人带到那缠绵宛转、绵绵不断的流水般的旋律中,但是,它更能使人浮想到飞腾九霄、神游太空的龙。我的脑海中突然飞出了一条龙——上海音乐学院是中国最早行驶的“音乐龙船”,而丁老和咱们的老院长贺绿汀,就是这艘船的“龙头”——在难忘的五六十年代,音乐学院的鼎盛时期,就是这两位“船老大”将这艘“龙船”驶进了黄金海岸!
人们既然习惯于将音乐学院的大—中—小学的“连锁教学”比喻为“一条龙”,我也就不妨试着从龙头(大)、龙腹(中)和龙尾(小)这三个部位来描一描咱们这位“老龙头”。
先说一个“大”字。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庄子也提出,作一个“大人”,必须懂得“大本大宗”,也即做人的大道理。这个大道理就是爱国爱艺爱真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就参加了学生小组到松江一带去宣传抗日及为马占山的东北义勇军募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当李惟宁将老音专改为汪伪“国立音乐院”,挂牌招生时,他又毅然与之断绝往来,不再去老音专兼课,并拒绝向日方办理私立音专的学校开业的登记手续。抗战胜利后,他以作品第一号《春之旅》钢琴组曲来反映“当时中国人民盼望抗战胜利、迎接新的春天的迫切心情”,并创作了既“反映了抗战后的喜悦”,又“带着忧虑、彷徨的心情”的《E大调奏鸣曲》(op。2)。在解放战争捷报频传、新中国诞生的前夕,他又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奉献了《新中国交响组曲》。这部作品于第二年在上海兰心大戏院由富华指挥市政府乐队首演,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人民政府乐队演出的第一部中国作曲家的交响乐作品,而且是中国现代音乐史上第一部以新中国为主题的作品……
丁老不仅是位怀有“赤子之心”和“大本大宗”的“大人”,而且还是位大度豁达、大家风范的大雅君子,大方人家。
音乐学院和其他“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一样,唧唧喳喳、喋喋不休的小人小事俯拾皆是。他扶了别人,别人倒过来骂他、踩他,他也不在乎。“文革”中,有的吆五喝六的“红卫兵”对他当众羞辱,可事后又低头哈腰地乞教于门下,以便混块“丁门弟子”的招牌,他也既往不咎,哈哈一笑就收下了。他总是从“大知闲闲”、“大言炎炎”来对付“小知间间”、“小言詹詹”。他还敢于用人,善于管理,不逞小智,不代下司职,真可谓“大师石斫”——高明的匠人不用斧头砍削,而是让各部门自司其职、独立运转。他可真是音乐学院第一号大度之人也。
因为大度、大方、大气,所以才能大公无私,大刀阔斧。他敢于决断,敢于拍板,从不推诿扯皮,拖拖拉拉。在他执政期间,升教授、分房子等这些麻烦事,都被他处理得顺顺当当。他人如其名——丁善德者,行善积德之园丁也!他施政为民,做了很多好事——用现在的时髦话说,就是“大办实事”!这次举办丁老从艺六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全院各部全出动,齐心协力,毫无怨言。在闭幕式回昆山故里访问时,警车开道,乡亲们扶老携幼迎丁老,看看这些动人的场面,就可知其为人之一斑了!
李白说:“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丁老就是这样一个胸怀大志的大丈夫。当他还是染坊小丁时,就已是“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到后来,又从昆山走向上海,从上海走向巴黎,从巴黎走向世界,从小吹小打一直到铸成《长征》交响乐、《黄浦江颂》大合唱这样大气磅礴、大笔如椽的“大块文章”,真不愧为大丈夫也!可大丈夫不是一蹴而成,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所谓“大辂椎轮”,就是说华美的大车是由没辐的原始车轮演变进化成的;又所谓“大乐之成,非取于一音;嘉膳之和,非取于一味;圣人之德,非取于一道也”!如果我们读一下丁老的奋斗史,回顾一下当年他在查哈罗夫班上“课前吃不下,睡不香;听到他的脚步声,心发紧,手发颤”的情景,特别是查哈罗夫对他吼道:“I Kill you!”(我宰了你)的场面时,我们就可得知他是如何从一个染坊小丁成长为乐坛大师的!
作为“大丈夫”,还必须有“大丈夫相时而动”的机智变通和“大丈夫能屈能伸”的品性修养,不然是难以度过时代的重重磨难的。在“文革”中,他被直抛地撂倒在地——“掼沙包”,还被皮带把手抽得皮开肉裂,可是他想什么呢?——他对我说:“我在想,虽然我在受苦受难,但总比非洲奴隶要好得多……”残酷的现实使他大彻大悟,他将一切视为身外之物——一家的住房因中房被人霸占后隔成东西两段,他自嘲为“东巴基斯坦”和“西巴基斯坦”;后来造反派又来抢书房,他干脆咬一咬牙将一千多斤珍藏的书稿乐谱以七分钱一斤的废纸收购价,连同书柜一股脑儿地当旧货卖掉了……对于这段现代中国的丑史,我们能说些什么呢?好在丁老大难不死,已是福星高照了!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说来丁老也真是有福——四岁时家里整修住房,一根横梁掉下来正打在头上,险遭不测,却大难不死(只是头顶至今还凹进一块);过了六十年,在他六十四岁时,一次开小组会时因发言情绪激动,头晕目眩,得了小中风——虽然嘴都歪了,可还是大难不死,过了三个月就彻底痊愈了!最险的是七十岁那年,突然心肌梗塞,医院已发出病危通知,后因治疗有方,调理得法,终究还是大难不死,转危为安了!
“老叶经寒壮岁华,猩红点点雪水葩,老去又逢新岁月,春来更有好花枝。”这是明朝沈周的诗《红山茶》。谨以此诗献给“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的丁老!
讲了半天“大”,该说说“中”了!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白居易也说:“中立不倚,道直气平。”
丁老为人不偏不倚,平和中正;作曲时也像工人做工,农民种田一般——日出而作,日暮而归;晚上十点准时睡觉,雷打不动。他有一个和谐的家庭,爱妻庞景瑛是他的学生、知音、伴侣和“后方总司令”,这就使他获得了一个“安定团结”的“小气候”。韦瀚章在《记丁善德》一文中说:“他的订婚是经过自由恋爱的。不过他的自由恋爱是恬静的,不是燥热的;是油然而生的,不是急先锋的;是恋爱不忘读书,不是读书不忘恋爱。所以他的学业是不曾受过什么不良影响……”
“恬静的,不是燥热的;是油然而生的,而不是急先锋的。”这也是丁老作品风格的特征。我们在他的大部分作品中,都能感受到一种典型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国传统的审美情趣。这也是“中庸之道”在艺术上的折射——作品要自然,表现要适度;不要故意用“恶趣”与“惊人之笔”来哗众取宠。在我们品味《山上的松树青青的哩》时,就真可感觉到一汪清泉从作曲家的心泉里涓涓流出……
丁老的“中”还表现在他的“中西合璧”。他六岁时就怂恿母亲掏出八块银洋,买回一套锣鼓,以后又买了一只琵琶,自己拨弄。他还经常从节省的零用钱中,花七个铜板去听昆山评弹演员张步禅弹“大套琵琶”。他从吹、拉、弹、打到昆曲、评弹,件件拿得起手。初进音乐学院时,还是主修琵琶,副修钢琴,到第二学期就改为主修钢琴,副修琵琶。1928年11月,他在学校成立一周年音乐会上,就演奏琵琶独奏曲《平沙落雁》。在学校第七次学生音乐会上,他又同时独奏了菲尔德的钢琴曲《A大调夜曲》和琵琶曲《宫怨秋思》、《卧看双星》、《金风落叶》和《月冷熏笼》。当他毕业后成为第一个在全国公开举行个人钢琴独奏音乐会的中国钢琴家之后,他说:“这次音乐会后,我想了很多,我强烈地意识到,演奏世界名曲虽有一定的意义,但是显然是很不够的,中国应该有中国人自己的钢琴作品。”因此,“要搞创作的欲望再一次在我脑际产生”之后,拜弗兰克尔为师,又留法深造,刻意中西合璧,像他的好友赵无极在自己的油画作品中把注意色彩的法国印象派技法和研究意境的中国山水画特色结合在一起那样,也开始在音乐中探求此路。他在来到法国之后的第一部作品,钢琴独奏《序曲三首》中,就将绥远民歌《小路》的音调、昆曲《玉簪记》中的“琴挑”一折,与印象派的手法有机地结合成一体,别有一格,独具新意。在丁老七十三岁高龄时,他还完成了被称为“具有浓郁的东方风味”的《C大调钢琴三重奏》和声乐套曲《滇西诗抄》。他自己说:“在创作手法上我作了一些新的探索,如何把近现代的创作手法与我国民族风格和音调结合起来,在这部声乐套曲中,我作了一些尝试,如不同节拍和双调性的同时应用等”。丁老就是沿着这条“中西合璧”的路,越走越宽广的!
最后要带一笔丁老的“小”。
丁老的小品写得很精彩,小品如小诗,而“小诗有味似连珠”。我最欣赏他那首经布朗热(Nadia Boulonger)指点过的《中国民歌主题变奏曲》。这首作品的主题是从李丽莲赠送的一本油印的民歌集中选材的;出国前,丁老看过戴爱莲跳的一个独舞,舞蹈音乐就是用的这首藏族民歌。在创作过程中,布朗热经常讲的“作品要精炼”、“节奏要有变化”,点化了他创作了这首隽永精致的钢琴曲。我同样欣赏他的《序曲三首》和为蔡绍序改编的四川山歌,在这些民歌中,他真正做到了“用钢琴伴奏来写出民歌的意境,通过钢琴与歌唱的艺术来表达民歌的思想感情”。
丁老的“小”还表现在“小事糊涂”,“小事化为没事”。而我们这些弟子常易情感浮动,有时甚至会越些小轨,闯些小祸,每逢此时,幸灾乐祸者拍手称快,而丁老总是充满爱心,为弟子排忧解难,充当“小事化为没事”的“革命和事佬”!
好了,好了!我已经将丁老从头描到脚,从大描到小了!我的“素描”也快成了“工笔画”了!谨以此画献给我师,祝他松柏长青,还是那样龙腾虎跃!
1991年7月3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