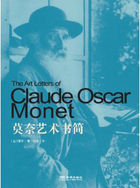肖邦二百岁诞辰即将到来(据称肖邦生于1810年3月1日,确切日期尚有争议)——所以今年是音乐界的“肖邦年”。前几天,上海电视台艺术人文频道要制作《三月的肖邦》专题节目,邀我谈谈肖邦的音乐精神。
不妨思考一下,肖邦之所以不朽的根本原因。按照艺术的通理,艺术家不朽,一定因为该艺术家有“绝活儿”——所谓“绝”,盖指其成就之“独特”乃至“奇特”,举世罕见,甚至独一无二,从而成为某一方面或某一范畴的精粹典范,并借此彰显令后人崇敬和仰慕的正面价值。
肖邦之“绝”,依笔者浅见,总体上表现为将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艺术追求融合在一起,由此达到了一种几近不可思议的矛盾统一——用英文表述,这种现象叫paradox,通常译为“悖谬”或“吊诡”,但更恰当的理解应为“似非而是”。这种独此一家的矛盾统一性体现在肖邦创作及风格的各个方面。
例如,表达媒介的单一性与表现内涵的丰富性——肖邦之为肖邦,两者的同时存在必不可少,缺一不可。在肖邦所有二百余首作品中,无一不包括钢琴,即便是为数很少的室内乐和歌曲,肖邦也从不离开钢琴。他是历史上唯一一个只为钢琴写作的大作曲家。这是有意为之的自我限制,并由此带来了表达媒介的极度单一——这种大胆和绝对,不禁令人想起多年后另一位大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的悖论言辞:“我对自己的行为划定的范围越小,为自己设定的阻碍越多,我所获得的自由度就越高,其意义也就会越大。”另一方面,肖邦在这个看似单色狭小的黑白键盘中,“螺蛳壳里做道场”,营造了一个怎样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其孤冷,其雅致,其精美,其诡变,正与贝多芬、柏辽兹、李斯特、瓦格纳、马勒等体量庞大的巨人反其道而行(难怪肖邦不喜欢贝多芬,对柏辽兹和李斯特也颇多微词。猜想如果他听到瓦格纳和马勒的音乐,一定会“皱眉头”),但在艺术质量上又毫不逊色,这可被看作是以少胜多、以小制大的奇迹,其眼光和功力令人瞩目。
次如,浪漫的随意自如与古典的严谨逻辑——这两种看似完全对立的风格范畴居然同时共存于肖邦的作品中,且相互支持,彼此交融。笔者寡闻,放眼乐史,在这方面可与肖邦媲美的也许只有莫扎特一人。但莫扎特的率性自如与肖邦相比仍迥然相异,因其运作于古典风格条件之中,即便灵活多变、灵光焕发,也依然有规可循、有据可查。而肖邦那些宛如滑丝的装饰花腔,那些匪夷所思的音型变织,那些似是顺手拈来的即兴式进行,真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奇妙在于,这些看似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音乐表层之下,却潜藏着坚固、严格、扎实而规范的声部结构。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肖邦的低音写作从来都遵循着严谨的导向感,并与高声部始终形成良好的对位关系。随手举出那首并不算肖邦的最佳代表作、但仍旧不可多得的《摇篮曲》(作品57),右手是花样不断翻新的装饰变奏,左手则自始至终保持着一个绝不改变、近乎刻板的主-属和声音型(摇篮的音响写真)——如此严格规范的左手基础与如此花样百出的右手装饰,在我看来,这里的矛盾统一简直是肖邦音乐趣味的缩影写照,也是其美学思想的无言表白。
再如,音乐风格的个人性与音乐元素的民族性在肖邦的创作中达到了高度的辩证统一。肖邦音乐的“味道”在音乐史中属于最具个人风格、最容易辨认、也最不可模仿的例证行列。但“吊诡”的是,他的这种个人性中却包含着极为复杂和多样的波兰集体与民族元素。马祖卡的节奏和韵律,波罗涅兹的矫健舞步,古老圣咏的遥响与回望,这些原本并不是肖邦个人拥有的音响财富,在肖邦手中不仅成为他作为波兰民族音乐代言人的身份特征,而且也成为构筑他个人风格的不可或缺的组成要件。特别应该指出,肖邦的音乐尽管极富波兰性,但他本人却无论如何不能被算作是“民族乐派”。他最重要的后半生主要生活在法国巴黎,而且他既没有提出任何有关波兰民族乐派的理论主张或宣言,也没有在自己周围或身后形成一个“波兰乐派”。肖邦于是成为史上的一个绝响和孤例,他以自己的独特视角规定了音乐的波兰,波兰的音乐则经过肖邦才通向了世界。
又如,肖邦的作品中,口吻语调的时尚通俗性与语言探索的先锋前卫性恰也形成一对貌似矛盾的统一体。众所周知,肖邦的创作场域和意向听众主要是上流社会的贵族沙龙。他的教学对象也主要是贵妇和小姐。因此,毋庸讳言,他的部分作品中确有某种不可避免的“沙龙气”和“脂粉感”。不少人甚至感到肖邦有“娘娘腔”,这种论调尽管极为狭隘(傅聪先生特别反感这种说法),但也并非毫无根据。至少,肖邦的夜曲和圆舞曲,以及诸多其他作品的抒情段落,确乎充满着圆润清丽的“小资情调”,路数上接近柳永、周邦彦那类“婉约词”。但是,诚如舒曼评论肖邦的那句名言,所谓“隐藏在花丛中的大炮”,肖邦之所以超拔于一般的沙龙音乐之上,正是由于在这些“风花雪月”、“儿女情长”的美丽“花丛”中,隐藏着不为外人所知、因而常被忽略的“大炮”——舒曼的这句话其实不仅可以作一般性的政治化解释,也可以用来理解肖邦的艺术匠心。这些“大炮”不仅仅指《“革命”练习曲》(作品10之12)、《“英雄”波罗涅兹舞曲》(作品53)中那些明白无误的战斗性格,而且也意味着肖邦作品中那些更为内在、更为“专业”的激进手法。肖邦大胆的和声探险(其超前甚至直接预示了瓦格纳),他在大型曲体结构上的独特建树(特别是摆脱奏鸣曲式束缚的勇气),以及他在钢琴织体写作上的高度创意(在充分利用钢琴的潜能上至今无人超越),所有这一切映照出肖邦在艺术上的“先锋”姿态,但这种“先锋性”却又常常埋在看似时尚甚至有意通俗的音乐外表之下——这样成功的矛盾结合,在今日看来,已经近乎是神话。
凡此种种,均说明肖邦音乐在艺术上的成就,虽已经过近两百年的消化和吸纳,其独特与奇妙仍然远远超越了常人的理解和想象,仍然能给我们带来无穷的惊喜和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