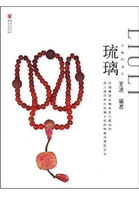肖邦的音乐具有一种无法道明的特别气质。乐声幽扬飘来,听上去似乎是作曲家一不小心让你窥见了他内心最深处的孤寂沉思。当然,音乐没有具体和明确的语义,谁也说不清楚,肖邦的自言自语究竟说了什么,但肖邦音乐所独具的表达口吻,几乎从一开始就会在听者的音乐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迹。久而久之,人们给肖邦冠以“钢琴诗人”的雅号,承认他的音乐蕴含奇妙的诗情与高度的创意。
这种不可模仿的独特诗意首先源自肖邦所选择的表达媒介――独奏钢琴。一个人独自坐在钢琴键盘前,从手下流出的音符自然具备私密性,与上百人合奏交响曲的“千军万马”之势迥然相异。虽然肖邦远非首创钢琴独奏的第一人,但在他的手下,钢琴在历史中第一次被转型――成了倾诉个人心境的最佳手段。用现在的批评术语说,肖邦开始在钢琴写作中有意识、有系统地回避了“宏大叙事”,转向更为自由、也更加幽微曲折的“私人叙述”。
交响曲、歌剧这类“宏大叙事”的代表性体裁因而在肖邦的创作视野中全然消失,就连奏鸣曲、协奏曲、变奏曲这些在传统中占据钢琴作品中心地位的大型曲体,在肖邦的创作生涯中也一律被置于边缘地带。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具有暗示性标题、但绝没有具体景物描绘意图的“小型”作品:夜曲、叙事曲、谐谑曲、船歌、摇篮曲以及波兰舞曲、马祖卡舞曲、圆舞曲……就像一位文学家主动放弃长篇小说或大型戏剧的编织,专心致志于短篇小说乃至抒情短诗和性灵小文的写作,这样做不仅需要艺术上的眼力,而且需要道德上的勇气。因为在肖邦时代,除他以外,没有任何一个重要音乐家终其一生固守这种“私人叙述”的写作思路。舒曼在早年似乎是肖邦在音乐上的同道,但人到中年后,终于没能摆脱德奥根深蒂固的交响乐传统的强大吸引力,拼命在言不由衷的交响语言旋涡中挣扎。门德尔松与正统的音乐遗产达成妥协,采取将“宏大叙事”平面化的策略,虽缺乏戏剧深度,但笔法潇洒流畅。至于李斯特,虽然也热衷于钢琴音乐的潜能挖掘和性格拓展,然而更多是为了博取外表的辉煌与廉价的掌声,因而与肖邦暗自独语的趣味恰恰形成对极。
肖邦因此踽踽独行。这种独特的“唯一性”体现在他艺术的所有方面:他只为独奏钢琴写作,绝少旁骛,所有二百余件作品中无一没有钢琴;他身为著名钢琴家,但却完全不像其他炫技大师,不仅在成名之后拒绝旅行演出,甚至很少举行公开音乐会(他的收入主要依靠私人教学和作品版税)。而作为作曲家,如上所述,他又违反常规,作品的体裁类型看上去更像是炫技钢琴家为自己实际演出而写作的一些应景小品,而不是更具“分量”、更能显示创作“实力”的大型交响曲与歌剧。据说,肖邦年轻时在华沙音乐学院的作曲教授曾对这位才华横溢的后生寄予厚望,希望他日后能在波兰民族歌剧的创建上一展宏图,但日后的事实令他失望。肖邦似乎很早就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天然禀赋,他命定属于一个孤寂的抒情世界,排斥人声鼎沸的喧哗与凯旋。
奇怪的是,他真的非常喜欢歌剧,旅居巴黎时晚间经常去观赏歌剧。众所周知,他最欣赏的同代作曲家是以优美旋律著称的意大利歌剧作曲家贝利尼。然而,意大利歌剧中的华美咏叹和醉人旋律转至他的笔下,却没了舞台上的灼热气息,变成了清冷而细腻的内心婉唱(例如降D大调夜曲作品27之2),如泣如诉,丝丝入扣。这种对先在摹本的个人化转型,是肖邦艺术最令人惊叹的鬼斧神工之处。你明明能听见他音乐的源头所在,但最终的整体音乐风格却明白无误只属于肖邦个人。例如马祖卡舞曲,本是波兰各地村民最常见的民间群舞形式,属于一种真正的“公众性”社交娱乐品种。但在肖邦手中,马祖卡成了他最富私密情怀的个人心理发展笔录。从早期幼稚的作品7之1(降B大调)中对民间舞蹈节奏和特殊音响的单纯模仿,途经作品17之4(A小调)古朴的调式和声与幽咽的心曲吐露,再到作品50之3(升C小调)中利用民间特有的不间断重复音型而企及的抒情高潮,最终是作品63之3(升C小调)这首作曲家生前最后一首马祖卡中悲剧性的挣扎,我们从中不仅看到肖邦风格成熟发展的全部过程,也听到这位早逝的敏感诗人通过音响所展示的心路幽径与情感境况。再如肖邦对巴赫音乐的独特吸收。肖邦终身崇敬这位日耳曼先辈无与伦比的深刻逻辑与清晰思维,虽则巴赫的神性音乐世界与他自己飘逸的音乐风格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然而,肖邦作品中无所不在的复调穿插与线条出没,恰是巴赫对位精神的肖邦变种,它们出自肖邦对巴赫《平均律键盘曲集》自幼便如庖丁解牛般的纯熟运指体验,是肖邦善于化解和吸纳异质外来影响的最佳明证。
伟大的艺术家之所以不朽,是因为他们能通过自己的艺术构造出一个独特的想象世界,它与现实世界相平行,反射现实世界的阴影与景象,但与现实世界又绝不相同。肖邦的世界是绮丽精工、含蓄深沉的内心写照,美不胜收,又深不可测。其后,无数追随者起而效仿,但如方家所言,被模仿的只有外表,缺乏的是灵魂(例如早期的斯克里亚宾)。或许肖邦真正的艺术同道不是音乐家,该是跨越时空的其他文学艺术家?晚唐诗人李商隐工丽深细、和美婉转的诗风难道不就是肖邦音乐的文字对应?再看日本小说家川端康成对人、物、事细针密缕而若即若离的精致叙述,与肖邦无限关注音乐的细部处理与层次变化又何其相似?!即便如此,我们仍可以争辩,肖邦的音乐进行中自然的即兴风味扫除了李商隐式的刻意求工,而川端康成近乎没落贵族的腐朽病态更是肖邦血脉中所忌讳的。傅聪先生十多年前在上海音乐学院开设大师班时说过,肖邦的艺术道路,应被看作是从诗人到先知(frompoettoprophet)的过程。生而诗人,死为先知,肖邦的音乐独语由此穿过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隧道,在今天一如既往地在听者心中激起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