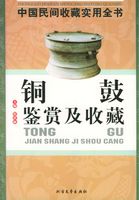同时,“第五代”以其不同于传统的崭新气质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电影的刻板印象,夺得中国电影史上具有纪念意义的几项大奖:《黄土地》荣获第38届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银豹奖”,这是“第五代”第一部受到世界关注的影片;《红高粱》所获的第38届西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更是三十八年来中国电影第一次打开了这扇大门,而张艺谋也成为第一个捧走“金熊”的亚洲人;《晚钟》(吴子牛导演,1989)获第39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再次证明欧洲对“第五代”的青睐。
在整个90年代,第五代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四面出击,全面开花,各大奖项悉数收入囊中:李少红的《血色清晨》(1990)、何平的《双旗镇刀客》(1990)、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1992)、陈凯歌的《霸王别姬》(1993)、张艺谋的《一个都不能少》(1999)……这些第五代影片以凯旋的步伐,走过欧美许多国际影展,使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之林中占据重要一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第五代”最风光的时代,但从90年代中期开始,第五代导演便因为各自个性化的追求开始分道扬镳、各立山头了。“第五代”这个具有特定历史涵义和时代意义的指称已经意义甚微,我们现在概括的“第五代”在很大程度上是指那些曾经属于“第五代”这个范畴的“第五代人”了。
曾经的“第五代人”虽然已从电影题材、艺术气质上相去甚远,但是商业意识的不断强化却是相同的。2002年初,“第五代”就以一种集体复出的势头拿出了各自的作品:《和你在一起》(陈凯歌)、《极地营救》(张建亚)、《假装没感觉》(彭小莲)、《周渔的火车》(孙周)、《恋爱中的宝贝》(李少红)、《小城之春》(田壮壮)等等,这些新作,无不呈现出精美的艺术品质,但绝大多数都放下了“精英文化”的身段,而将观众和市场作为第一考量。从《英雄》(2002)开始,继而有《十面埋伏》(2004),张艺谋在电影商业化道路上的步子越迈越大,直到《满城尽带黄金甲》(2006)遭受猛烈的批评。陈凯歌2005年的所谓“大片”《无极》,尽是没头没脑的稀奇古怪的场景,从电影艺术的角度来说是失败之作,并不过分。从当今电影市场的份额来看,“第五代”无疑已经成为国际电影投资商在中国电影市场的代言人,“第五代”以艺术冲破中国传统电影藩篱,又以金钱圈占中国电影的市场,是喜是忧还未见端倪。
七第六代:成长的烦恼(1990—)
评论界对于“第六代”的界定,基本以1990年为一个坐标系。以当时刚刚毕业的张元以及尚未走出学院大门的一批年轻人为代表,他们构成中国电影第六代的整体基座。常见的名单是:张元、管虎、贾樟柯、王小帅、娄烨、路学长、胡雪杨、陆川、刘冰鉴、李欣、徐静蕾、张扬等年轻导演。王全安、侯咏、姜文、顾长卫、朱文、章明等可以算作异数,但如今还是被笼统地纳入了这个圈子,有人笑称为“五代半”。其实“第六代”的定位更具美学意义,这是一批迥异于“第五代”的新生力量,他们的观念、语言和态度已日臻成熟、别开生面。
“第六代”的作品也可以开出一长串名单:《妈妈》(张元导演,1991)、《北京杂种》(张元导演,1993)、《阳光灿烂的日子》(姜文导演,1994)、《东宫·西宫》(张元导演,1995)、《小武》(贾樟柯导演,1997)、《站台》(贾樟柯导演,1998)、《苏州河》(娄烨导演,2000)、《十七岁的单车》(王小帅导演,2001)、《寻枪》(陆川导演,2002)、《任逍遥》(贾樟柯导演,2002)、《青红》(王小帅导演,2005)、《孔雀》(顾长卫导演,2005)、《可可西里》(陆川导演,2005)、《图雅的婚事》(王全安导演,2007)……“第六代”的作品在2005年之前大多没有惊人的票房和足够的知名度,但通常是国际各大影展上的常客并屡屡获奖,加之影迷的竞相追逐与碟片市场的炙手可热,悄然造就了颇为神秘、独特、纯粹的“第六代”群体。
这一批导演制作的影片曾经被称为“地下电影”或“独立电影”,因为年轻的导演刚进入影坛时遭到来自文化和经济的双重压力。在文化上,这些影片在某些方面不够成熟或者不符合官方某些意志,没有得到在国内放映的批准;在经济上,也处于找不到资金、捉襟见肘的境地。这些影片几乎完全按照导演自己对电影的理解来拍,与商业电影有很大的距离,因此很难找到赞助商。正是由于他们在艺术上的独立性,这些影片屡屡在国际上获奖,引起了观众的注意。比较引人注目的是,贾樟柯导演的《站台》、娄烨导演的《苏州河》、王小帅导演的《十七岁的单车》、姜文导演的《鬼子来了》(2002)等,它们分别在或大或小的国际电影节上以“中国电影”的身份获奖,然后等待它们的共同命运却是在国内(大陆)的禁映,即不能进入国内电影市场而获得公开放映的权利,有的导演还被处以禁止拍片的惩罚。
第六代导演的批判锋芒指向了当时电影的流行样式“散文化电影”。他们强调当时的电影界对《黄土地》的美学评价实际上是一种历史性的误读,“说《黄土地》真实再现了黄土地上人们的生活状态,倒不如说它把这种生活风格化了,这种认识上的差异使《黄土地》的追求成为之后中国电影的一种时尚,并在一种貌似深奥却是很幼稚的层次上进行效仿”《中国电影的后“后黄土地”现象》,《上海艺术家》1993年第4期。。由于“电影制作界对于这种个人电影的追求,导致了一种以浮浅的社会学、文学、文化学甚至精神分析解释自我作品的风尚,这使中国的电影导演们始终处在一种欠清醒的状态中”贾磊磊:《时代影像的历史地平线——关于中国“第六代”电影导演历史演进的主体报告》,《当代电影》2006年第5期。。
与“第五代”那种对历史、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挥写相比,第六代导演更关注作为个体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存状态,这使得他们的影片在题材上具有一种“原创性”,在表层形态上力图呈现出一种生活本身所具有的“原在感受”。普遍采用同期录音保持现实空间的环境真实;通过大量的移动摄影建立观众与剧中人物相同一的视觉心理感受;与此同时,电影开始自觉地淡化演员的戏剧化表演方式,最大限度地还原剧中人物自身的职业特点,给观众造成一种“目击现实”的心理感受,进而改变电影仅仅供人娱乐、解闷的游戏性质,在弥漫着商业气味与低级娱乐的电影市场上,重新树立起中国电影透视社会现实、展现历史变化的美学旗帜。
从某种意义上说,“第六代”作品的共同主题首先是青春——变动的城市的青春。他们的人物大多是生活在90年代的年轻都市漫游者,以及形形色色的都市边缘人。没有了历史反思的使命,这些导演自然选择了熟悉的自身成长经历的青春书写,热衷于表现所谓的成长的故事,更准确地说是在谱写“青春残酷物语”!正是由于这个特征,他们的电影中人物往往就是他们熟悉的人,很多电影都有一批固定的演员,如贾宏声、周迅、徐静蕾这些导演熟悉的演员;或者干脆使用业余演员,让他们自己表演自己,《妈妈》中母亲的扮演者秦燕自己就是一个残疾儿童的母亲;或者是导演自己参与表演,更增添那种青春的熟悉感,如《周末情人》中的王小帅,《冬春的日子》中的娄烨。电影中的残酷物语正是这些导演自身残酷物语在镜中的投影。
随着时间的推移,官方在观念上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2004年起,国家电影局在电影审批上采取了宽松的政策,对这些被封杀的年轻导演全面开禁,并且对一批在国际上获奖的导演进行经济上的资助,“第六代”全面从地下走到地上。然而,这些导演马上又面临在主旋律和商业片的大潮中如何保住自己独立的艺术风格,如何不被观众和票房吞没的考验。
八结语
冯小刚曾以调侃的方式说,电影界“第三代和第四代导演占据着宝殿,他们把大门把得很死。接着,第五代导演杀到,他们没走大门,直接‘破窗而入’,然而第五代导演杀入这座电影宝殿后,同第四代一起把窗子关严了。后来,第六代导演竟然也杀入了这座宝殿,他们既没有走门,也没有走窗户,而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等我杀到这里来一看,不但进不去这座宝殿,即便就是进去,也没有我下脚的地方。于是,我索性就在宫殿旁边自己建了个耳房。没想到,通过不断发展,日子过得还不错”谷子:《中国电影百年论坛开幕呼吁给国产电影更大空间》,《大连晚报》,2005年12月16日。。
中国电影的“代际”划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其实,中国电影真正的划分还是以改革开放的1978年作为红线,这以前的意识形态的强力介入是无法抵挡的,这以后中国电影在艺术形式上的追求已经初见端倪,但是距离形成独立的艺术精神还相距甚远。
从“第一代”的“影戏”、“第二代”的“呐喊”、“第三代”的“革命”、“第四代”的“解放”、“第五代”的“井喷”,一直到“第六代”的“烦恼”,中国电影的“代际”划分也许将寿终正寝,但目前还找不到一种新的指代来替代这个很不准确但又不得不用的划分方式。随着中国电影进入21世纪,一种新的力量正在大规模地介入到中国的电影艺术创作之中,这就是市场的无形之手。当我们面临着“第五代”被“收购”、“第六代”被“收编”的复杂局面时,那种长期被意识形态纠缠不清的艺术精神又如何在强大的市场中重新取得主导地位,正是新一代电影人面临的考验。
文化“解禁”与新生代电影的多重面向
聂伟,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
在2004年的第七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曾一度遭冷置的“地下电影”导演贾樟柯、王小帅、朱文等人集体亮相。这是他们第一次获得正式邀请参加中国内地由官方举办的电影节赛事。这场从“地下”到“地上”的集体“浮现”,再加上2003年底电影局主持召开的座谈会,公开宣布第六代导演正式回归中国电影市场体制和文化认同体系之内。2004年《十七岁的单车》更名为《单车》,通过了电影局的审查,并获得了放映许可证。该片虽然没有真正获得票房统计数据,但已然表明相关管理部门的一种宽松姿态。此后,相继出现了《可可西里》、《世界》、《看上去很美》、《青红》、《落叶归根》、《图雅的婚事》、《三峡好人》、《左·右》、《两个人的房间》、《二十四城记》等一批剧情电影以及《东》、《无用》等纪录片。
短短五年间,“新生代”俨然成为中小投资国产电影和青年导演群体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品牌。而新生代电影导演在获得更多投资渠道和创作机遇的同时,也必须面对远比“地下”时期更为复杂多变的“意识形态动力学”参见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转引自周宪:《超越文学》,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页275。问题,即在保障自身创作自由度的前提下,如何在主流电影叙事、国际电影节、目标受众和电影票房多重力量的相互制擎之间,寻求个体言说与接受空间的最大化。早期的新生代导演大多追求艺术层面上的一维创造,这种简单的纯粹性也维系着“这一代”的独特属性。及至当下,置身于独特的中国电影工业体系与复杂的国际语境之中,他们各自不同的关注焦点、主题选择、创作姿态,乃至对电影艺术本体的理解差异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放大,从而产生出多元化的美学创作面向。如果说“这一代”尚且存在一些共性,那么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也许就是,他们都在极力脱离早期“SMHM”参见聂伟:《SMHM:新生代影像传播的文化模式分析》,《文艺研究》2006年第1期。(SmallMovieandHomeMovie)的叙事类型与影像传播模式,试图建构真正意义上的大银幕作品,以满足导演的“影院情结”。同样,当维系“这一代”的属名仅仅在商业品牌的市场意义上具有相似性的时候,恰恰也开启了中国电影新世纪以来的“无代”叙事参见贾磊磊:《时代影像的历史地平线——关于中国“第六代”电影导演历史演进的主体报告》,《当代电影》2006年第5期。,一个崭新的电影文化地形图正渐次展现在我们面前。
主流/边缘:价值滑动与类型转变
在早先的一篇文章中,笔者曾经指出新生代电影属于一种典型的“异托邦”(Heterotopies)叙事。参见聂伟:《从“后黄土地”到“后贾樟柯”时代——第六代电影美学与产业发展略论》,《上海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在德勒兹的意义上,“异托邦”是一种描述,而非实在的客观事物。这一概念提供了现实社会中可能的另外存在,也就是以生态学的形状而非金字塔的结构,另行发展一个亚社会、一个无形的地下世界。它外化为年轻人自发的公益团体、非营利自由媒体、无政府主义研究会、黑客和网络社团、遍布全球的地下音乐传播体系、艺术家社区和互助公社等各种亚文化圈。与第五代影像面对历史记忆的乌托邦式空间改写不同,第六代导演更侧重于具象化地呈现出同一历史时期不同个体自身叙事空间的多元文化属性。创作者通过崭新的“异托邦”叙事打捞有限的个人记忆,借此在微观化的自传、半自传体文本世界中完成对“现实”的局部触摸。姑且借用学者张真的说法,这是一种与“身体写作”相仿的“触感电影”。参见张真:《苏州河,城市记忆和触感电影》,赵锡彦译,文章载于“终点网”,http://www.zhongdian.net/show.aspx?id=215&cid=23。新生代导演终于从传统现实主义电影的说教体例中挣脱出来,在他们的镜头中呈现出迥异于宏大叙事笼罩视野之下的另一类“现实”。如同贾樟柯的《世界》,工作在“万国建筑”中的“民工演员”小桃永远也不可能体验到精英知识分子所痛心疾首的时空错乱症,相反他们感触最深的却是彼此在同一时间截面上的空间离散之痛。表面看起来他们工作在一个象征广阔的万国空间里,事实上并没有任何空间属于他们,他们的“在世性”也是靠不住的。亦如同张元的《看上去很美》,导演借助方枪枪略带叛逆的目光,窥探到成人世界彼此心照不宣的成长隐秘。影片中导演有意悬置了自己的成年人身份,他并非像《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那样通过镜像将成人世界简单倒置,而是以喜剧化的手法揭露了“小红花”传统背后的权力生成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