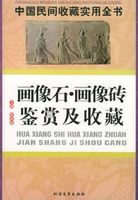在纷繁芜杂、暗流涌动的战后上海,不论是设想还是实践一个纯洁自为的电影(文化)都是徒劳的,一个最简单的原因就是电影已是上海居民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必需品了。选美事件之后的1947年,文华公司第二部电影《假凤虚凰》引起更大轰动,招致全国范围的抗议、抵制甚至骚乱。就因为《假》片中有所谓“贬低”理发师(匠)形象和对苏北人“漫画般”刻画的片段。上海的理发公会、理发工会、扬州同乡会同时发难。很多苏北人由于方言和地域的亲近,在工作中多保持传统的师徒关系,而理发师行业多半也是苏北人垄断,详见第39页注1。7月11日,《假》在首轮影院大光明试映,成群的理发师将影院层层包围,阻止观众入场并竖起标语抗议片中的“侮辱”场景。很快事件升级为一场骚乱,引来大批警察的干预。虽然事件最后是在上海社会局的调停下,各个工会/公会、同乡会和文华公司达成了和解(删去3处“羞辱镜头”),但美国萧知纬教授提醒我们这个事件可以放在民国“社会激进主义”的框架中考虑,这种激进行为不是和热议的国家—民族有关,而是更关乎职业体系和地方因素,同样也是民国后期“抗议文化”的一个典型。萧知纬:《民国时期社会激进主义》(“SocialActivismduringtheRepublicanPeriod:TwoCaseStudiesofPopularProtestsagainsttheMovies”),《二十世纪中国》2000年第25卷第2期,页55(TwentiethCenturyChina,Vol.25,No.2[2000],p.55)。在此我想补充三点与1945年后的上海电影图景有关的论断。第一是大规模的抗议吊诡地使文华公司因祸得福:《假》一片在上海乃至全国都受到无数媒体报道,家喻户晓,很多场次爆满。所以某种程度上,它巩固了电影娱乐领头羊的位置,也让电影成为媒体报道的中心。第二,导演黄佐临在看到《假》的流行之后,亲自张罗人马用英语配音,并将英文拷贝卖到美国和英国,成为中国人最早用外语配音的国产电影。这不仅让此片的“剩余价值”大大增加,而且让整个《假凤虚凰》事件产生了跨国和翻译的风味。第三个论断是有关一些潜在因素而使《假》成为轰动一时的电影事件:其女一号李丽华也是被诟病的“伪华影”明星,《假》是她战后复出的首部影片,自然又是媒体炒作的一个话题;例如在《李丽华是怎么成名的》一文揭露了她的“通敌”史,以及这样的名声如何让《假凤虚凰》变得更有争议性和卖座。见《中国明星》1948年第1期,页12。上海的地方势力和情感(扬州同乡会)发挥了与公会/工会几乎同等的抗议力量,表达其诉求;事件的力度和规模显示了各种社会团体的斡旋和干预本领,反映民国后期的市民社会的特征;最后《假凤虚凰》在不同地区的不同命运(或被剪,或被禁,或被保留)也反映电影发行的地方政策因素以及在中央体系下地方相对的自治权。关于《假》不同的放映命运,可见《〈假凤虚凰〉在北方》,《青青电影》1947年第8期,页11;《〈假凤虚凰〉在广州》,《青春电影》1947年第4期,页16;以及《假凤虚凰在福州》,《青春电影》1947年第12期,页15。
但不是每个事件都远离政治,或者归于和解。“金都戏院血案”就是一例。该事件发生在1947年7月28日,造成9死19伤的严重后果。尽管这是一场上海警察和宪兵为了争夺戏院的控制权和话语权而发生的惨案,却反映了电影的风靡程度。和金城、文化会堂一样,金都从属于国泰电影公司,所以经常首映国泰的电影。《大中华发行新片改走中间路线》一文中论及上海三条国产院线,金都、金城和文化会堂就是其中一条。见《艺海画报》1948年新第10期,页6。28日这一天,国泰的巨资大作《龙凤花烛》继续上映,门口照例排满了买票者。7月上海,如火焦烤,在工务局供职的刘俊夫看见买票长龙,没有买票就和朋友走进戏院,要求张检票员让他补票进场。张的严词拒绝很快变成双方激烈口角,引来无数行人和买票者观望。事件很快升级为交通大堵塞,随后招致警察和宪兵两股不同势力的干预,每一方都希望是仲裁者,然后从戏院处收取好处费和调停费。双方互不相让,导致走火和对射。如果不是国泰《龙凤花烛》如此火爆,排队者众多,人群也不会阻塞交通,引来武力干预;如果电影不是最赚钱最风光的产业,成为各利益集团觊觎和蚕食的对象,就不会有军警双方的争夺和互射。也许就连国泰和《龙》的导演屠光启也没有想到一部古装大片的流行会带来这么大风波和这么多的生命逝去。
即使在电影圈内,电影的流行也造成资本和权力的不均衡分配。在产业链终端的影院(特别是首轮)攫取了大部分行业利润。而处在产业链上游的本土制片公司,则因为投资要求大,规模更巨,人员芜杂,没办法维持稳固的现金流和适应物价日涨的环境。可是,电影制片者并不能像放映人员那样能轻易罢工或抗议,因为前者一旦停下就无米可炊,而有较高的自由度和控制力的后者即使没有国产片放映,还可以放外片(特别是好莱坞和英国片,即使是二轮)。《物价涨,影响制片商》,《青青电影》1948年第36期,页2。因此每当电影票价不能弥补疯狂的通货膨胀时,影院从业人员,就往往会由工会组织联合其他力量罢工。早在1946年7月1日,上海影院行业已有“预演”,集体“自动停业”要求票价随物价指数上涨,并要求能自主定价。但其要求被社会局否定,理由是“电影作为最流行和最大众的娱乐,是居民的必需品,故其票价应由政府掌控”。《上海票价又涨;停业请求减免娱乐税》,《时代电影》1946年第16期,页11;以及《7月1日各个戏院自动停业请免专辑》,《中外影讯》1946年第17期,页9。1948年11月18日,一场由影院职工和技工组织发起的全市范围内的电影从业人员大罢工(超过1000人)又在呼吁提高票价,抗击通胀。这场罢工事件持续三天之久,最后社会局不得不让步。和“金都血案”类似,这场罢工并不是政治起义,而是源于商业团体/工会和政府机构之间的经济矛盾。因为社会局费尽心思要稳定/打压电影票价来营造一个“和谐,容忍”的氛围,而工会和电影从业人员却更多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结果却是零和博弈:多名工人被抓,52家影院停业3天颗粒无收,上海税务局也损失大量税收。《电影院停映内幕:一共3天,劳资爆发》,《世界电影副刊》1948年第4期,页11;以及《电影院停业,各方损失大》,《艺海画报》1948年新第9期,页14。虽然最后各方有一个妥协方案,然后损失已无法弥补。但换个角度,作为战后上海“抗议文化”中高潮之一,这个事件也证明了电影产业强大的运作能力,各方利益集团都不敢小觑电影在娱乐、教化、宣传上举足轻重的作用。
四结论
最近美国出版了重建美国电影史的一系列类似编年史的专著,其中一本《繁荣与萧条:1940年代的美国电影》有如下阐述:“此书的研究强调一手资料,特别是行业交易文件和制片公司档案。在这所有的档案材料中,我们特别关注生产记录、办公室之间的备忘录、合同、法律文书、经济报告、制片公司和纽约总部之间的通信。主要的媒体报导来自Variety和MotionPictureHerald杂志以及WallStreetJournal和NewYorkTimes。”ThomasSchatz等编著:《繁荣与萧条:1940年代的美国电影》(BoomandBust:TheAmericanCinemainthe1940s),页6。从比较分析的视野,这段论述对中国电影学者,尤其是有志于产业研究的,应该有非常大的启发。它提供了在特殊历史情境下如何切实研究电影产业的思路。的确,时代更迭、战乱频繁、政治敏感让中国电影的第一手资料憾缺很多,包括珍贵的电影拷贝、电影杂志、制片档案和经济资料等。而且很多资料的运用带有很多偏见和导向性。但这样的困境不应该阻碍我们的研究,正相反,电影学者更应该努力去挖掘尘封的材料并重新理论化使用它们。在这篇文章中,笔者采取的是跨媒体、多学科的方法去考察战后上海短暂却激荡的电影岁月,并偏重于产业特征研究。文中几乎没有接触到任何电影文本或细读分析,却用历史、文化理论、社会科学和媒体研究的方法论来补充和丰富传统的电影产业话语。这篇论文可以说是一种比较的、跨学科的理论实践,希望对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有所启发。这个领域不仅潜力无限,更需要不同的批评声音。
赎罪与新生: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创建
石川石川,上海大学教授。
1949年创建国营上海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上影)的过程,是被各类中国电影史反复述及的话题。本文再次触及这个题目,与其说旨在重建它所指涉的历史事件,毋宁说是想对人们的历史记忆进行一番重新梳理。本文关注的重点并不在于上影初创时的创作现实、文艺思潮或美学突变,而在于考察一场历史转型背后掩藏着怎样的政治、文化与体制操作。与1949年其他地区国营电影厂不同的是,上影的重建并非是一段从无到有的拓荒史,它是一次赎罪后的新生,是一场浴火涅槃,是对1949年前上海原有电影厂基础的一次清盘和重构。这一过程既包含对电影工业要素的重组,也包含对上海电影文化、意识形态与其社会文化功能观的批判性重建。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1949年前的文化原罪让上海电影背负起了一座沉重的精神十字架,这种原罪不仅是由上海这座城市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的角色所决定的,也是1949年以后人们基于特定历史观对上海城市文化与城市功能的一种想象与定义。从这个角度说,1949年后对上海电影厂的重建,其实也是上海电影、上海电影人所经历的一场自我忏悔、洗清原罪、最终求得救赎和新生的历史忏悔录。正如夏衍1949年11月在国营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大会上发言所说的那样:“上海过去不但是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侵略的据点,也是它文化侵略的据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观念在这里是根深蒂固的。因此,我们在这个地方能从事人民文化的责任确实是非常艰巨的。”夏衍:《在国营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大会上的讲话》(1949年11月16日),上海档案馆档案号:B17711。或许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历史判断与文化经验,才使得后来人们对于上海电影重建的历史陈述中,充满了一种脱胎换骨、焕然一新的自我欣赏与满足。这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的那样,关于这段历史的种种描述,就像婴儿在镜像中所看到的自我——一种想象中完美的自我投射。林勇:《文革后时代中国电影与全球文化》,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于是,在镜像与现实、理想与肉身自我之间便形成了一道巨大的空隙,它为后人反复想象、反复阐释这段历史提供了充分的可能,也使得各种彼此冲突、抵牾的历史叙事都能获得它们各自的历史合法性。
相比较于历史书上一笔带过式的简约且语焉不详的表述,上影厂的创建过程要显得复杂得多。为了叙述方便起见,本文将沿用所谓“四级跳”的说法徐桑楚:《风雨征程四十年》,上海电影局史志办编:《上海电影史料》第4辑,1994年。,通过对“敌产接管”、“公私合营”、“国有改造”、“两厂合并”四个部分的描述来呈现上影厂的创建轨迹。
一敌产接管:上影的起点
1949年4月,上海解放在即。此时,上海电影的接管计划也分为内、外两条线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所谓外线,是指刚刚在江苏丹阳成立的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所属文化教育管理委员会。委员会主任由陈毅兼任,副主任有夏衍、钱俊瑞、范长江、戴白韬、韦悫,其中电影部门的负责人为于伶和钟敬之。所谓内线,是指中共上海地下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下的“影剧中心组”(成员有吴小佩、吕复、刘厚生三人)及其外围组织“剧影协会”。曹懋唐:《在迎接解放的日子里——记“剧影协”地下党外围组织》,《上海电影史料》第4辑。
1949年5月27日,解放军进驻上海。军管会文教委员会随之进驻位于爱多亚路(今延安路)的浦东大楼办公,并在此设立新闻、文艺、出版、教育等多个业务处。电影由夏衍、于伶负责的文艺处归口管理。文艺处又设有电影室,办公地在梵皇渡路618号,具体承担电影接管工作,电影室正副主任有于伶、钟敬之,工作人员有张客、池宁、徐韬、吴铭等;电影室所属的电影工作委员会,主任由钟敬之兼任,副主任为徐韬、池宁,另有干事2人、联络员15人和1个放映队。《上海军管会文管会文艺部人员名单》,上海档案馆档案号:B17211。
早在解放军进城之前,中共地下党方面已为接管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关于中共地下党具体工作内容可参见朱江:《“天亮”前后的斗争》、王铭章:《关于“五人小组”的回忆》、袁立风:《我参加护厂斗争的经过》,均载杜文林等:《上海电影史料》第2辑,1993年。包括在各电影企业中组织护厂小组,保护场地、器材设备不受损坏和丢失,对国民党公营电影机构的资产、设备、人员组成情况进行清查造册,动员电影工作者留守上海,迎接解放等。
对于电影的接管,军管会文教委主任陈毅曾提出过明确的要求:一、分步骤展开,“先接后管”;二、对私营电影厂应“扶持管理、逐步改造”;三、对充斥市场的英美“有毒”影片采取限制、抵制措施。江海天:《难忘的历程——上影厂初建的回顾》,杜文林等:《上海电影史料》第2辑,1993年,页1。根据陈的指示和中央有关“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没收官僚资本”的整体部署,军管会从1949年6月3日一般电影史都说是6月初开始接管,据1950年1月出版发行的《青青电影》1950年第1期刊登的《1949影坛大事记》记载,接管工作开始于1949年6月3日。开始对原国民党所属电影机构进行全面接管。据军管会文艺部拟定的《工作计划草案》上海军管会文艺部:《工作计划专案(第三篇)》(1949年6月)。一文,电影接管的对象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国民党公营电影制片机构(5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