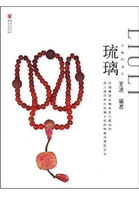不管是“流利的调子”,还是“胡闹喜剧”或“流线型的喜剧”,这些概括都注意到疯癫喜剧情节和节奏轻快、紧凑风趣的艺术特色。就疯癫喜剧的导演而言,刘别谦早在20年代就为中国电影人所熟悉,他的《循环夫妻》(1924)、《三个妇人》(1925)、《禁入的乐园》(1924)和《温德米尔太太的扇子》(1925)以含蓄婉转的风尚喜剧(comedyofmanners)手法博得中国电影人的喜爱。他1938年拍摄的《第八夫人》以及几年之后拍摄的《不确定的感情》(ThatUncertainFeelings,1941)则具有明显的疯癫喜剧特征。30年代因《一夜风流》而成名的卡普拉是深受中国电影人爱戴的另外一位导演。尽管进步电影人夏衍对卡普拉的作品持一定的批评态度,认为他的电影“大部分是投合小市民心理的非现实性的所谓‘娱乐影片’,他的‘娱乐’的特征,就建立在这种‘非现实’的基础上面”,认为卡普拉只是流利而诙谐地讲述空虚缥缈的故事,让观众感到“暂时的抚藉和安慰”,夏衍:《电影作家的态度问题——关于最近美国影片的杂感》,见《夏衍电影文集》第1卷,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页186—187。但是也有评者指出,卡普拉的影片“都有一种优雅的幽默感,敏锐的社会讽刺性和对于纯真人性的信仰心”《天才导演卡普拉》,《电影周刊》第32期,1928年4月。。今天读来,似乎后者更准确地概括出了卡普拉电影的主旨与风格。
桑弧在回忆自己的艺术生涯时曾谈到刘别谦和卡普拉对朱石麟和他本人创作的影响,特别是幽默喜剧的创作。参见陆弘石、赵梅:《桑弧访谈录》,《当代电影》1999年第6期。虽然目前尚缺少一手资料说明疯癫喜剧与其他导演的关系,但在本文所列举的战后浪漫喜剧中,有各种各样的细节指示出疯癫喜剧的影响,比如《乘龙快婿》在叙事结构上对《休假日》的搬用,陆文蕙(白杨饰)模仿凯瑟琳·赫本的男孩儿性格塑造;《假龙虚凰》与《伊芙夫人》类似,都把欺瞒手段用到男欢女爱的情场上,而片中的“婴儿”很容易勾起人们对《育婴奇谭》的记忆;还有就是《街头巷尾》对《一夜风流》最著名桥段的引用,《还乡日记》中闹剧(slapstick)段落的嵌入等等,都说明美国疯癫喜剧被以各种方式引入中国浪漫喜剧的创作之中。
但更重要的是,这个移植过程同时也是中国电影在自身政治、社会、文化、电影工业和审美传统背景之下对浪漫喜剧的重构与创造。
二主题转换:从质疑美国梦到战后伦理重建
从时代背景看,中国社会在经历了短暂的战后喜悦之后,40年代后期社会经济生活陷入困局。在战场上失利的国民政府当局,在后方的经济领域也渐露颓势,失业率上升、法币巨幅贬值,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倍感艰辛。由此,中国战后浪漫喜剧也像美国疯癫喜剧一样是经济萧条背景下的产物。虽然背景相似,但影片的社会功能却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美国疯癫喜剧是通过贫富男女的爱情沟通阶层差别,通过对率真、自由的生活的颂扬质疑、校正单纯追求财富的“美国梦”,通过多元化的价值观让人们看到生活的丰富多彩,从而摆脱经济压力困扰的话,中国战后浪漫喜剧更侧重的是社会伦理的重建,它强调的是一种底层民众的劳动伦理,并且表达了对正常生活秩序的渴望。
在影片《假凤虚凰》中,寡妇范如华为摆脱生活窘境,冒充家产丰厚的年轻女子征婚,而理发店的“三号”理发员张小毛,向往着住洋房、乘汽车的日子,因而接受他人建议,冒充留学博士前去应婚,男女双方都急于靠他人改变暗淡的人生,在互相欺瞒的过程中,尴尬场面不断,从而制造了种种笑料。真相大白后,两个人的情绪从愤怒转向相互谅解,最终认识到要靠自己诚实的劳动生活:最后,范如华成为店里的一位修甲师,夫唱妇随,两人开始了平实而快乐的生活。这种伦理上的规诫是美国疯癫喜剧中所没有的。比如在《伊芙夫人》中,伊芙的英文Eve即夏娃,影片借用了《圣经》故事,用此名暗示片中女郎的骗子身份。伊芙是个常在邮轮上行骗的女子,因为对富家子克比萌发爱情,才放弃了行骗的机会;为了报复克比离她而去,伊芙又假扮英国贵妇,用自己的魅力征服了爱人。直到剧终,木讷的克比也没有识破她的圈套,并再次投入她的怀抱。在片中,伊芙的机敏、智慧与出色的口才完全掩盖了她行为的不道德感,而事实上,为了爱情不择手段十分符合疯癫喜剧的伦理。有趣的是,《假凤虚凰》以谐谑的方式所表达的伦理观在当年并未得到完全的理解,相反,还因为有损理发师的形象引发上海理发公会的抗议。《〈假凤虚凰〉发生纠纷上海理发公会提出抗议》,载《联国电影》8月号,1948年第8期。
《街头巷尾》对劳动伦理的肯定更为彻底。该片讲述了青年小知识分子李仲明(张伐饰)由于失业,生活无计,变成三轮车夫但最终赢得爱情的故事。由于社会的偏见,他跟小学教师赵淑秋(黄宗英饰)的交往受到非议,不久丢掉工作的赵淑秋不得已做起了报摊生意。影片通过李仲明之口,批评了中国对劳动者的歧视,他说:“我们知识分子也只知道在理论上否定这种看法,却并不曾彻底去认识这条社会上久已存在的鸿沟。”潘孑农:《街头巷尾》,《电影小说丛刊》,作家书屋刊行,1937年8月再版,页43。而影片肯定的正是李仲明和赵淑秋用实际行动跨越这条“鸿沟”。正如前述,美国疯癫喜剧在面对类似的经济危局时,通常采取调和手法,在《一夜风流》里,富家女爱上了穷小子;《浮生若梦》中,艾丽丝演绎了现代版的“灰姑娘”,最终赢得了大银行家克比家族的认可;《育婴奇谭》里一个盼望得到资助的动物学家最终在富家女那里实现了梦想……总之,爱情成为跨越阶级鸿沟的桥梁。但《街头巷尾》却没有借用这种处理手法,没有让穷小子李仲明和富家女,即车行老板女儿孙金娥(章曼苹饰)相恋,不仅如此,编导还有意把富家女孙金娥设置为丑角,她因对李仲明的单恋而受到其他三轮车夫的嘲讽。应该提及的是,编导潘孑农在回忆《街头巷尾》的创作过程时曾说,他在重庆读了老舍的《骆驼祥子》,就产生了改编之意,那时还常与作者见面,甚至共同设想过由魏鹤龄饰祥子,舒秀文饰虎妞。战后,“中电”一厂邀潘孑农编导影片,他就重新想到了这个未实现的梦想:“如今一厂找我拍片,总去不掉设想已久的《骆驼祥子》的影子,心想北平没有骆驼,上海有的是三轮车,于是构思了这个以‘劳心不如劳力’为主题的讽刺喜剧《街头巷尾》。”潘孑农:《舞台银幕六十年——潘孑农回忆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页193—194。因此,孙金娥这个人物形象显然受到虎妞的启发。但正如潘孑农自己所说:“这个故事既非‘剽窃’,也不是‘改装’”,他并没有照着老舍原作的叙事线索,让车夫和车行老板女儿走到一起,而是仍然把孙金娥作为另一个阶级的代表。由此,这部浪漫喜剧并不追求对阶级鸿沟的触动或消弭,而是通过李仲明和赵淑秋的阶级身份转变,对底层劳动阶层予以了肯定。
《乘龙快婿》通过爱情的选择,通过对善恶的区分,在重建伦理的同时表达了对社会秩序的渴望。影片叙事结构与《多情大姨》十分相似,都是一个男子在即将步入婚姻之际爱上了未婚妻的妹妹/姐姐。但这种选择变化背后所包含的价值取向却有很大区别。《乘龙快婿》中的司徒炎(金焰饰)战后从重庆返回上海,女朋友陆文兰满以为他会像别的“接收”大员一样,给她带来洋房汽车,使她发大财,从此过上优裕富足的生活。但没想到司徒炎空手而归,只是一个无权无势的报人,还在报上揭露文兰舅舅的丑行。陆文兰一气之下投入他人怀抱。原本对司徒炎抱有敌意的陆家妹妹文蕙渐渐对他心生爱意,她是个性格独立、富有正义感的职业青年,嫉恶如仇,渴望建立一个公平美好的社会,正是这一点深深打动了司徒炎。最终一对有情人离开上海,追求共同的事业。在《多情大姨》中,年轻的穷小子强尼(格兰特饰)爱上了银行家之女朱丽亚(多利斯·诺兰饰),但却不愿像未婚妻所希望的那样,进入大银行从事呆板无趣的工作,两人分道扬镳。姐姐琳达(凯瑟琳·赫本饰)与强尼性情相近,性情奔放,无拘无束,最后,她取代了妹妹的位置,与强尼一起出海航行。像其他美国疯癫喜剧一样,影片表达了对富人刻板生活的蔑视,对天真、自由、富于童趣的生活态度的肯定。但促使司徒和文蕙走到一起的,却是对腐败的厌恶,是建立一个公正社会的愿望和热情。也正因为这一点,《多情大姨》中娱乐室的玩耍、嬉闹场面,在《乘龙快婿》中被转化成恶势力与正义人士在报馆里的打斗,前者是身体的自由与解放,后者则是善恶的较量。显然,主题的转换使中国战后浪漫喜剧直接面对中国现实,为困惑不安的中国观众点燃了新生活的希望。
三含蓄的东方情爱
作为疯癫喜剧的开山之作,《一夜风流》和《二十世纪快车》同时也代表了这一类型片的两个不同形态:一个是以卡普拉的作品为代表的社会主题喜剧,它具有明显的价值观导向和提升民众精神的意图;另一个则是以霍克斯的作品为代表的偏重男女感情的爱情主题喜剧,正如贝克顿所说,有相当数量的美国疯癫喜剧“将政治问题,比如阶级差异等转化成隐藏的性别问题”。约翰·贝尔顿:《美国电影美国文化》,页190。而且,与一般的浪漫故事不同,疯癫喜剧的爱情公式是用激烈的矛盾冲突掩饰男女彼此爱慕之心,正像《育婴奇谭》借精神分析学家莱曼教授之口所说的那样:“男人的爱欲冲动经常用冲突的方式显露出来。”因此,男女双方由矛盾冲突最终转变为炙热爱情,成为疯癫喜剧一再重复的叙事模式。可以说,在《海斯法典》的压制和约束下,疯癫喜剧通过制造男女之间张力关系,使被压抑的爱欲得到宣泄和释放。
一方面,在爱情表现上,中国战后浪漫喜剧移植了疯癫喜剧的这一风格特征。比如《花外流莺》一片正是以男女的矛盾冲突开场的,他们因歌声结下了冤仇:在沈家做家庭教师的丁求实喜爱读书,却受到邻居歌声的干扰,劝阻不成,他一气之下,用一个便笺包裹着小石块投进邻居周莺(周璇饰)的房里,表示抗议。第二天,丁求实来到周家餐馆吃饭,得知他就是那个扔“石头”的人以后,周莺故意让人在他的面条里加入了许多辣椒,把丁求实辣得口舌生烟。同样,《乘龙快婿》中的司徒炎和陆文蕙也是以矛盾关系开始的:返回上海的司徒在火车站错过了接站的未婚妻,只好和朋友老邱直接前往陆家。家里只有文蕙和小弟,得知客人到了,文蕙故意坐到沙发上看书,对司徒他们不理不睬,让二人颇感尴尬。
但是另一方面,战后浪漫喜剧并没有像疯癫喜剧那样紧紧围绕男女之间的“情爱战争”展开。《花外流莺》中,虽然周莺和丁求实开始时有些小摩擦,随后又因为丁求实的学费问题有过一些争执,但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很快缓和下来,影片的叙事线索也从“周丁恋”转变为一场追逐闹剧,变成一出捉迷藏式的游戏,周莺被误带到上海,并因此发生一连串误会。《乘龙快婿》里,司徒和文蕙的分歧因姐姐文兰的失望和变心而结束,随后,他们的爱情被共同的正义事业加温。在影片中,当司徒激动地告诉文蕙“我们跟那帮贪官污吏的战争已经开始了”的时候,旁边的小学生们哄笑着哼唱《结婚进行曲》的调子,委婉地道出他们心底涌动的感情。
因此,战后的浪漫喜剧虽然明显受到疯癫喜剧的影响,加入了一些搞笑的情节,比如夸张的动作和大量的巧合,但在男女情爱表现上却不像美国疯癫喜剧那样充满张力感,从而缺少颠覆性的快感,而是更温情脉脉,更充满两情相悦的温馨感,比如《街头巷尾》中的阁楼爱情和《还乡日记》中的夫妻恩爱就是如此。由于学生家长反对小学教师赵淑秋与三轮车夫来往,赵因此丢了工作,一时无处可去,最终接受了李仲明的提议,暂时借住在他的阁楼上。随后夜晚下雨,本来打算在三轮车里过夜的李仲明不得已回到了阁楼,他用布帘将一间屋子一分为二,开始了与赵淑秋的“同居”生活。这一场景不免让人联想到《一夜风流》里的经典桥段:任性富有的安德鲁小姐(考尔白饰)与靠采写新闻为生的平民记者皮特·沃纳在一家旅馆内隔帘而居。这幕场景被电影研究者认为是“法典对银幕上男女的爱恋压抑最好的案例”,盖博的克制是对欲望的“自我审查”,是法典的“内在化”。约翰·贝尔顿:《美国电影美国文化》,页188。《街头巷尾》对这一桥段的移植以虚构的方式复现了《一夜风流》给中国观众带来的观影愉悦:住在楼下的朱老五发现了李仲明和赵淑秋隔帘而卧的秘密,大感兴趣,他招呼妻子来看,妻子也忍不住笑出声来。朱老五说:“你可别闹醒他们,让我去找大家来参观参观这新鲜玩意儿!”随后,他果真把陆长根、小神仙、黑寡妇三媛等左邻右舍带了来,“大家争先恐后,蹑手蹑脚地爬上楼梯去看”。最后,单薄的楼梯不胜重负,咔嚓一声,断了。潘孑农:《街头巷尾》,页51—52。“新鲜玩意儿”暗示出这一景象的外来性,沉睡中的李仲明和赵淑秋像银幕“奇观”一样给观众带来“窥视”的愉悦感。
但与疯癫喜剧从敌对到相爱的爱情曲线不同,“同居”中的李仲明和赵淑秋一派“琴瑟和谐”,赵淑秋不仅协助李仲明攒钱购置三轮车,还利用工余时间教弄堂里的儿童识字,李仲明则帮助赵淑秋置办报摊,他们互相关爱,渐渐地相互萌生爱意,两人都暗自备下一对金戒。在这里,爱情像是一丝阳光,照亮和温暖着穷困的现实,因此,《街头巷尾》的爱情更接近鲍才琪(F.Borzage)《七重天》(SeventhHeaven)式的浪漫温情。只是通过朱老五、陆长根等邻居的加入,影片才有了喧闹的喜剧气氛。
《还乡日记》中,一对在后方从事话剧事业的年轻夫妇老赵(耿震饰)和小于(白杨饰)回到上海,他们与其他朋友一起,聚居于阁楼之上。夫妻分卧上下铺,再次重现了《一夜风流》式的情欲克制场面,达到异曲同工之效。结合中国的历史社会背景,影片将抑制的情欲转换成外在的社会矛盾,即复员人员重新融入社会的艰难。他们四处寻找房子,但梦想一次次落空,最后在目睹了接收大员和“汉奸”的一场混战之后,他们重新回到阁楼。夜深之后,小于从上铺下来,之后镜头摇移到窗户,再叠化成清晨,全片最后以一个特写的双人镜头结束,一对夫妻在幸福地酣睡。